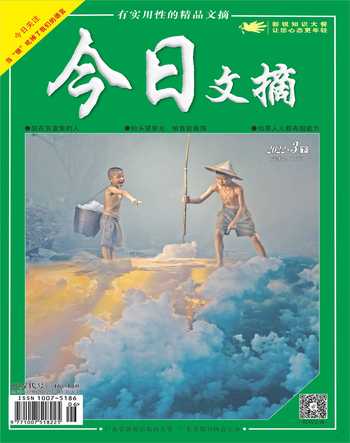菜名翻譯鬧笑話

同事從巴厘島旅游回來,談到一路上的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語言不通。翻譯,尤其是菜名翻譯,說與聽意思不一致,帶來了諸多不便,甚至造成笑話和誤會。
在“啞巴英語”的口語水平和單詞積累的情況下,很多對服務員講出來的菜名,上菜時端出來的卻是另一種東西。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英語發音舌頭卷得太厲害國度的某些地方,更是讓人崩潰。所以,在飛機上,在飯店里,在商業區,在旅游景點等就餐,只好一個勁地充當“膽小鬼”發“牢騷”——只能反復說著既指“膽小鬼”也指“雞肉”的“切坑”(chicken),既指“牢騷”也指“牛肉”的“碧芙”(beef),整個旅游期間,吃的全是雞肉和牛肉,吃得口淡無味。
菜名的翻譯一直是翻譯界的大難題,就連資深的翻譯家都覺得很難譯得意思準確、傳神達意。在報紙上看到一個為國家領導人當翻譯的翻譯家的經歷。有一次,他負責翻譯國宴菜單,有道熱菜叫罐燜鴨子,外賓很感興趣,看過譯好的菜單,卻嚇了一跳。見外賓的驚訝,他就拿起菜單,便發現了問題。于是,他把菜單遞給身邊的更為資深翻譯家看,兩人都樂壞了。老翻譯家舉著菜單說:“你啊,鴨子怎么受傷啦?”原來罐燜鴨的“燜”(braised)譯成了“受傷”(bruised)。也許這個“鴨子在罐子里受傷”是譯者的疏忽,將一個字母寫錯,從而使人忍俊不禁。其實,即使字母沒寫錯,braised這個英語單詞是燜和燉的意思,也就是說,燜鴨也許會被理解為燉鴨。而燜鴨和燉鴨并不是一回事。
無獨有偶,下面這個例子就更能說明菜名翻譯之難。中國有道菜叫童子雞,有位翻譯將其譯為“從未有過性愛經歷的公雞”。翻譯領導覺得不雅,便問翻譯為何不譯成“未成年的雄性雞仔”呢?翻譯說:“曾經這樣譯過,遭到了動物保護組織人士的抗議,他們認為將未成年的雞宰殺是殘忍的動物虐待。所以才譯成沒有做過那方面事的雞。”領導又說:“可以譯成‘處于青年時期的雞’嘛。”翻譯回答:“動物在青年時期也會有過那方面的經歷,一旦有過,便不是童子之身了,所以這樣翻譯不能準確表達其含義。”如此一說,領導也就不再追問了。
曾在一個菜單上看到擔擔面的翻譯,叫“芝麻摻著醬肉和讓它發芽成豌豆狀的面條”(noodleswithsesamepasteamp;peasprouts),確實復雜,但好像沒有譯出擔擔面的特色和風味來。水煎包子翻譯成“輕輕地油煎一下的面包”(lightlyfriedChinesebread),啰嗦又不準確。
對于復雜的菜名翻譯,建議對中國菜名干脆音譯,不要費勁地意譯,就像人名的翻譯那樣。對外國菜名,目前好像有很多音譯,如比薩、漢堡等,至于其中的寓意和韻味,那就只能意會,讓食用者在享受中細細體會吧。
其實,生活中有很多事只能意會而無法言傳。對這些我們千萬別去做弄巧成拙的說明和解釋,否則,要么造成誤會,要么成為笑話。假如讓我去翻譯菜名,童子雞就叫“童子切坑”(tongzichicken),不會絞盡腦汁去說明已經烹熟的雞有無感情經歷啦!
(彭嘉木薦自《松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