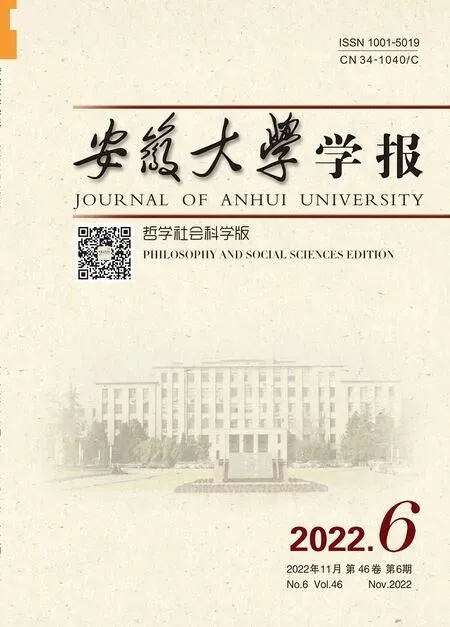安大簡《詩經》中的“蟡”字試析
侯乃峰
一、安大簡《詩經》中的“蟡”字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公布了一批戰國《詩經》竹簡(以下簡稱“安大簡《詩經》”)。這是迄今為止可以見到的最早的《詩經》抄本,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安大簡《詩經》中,出現了三個原整理者隸定為“蟡”的字,字形列舉如下:



三個字所在文句的辭例都是“蟡=它=”,即“蟡它”之重文,皆對應今傳本《毛詩》的“委”字,毫無疑問這是同一個字。原整理者于第31簡注釋說:
蟡=它=:《毛詩》作“委蛇委蛇”。“蟡”“它”二字后有重文符號。“蟡它”,疊韻聯綿詞。《韓詩》作“逶迤”。“蟡”屬匣紐歌部,“委”“逶”屬影紐微部,影、匣同屬喉音,歌、微二韻亦很近,《詩經》中有大量歌、微合韻的現象,可資佐證。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卷十九“逶迤”注引“逶”又作“蟡”。“它”,“蛇”之初文。古從“它”者多與從“也”通,故“蛇”“迤”可相通(參《古字通假會典》第六七八頁)。毛傳:“委蛇,行可從跡也。”鄭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此句指行步之姿態。(2)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第90頁。
于第87簡注釋說:
蟡=它=:《毛詩》作“委委佗佗”。簡文此句又見《羔羊》。“蟡”,從“蟲”,“為”聲,《說文》“逶”之或體。“蟡=它=”,有重文符號,《魯詩》作“袆袆它它”,《韓詩》作“逶迤”。“蟡它”“委佗”,即“逶迤”,聯綿詞,行走之貌。簡文當從于省吾說,讀為“逶迤逶迤”(參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第一二至一三頁)。(3)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第130頁。
也就是說,原整理者將此字隸定為“蟡”,字形分析成從“蟲”“為”聲。
如果僅從字形出發進行嚴格隸定,這種處理方式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如果從古文字形體演變的角度進行分析,就會發現“蟡”字當是一個由于形體割裂訛變而產生的分化字,直接隸定為“蟡”其實并不是十分妥當。
《說文》:“逶,逶迤,衺去之皃。從辵、委聲。蟡,或從蟲、為。”即“蟡”字在《說文》中沒有單列字頭,而是作為“逶”字之或體出現。清人王筠認為《說文》以“逶”“蟡”為一字不可信,他在《說文釋例》中說:

王筠認為見于《說文》的“蟡”字是后人所增,據小徐本《說文》原無“蟡”字來看,《說文》原本并沒有這個字;“蟡”字的形體,也是后世因“逶迤”詞形有作“蜲蛇”者,故類化添加“蟲”旁而成。現在根據安大簡《詩經》來看,“蟡”字形在戰國簡中已經出現,且正好對應今傳本《詩經》“逶迤(委蛇)”的“逶(委)”字,可見《說文》以“逶”“蟡”為一字之說自有所本,許慎應當是見到過典籍文獻中以“蟡”為“逶”的用字現象,故將“蟡”字作為“逶”之或體。王筠認為“蟡”字是后人所增的看法是不對的。

二、“蟡”字的形體來源蠡測
“蟡”字,又見于傳世文獻《管子·水地》:“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虵(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6)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915頁。這段文字事涉玄虛,蟡似是隨文造字,當與戰國古文字材料中所見的“蟡”字關系不大。后世字書如《玉篇》等多引《管子》此文“似蛇”云云以釋“蟡”字,很可能只是單純的因襲舊文,不足采信。我們如此推測,是有較為充分的證據的,具體詳見下文。
大徐本《說文》將“蟡”字作為“逶”字的或體,而沒有單列字頭,是不是許慎由于疏忽而漏收呢?我們認為,實際情況應該不是這樣的。具體說來,“蟡”字其實當是大約戰國時期由“為”字形體割裂訛變而分化出來的一個古文字形,原本并不存在;“蟡”字形的產生,當是古人出于異體分工的需求,讓其分擔“為”字部分表義功能的結果。要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先從“為”字的古文字形體演變過程談起。
“為”字,最早見于甲骨文,寫作從又、從象,會以手役象以助勞其事,即作為之意(7)季旭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第194頁。。甲骨文的“為”字,有一種將大象的尾部特別突出表現寫成分叉狀的字形,如:



到金文階段,“為”字的這種寫法繼續保留下來,如:



















我們知道,楚系簡牘中所見的“象”字,有寫成省去身體部分的筆畫,只保留頭部象鼻形和下部尾巴形筆畫(多寫作二重分叉狀)的寫法,如:





安大簡《詩經》中的“象”字,還有將身體部分的筆畫與尾巴形筆畫近乎重合在一起的寫法,如:



尤其是第44簡的字形,如果沒有其他的“象”字形作參照,下部的筆畫幾乎分不清究竟是大象身體部分的筆畫還是尾巴部分的筆畫。若是古人書寫之時稍有草率,省略掉左上部的一撇筆,則就與上引第31簡“蟡”字形右部的寫法差不多了。

以上列舉的字形中所見的繁復寫法的“象”字,下部分叉狀的尾巴有的寫成兩重,有的寫成一重。可以設想,在戰國文字系統中,如果“為”字所從的“象”寫成上舉楚簡中所見的那種省去身體部分的筆畫,只保留頭部象鼻形和下部的分叉狀尾巴形筆畫,同時分叉狀尾巴形僅寫成一重,則就會出現如下字形:





綜上可見,在戰國楚簡文字中,將分叉狀尾巴形的筆畫割裂出來,寫成類似古文字“蟲”字旁的現象是很常見的。此種訛變現象正可以與戰國文字中將“為”字所從的大象之分叉狀尾部的筆畫割裂出來隸定成“蟲”旁,從而將字釋為“蟡”進行類比。
三、《說文》視“蟡”為“逶”字或體原因之推測
根據以上所列舉的現象我們可以確信,戰國楚系簡帛文字中那些所謂的“蟡”字,原本就是“為”字形,下部所謂的“蟲”旁其實是表示大象分叉狀尾部的筆畫,根本就不需要隸定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許慎在編纂《說文解字》之時沒有將“蟡”字單列字頭了。因為到了東漢時期,許慎當時所能見到的典籍文獻大都應當屬于今文經學系統的文本,其中大概根本就不存在出現于戰國古文系統的“蟡”字。追根溯源,戰國古文中所見的“蟡”字形,其實都應當是“為”字形割裂訛變而來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許慎在《說文》中沒有把“蟡”字單獨列為字頭,顯然是有道理的。

四、結 語
綜上所述,安大簡《詩經》中所謂的“蟡”字,其實是“為”的后起分化字,其所從的“蟲”旁其實是“為”字形中表示大象分叉狀尾部的筆畫割裂訛變而成的,可以直接隸定成“為”。戰國文字材料中,“蟡”字形已經分化出來,分擔了其所從出的母字“為”的部分表義功能,如讀為“化”、用為“逶”若“委”等。但這種分化進行得并不徹底,最終“蟡”沒有成為富有生命力的通行字進入秦漢時期的文字書寫系統中去。隨著秦朝“書同文”政策的推行,作為戰國古文寫法的“蟡”字被廢棄,只保留在戰國古文系統的文本中。許慎在編纂《說文》時,當是根據古文系統的典籍文獻里類似安大簡《詩經》中用“蟡”為“逶”的現象,將“蟡”字看作“逶”之或體,而沒有將“蟡”字單列字頭,自有其道理。端賴安大簡《詩經》的出土,為我們重新認識“蟡”字的形體來源及其與“逶”字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條件。
ATextualAnalysisoftheAncientCharacter“Gui(蟡)”inTheBookofSongsRecordedonBambooSlip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CollectedbyAnhuiUniversity
HOUNaifeng
Abstract: In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s written as “Gui(蟡)”.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hree characters written as “Gui(蟡)” should be directly assigned to “Wei(為)” as its later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s. In the material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haracter “Gui(蟡)” has been differentiated, sharing part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mother character” of “Wei(為)”. It is thereby understandable that Xu Shen regarded “Gui(蟡)” as a variant of “Wei(逶)”inOriginofChineseCharacterswithout listing “Gui(蟡)” as a separate Chinese character.
Keywords: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Gui(蟡); Wei(為);Wei(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