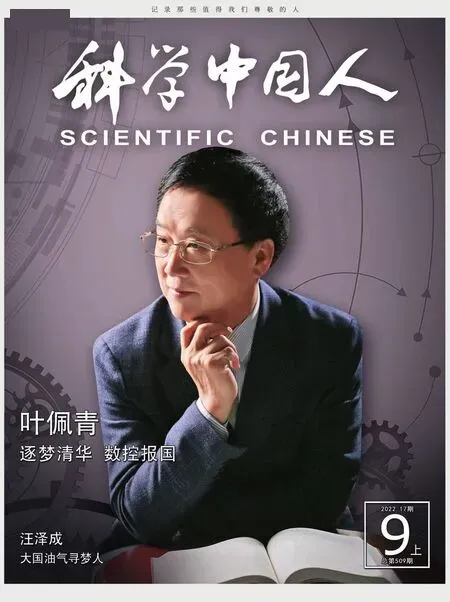打造天地信息走廊
——記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五院西安分院副院長李立
吳應清 李文博

李立作為陜西省第十三屆人大代表參加省人大會議
衛星的數據要實現高速率獲取和傳輸,就不能忽視其中很關鍵的有效載荷——數傳分系統。數傳分系統即數據處理與傳輸分系統。它通過數據處理器接收相機圖像信息,完成圖像數據壓縮、格式編排后進行直傳、存儲或回放,再通過高速調制與功率放大,由數傳天線跟蹤地面站,地面接收射頻信號后經過一系列的信號處理,還原星上圖像后進行分發使用。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五院西安分院(以下簡稱“西安分院”)是我國飛行器有效載荷研制的“國家隊”,更是衛星高速數傳技術研究的開拓者與主力軍。自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在返回式衛星上首次搭載傳輸型C C D電視遙感系統至今,傳輸型遙感衛星就逐步從試驗進入了實用階段。
作為西安分院的副院長,李立自1998年大學畢業進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五院504研究所(現西安分院)工作至今,不僅見證了西安分院在有效載荷技術攻關與突破中創造的多個第一,以及其為我國航天事業和國民經濟建設作出的突出貢獻;領銜重大航天工程項目、提出國際領先的技術方案、攻克重重的技術困難,李立及其研究團隊更通過所做工作成功推動了我國空間數據傳輸領域相關技術的迭代更新,不斷引領著星載數據傳輸技術再創新的輝煌。
從單機研制到系統研制
在西安出生和成長,家人在504所工作,李立周圍不乏做空間通信的人。從小的耳濡目染,讓李立在高考時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通信工程專業填在了志愿表的第一欄。
20世紀90年代,國家通信事業發展迅速,從通信工具的變化能窺見一些跡象。李立入學的1994年,大家用固定電話與親戚、朋友通信,后來有了B P尋呼機、“大哥大”手提電話,接近2000年時有了手機。在此背景下,高校里通信工程專業成為熱門專業,當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為此專業設了3個班級,一個班容納135個人。
樊昌信教授、詹道庸教授、張厥盛教授、吳成柯教授這些以前只在書上見過大名的學者面對面為自己傳授知識、答疑解惑,讓李立收獲頗大。1998年做畢業設計,李立找到張厥盛教授做指導,除了教會他如何看英文材料、如何查資料、如何找典型電路,張教授并未過多干涉他,給了他充分探索的自由,畢業時李立完成了一個不錯的設計。
通過畢業設計,李立發現了自學的重要性。“以前認為必須上這門課,才學相關知識,后來覺得只要是我們大方向類的,有書自己就要找來學。一本書花1個月看完,跟同學交流,再跟老師交流,知識也就掌握了。我覺得對科技工作者來說,從被動到主動的學習很必要,可以早早建立對科研的自信。”李立說。
畢業在即,懷揣對航天事業的熱愛,他來到504所數據傳輸技術研究室工作。從基層做起,憑著過硬的工作能力和技術水平,李立挑起了一個個重任。
早期的返回式衛星,在完成攝影任務后,裝有相機膠片的片盒會隨返回艙一起在預定地區回收,送回地面進行沖洗和分析。1999年10月14日,剛畢業到504所工作不久的李立趕上了中國第一顆傳輸型對地觀測衛星——“中巴地球資源衛星01星”的發射,衛星在星上對圖像進行處理,通過微波把圖像數據傳回地面,省去了膠片回收的步驟。504所負責“中巴地球資源衛星01星”相機與數據傳輸分系統的研發,李立當時在地面站負責數據接收和處理。
“說實話,我當時是兩眼一抹黑,一個人推著車子拉著所有的設備,試著搭建系統,心里盼著有人可以教我,突然發現要拜眾人為師。”李立說。有同事建議他把任務書從資料室全借來看一遍,李立照做了。看完后有許多不懂的地方,幸運的是所里有很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的老專家,編過教材,治學嚴謹,李立拿著任務書去找他們請教,就這樣慢慢摸索著完成了系統的搭建。
為讓年輕同志知識面廣一些,當時數據傳輸技術研究室陳泓主任制定了個制度,新同志的第一年實習期,每3個月換1個方向。先做圖像編碼,再做頻率源本振,又做調制器,跟著3個老師,李立將數傳分系統里最核心的3個方向都了解了一遍,同時三四個月換1次辦公室,跟室里的同志們也都能熟悉起來。
入職504所后,李立相繼參與了國家“資源一號”和“資源二號”衛星數傳系統的研制,因為在每個方向都干過,他的工作做得得心應手。在大項目中鍛煉,李立迅速成長起來。2003年,他被任命為研究室副主任,開始獨立承擔某小型光學遙感衛星數傳分系統的研制工作,還負責“嫦娥一號”衛星數傳分系統的論證工作,度過了一段雖辛苦卻充實的時光。
之前李立是看別人寫任務書,獨立承擔研制工作后,由于用戶需求變了,要自己設計新系統。當時分類元器件向大規模集成電路轉變已成為趨勢,包括接口、電路在內的所有東西都需要小型化。查資料、翻看英文手冊,為的是能重新制定一套方案、標準。為盡快將任務書寫出來,李立加班加點,廢寢忘食。
“寫任務書就是一個設計的過程,就是告訴單機設計師怎么按照你的思路、你的想法來。要對他提要求,就得把設計思路說得很清楚,這樣設計師才知道如何去實現。”李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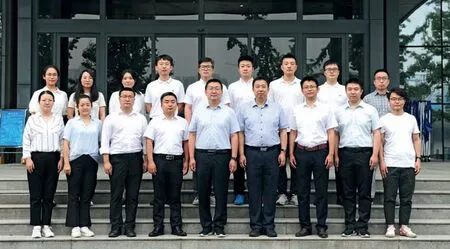
西安分院微波光子新型載荷創新團隊
當時困難很多,如何在舊系統的基礎上兼顧新技術,就是其中一個。查找問題出在哪兒,是另外一個。“有時兩個禮拜也找不到問題所在,但一步步去找,逐步割離問題,最后總能找到癥結所在。那時,我很樂意一兩個同志把所有的設備擺滿桌子從頭連到尾,拿著示波器一點一點看。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法,因為大部分工作我都熟悉,每一個單機的任務都是我定的要求,我知道每個地方應該是什么樣子。”李立說。
而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大家在理念上的分歧,經常是李立認為應該這樣干,但老同志卻認為應該那樣干。“今天按照老同志的思路改,明天按照我的思路改。但這個方法不行,因為做的是新事情,必須轉換思路,大家彼此爭執但又相互理解,創新就是這樣。”李立說。
之前圖像壓縮是基于行的壓縮,從研制某小型光學遙感衛星開始,圖像壓縮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基于行的DPCM變為基于塊圖像的小波變換壓縮,32行或者64行做一次壓縮。基于塊的文件,如果還拿示波器查找錯誤,顯然行不通。面對新情況,李立提出用數據采集卡一次將數據進行采集,檢查數據包有無差錯。“這個方法后來成了標準文件,成了測試依據。這都是一點一點摸索的結果,因為設計思想變了,方法也要變,讓方法更加優化,才能與時俱進。”
原來參與項目時跟著老同志們干就行,成為項目負責人或主任設計師時要總攬全局,面對的情況更復雜。對一些沒接觸過的事情應該怎么處理?李立心里沒底。另外負責“遙感衛星二號”“嫦娥一號”數傳分系統的研制任務讓他體會到了重大工程帶來的壓力。“嫦娥一號”起初定的是2007年上半年發射,但為了慎重起見,所有人都在做復查,壓力很大。
心里沒底,壓力巨大,老同志們的指點和鼓勁給予初擔重任的李立信心與力量。張有峰研究員曾是“資源二號”衛星數傳系統負責人,也是指導他的師父之一,當時他就對李立說:“年輕人要有信心,一定能干好。”“他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包括在一些事情上給我的指點,對我幫助很大。”李立說。
曾是“資源二號”衛星總師的葉培建院士,對年輕同志特別關心。他人很和藹,同時很嚴謹,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人。他負責了嫦娥系列衛星,以及月球中繼衛星“鵲橋”、火星探測等多項開創性的工作,他看得很遠。從葉培建院士身上李立學到,在做好手中工作的時候,還要關心新技術,關心技術未來的發展。
前輩的鼓勵與引導,加之個人的努力,初挑重擔,李立就以不俗的表現圓滿完成了項目攻關任務。“遙感衛星二號”項目2003年開始論證,2004年開始攻關,2007年5月25日成功發射,研制只用了3年時間,李立負責的第一個項目就順利完成。“遙感衛星二號”作為第二代數傳分系統的首發星在太空中熠熠生輝。“嫦娥一號”項目也同樣只用了3年多時間就順利完成。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號”成功發射,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具有深空探測能力的國家之一。
構建新一代空間數傳系統
通過承擔項目,李立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認可,2007年下半年他成了數傳室主任,2008年數傳室與微波遙感室合并成立微波遙感與數傳技術研究所,當時才32歲的李立成了西安分院最年輕的所長。
2007年,數傳系統剛迭代到第二代,李立就帶領團隊開始了第三代數傳系統的謀劃。5年一迭代,國際上大都是這樣的周期。當時美國的“Worldview-1商業遙感衛星”已經發射成功,分辨率達到0.5米,數傳能力達到800兆,遠超過他們研發的水平。
不停查材料,與天線室、微波室合作,李立想盡可能多地將所里自身的潛力挖掘出來。在此期間,與國外同行的交流,讓李立的想法更超前、更大膽,他也更敢放手去做了,新一代的數傳系統已在構想之中。2011年他參加了國際空間數據系統咨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Space Data Systems,C C S D S)在德國的一次會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在射頻與調制小組討論時,李立被美國和法國科學家提出的編碼調制標準草案所吸引。之前他也想過做同樣的事,但國內環境對新事物很保守,如果沒有相關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做參考,要說服別人做創新的挑戰困難重重。參加這次會議為李立打開了一扇窗,在會上他看到了國外的最新研究草案,更堅定了創新發展的信心。李立開始堅定地推進相關預研課題的立項。
2009年高分辨率對地觀測重大專項“星地數據處理與傳輸總體技術”項目立項,2010年李立入選國家高分辨率對地觀測重大專項專家委員會天基組專家,負責星地數傳大總體的論證工作,與高分專項緊密結合規劃我國新一代數傳分系統。
當時天基部分有十多顆星,最初規劃都用X頻段,而國外正在做K a頻段的研究工作,李立力推在某光學和雷達等衛星上攻關研制K a頻段系統。“我們不是純粹只做星上數傳載荷,而是負責整個星地數傳大系統的設計工作。”低軌衛星是90多分鐘繞地球一圈,一天繞約14圈,14圈中可見弧段只有四五圈,中國有5個地面站,24小時最多有1個半小時能接收到數據。“高分辨遙感衛星圖像數據量太大了,1個半小時根本不夠呀。”但當時團隊也計算過,因為接收的數據率特別高,X頻段只有375兆的帶寬,極化復用后,帶寬也只有750兆,遠遠不能滿足數據傳輸的需求。而K a頻段有1500兆帶寬,從375兆到1500兆,帶寬本身就增加了4倍多,再做雙極化,傳輸的數據率就可以高很多。
基于此種情況,李立當時提出了開發對地與中繼一體的K a頻段數傳系統,并提出了建設極地接收站的發展建議。因為如在南極和北極建站,幾乎每一圈數據都可以落地,通過通信衛星就傳回國內,這樣可接收到的數據量就大幅提升了。這是一個重大的技術進步,它直接推動了國家建設K a頻段接收站的步伐,現在北極站已經建成,南極站的建設也在計劃中,國內地面站都新建了Ka頻段的接收天線。
回顧十多年攻關路,并非一帆風順,尤其前期確定技術方案,1年中有1/3時間李立都在北京與國內的專家們進行討論,一次次修正思路,一次次修改技術方案。當最后形成的接口、協議都成了國家標準時,李立真正體會到雖艱難卻快樂的感覺。
2020年國家高分辨率對地觀測重大專項天基系統圓滿完成,西安分院為我國天地數據傳輸能力的大幅提升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項目攻關中,李立帶領團隊開展了高分星地數傳系統的頂層論證工作,提出并實施了多光譜譜間相關壓縮、在軌數據處理技術等多項關鍵技術,處理與傳輸能力有了質的飛躍,構建了我國新一代高速天地一體化的數傳系統,為我國數據處理與傳輸領域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高分十一號”的成功發射,K a頻段數傳系統在軌圓滿成功,傳輸能力提高3倍以上,傳輸頻帶效率提高1.5倍,標志著我國新一代數傳系統躋身國際領先行列。
“如果說以前我們是跟著國外跑,現在可以這樣說,在K a頻段或者在自適應V C M數據傳輸能力上,我們已經與國外比肩前行,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越了他們。”談起這些,李立不無自豪。
天地一體融合創新
從單機研制到系統研制,從型號論證到新技術開發和產品化,回顧李立到504所工作至今的科研經歷,他走過了這樣一條路。腳踏實地前行,李立走出的每一步都鏗鏘有力。
1998年至2004年,李立突破了300 M b ps高速編碼調制器和解調譯碼器等技術難關,研發的相關產品已應用于資源、海洋等多個型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2004年至2010年,他作為“遙感衛星二號”系列和“天繪一號”系列等衛星數傳分系統技術負責人,從事分系統總體設計工作,帶領技術團隊突破了基于小波的高效圖像壓縮技術、X頻段微波直接調制技術、多路數據AOS編碼等多項關鍵技術,完成了遙感衛星數傳系統向第二代的技術跨越。2012年至2015年,作為某光學遙感衛星副總設計師,李立提出并突破了高速圖像壓縮、450MbpsQPSK調制、可動點波束數傳天線等關鍵技術,并實現了在軌首飛成功。第三代數傳系統通用型譜產品已廣泛應用于資源、高分等后續衛星,其2×450Mbps數傳系統整體技術水平已達到和超越了國外在軌的商業衛星。楊士中院士作為我國空間遙感數傳領域的開創者,對研究團隊所做的工作也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并給予了指導。
由于成果意義重大,李立參與或主持的相關項目先后獲得國防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軍隊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國防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雖所獲成果、榮譽眾多,但李立并不會因滿足于現狀而止步不前。早在2008年任職微波遙感與數傳技術研究所所長時,他為團隊提出了“研制一代,應用一代,探索一代”的研究模式。眼光一直向前,是他從老一輩科學家身上繼承的寶貴財富,也是他對科研本質的深刻認識。

李立(右二)在重點實驗室與楊士中院士(左二)交流
2016年11月,李立升任西安分院副院長后,他的站位更高了。作為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衛星通信領域技術帶頭人,他帶領西安分院相關團隊,系統性地開展高通量通信衛星載荷、微波光子轉發器等通信系統設計,有效降低了寬帶轉發器的重量、功耗和體積,實現寬帶衛星的容量提升和靈活應用。對標國際先進水平,他指導了Q/V頻段載荷、多波束天線、小型化激光終端和雷達系統等核心產品的先期研制,全面提升了西安分院天地一體化的設計、仿真、驗證與應用能力。同時,在西安分院的空間微波技術國家級重點實驗室,李立將激光與微波的交叉融合作為重點研究方向,著力打造了一支基于微波光子的空間有效載荷創新團隊。他希望這支擁有國際視野的團隊能為高通量通信衛星載荷的研發以及空間激光、微波高速數據傳輸與組網等領域作一些貢獻。2020年,李立入選國防科技高層次人才;2021年,當選中國通信學會會士。同年,他所帶領的微波光子先進空間載荷團隊入選集團公司科技創新團隊。
李立認為,空間領域的數據傳輸終究要邁向更高頻段,結合中國自身技術基礎,瞄準大容量、高速率、高性能方向,星地傳輸領域激光與微波的融合發展是必然的趨勢;對于星間的高速組網通信而言,激光則是一個相當有潛力的選擇。“另外,我覺得還應該更加注重星地大系統的打造,空間段和地面段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服務于國防和國民經濟。如何融合不割裂?如何在更高的層次上來系統性地解決問題?我們創新的步伐與思路每時每刻都需要被拓寬。”李立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