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最剛烈的勇士,有最柔軟的心腸
王京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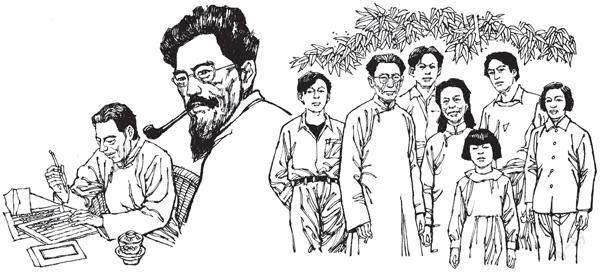
著名油畫家、91 歲的聞立鵬一生中辦過無數次畫展,但將自己的畫作與父親聞一多的藝術作品一同展出,還是頭一回。
在今年4 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紅燭頌:聞一多、聞立鵬藝術作品展”上,通過照片、信札和聞立鵬的畫作與講述,人們看到了“父親聞一多”的形象,并驚訝地發現:最剛烈的勇士,原來有一副最柔軟的心腸。
家 書
“ 這一星期內, 可真難為了我!在家里做父親,還要做母親。小弟閉口不言,只時來我身邊親親,大妹就毫不客氣,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發脾氣,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會說罷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邊時來一陣炮聲、飛機聲,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沒有心思,看書也沒有心思,拔草也沒有心思……你不曉得男人做起母親來,比女人的心還要軟。”1937 年7 月15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周后,聞一多在給妻子高孝貞的信中如此感嘆。
半個月前,高孝貞帶著長子聞立鶴、次子聞立雕回湖北老家省親,聞一多同三個更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清華園的家中。信里的“小弟”,就是聞一多的三子聞立鵬。
平靜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碎。這一年的10 月,聞一多獨自離家,前往長沙,擔任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的教授。此后,近一年時間,他與妻子兒女分隔兩地,只能借一封封家書傾訴思念。
聞一多是個戀家的人,常常剛一離家,就翹首期盼起親人的來信。赴美第一年年底,聞一多的第一個孩子、女兒聞立瑛出生。家人沒有及時告知聞一多,令他很不滿,給父母寫信說:“孝貞分娩,家中也無信來,只到上回父親才在信紙角上綴了幾個小字說我女名某,這就完了。大約要是生了一個男孩,便是打電報來也值得罷?我老實講,我得一女,正如我愿,我很得意。我將來要將我的女兒教育出來給大家做個榜樣……我的希望與快樂將來就在此女身上。”
遺憾的是,4 年后,聞立瑛因病早夭。
1937 年10 月23 日, 聞一多在深夜抵達長沙,當晚立即給妻子寫信,對家里的5 個孩子一一關心。
10 月26 日,他又給妻子寫信,抱怨自己出門快一周仍沒收到家信:“小小妹病究竟如何?我日夜掛念。鶴雕都能寫信,小弟大妹也能畫圖寫字,何不寄點來給我看看?”
10 月27 日,又修家書一封。
4 天后的11 月1 日,又寫信給妻子:“我現在哀求你速來一信。請你可憐我的心并非鐵打的。”
11 月2 日,發出新一封信前,他收到妻子和長子的信,還有幼子聞立鵬和大女兒聞銘的畫,十分喜歡,于是給妻子回信:“家中的一切事,不管大小,或是你們心里想的事,都可以告訴我,愈詳細愈好。”
孩子們的每封信都被父親鄭重其事地對待。他夸長子立鶴的信寫得好,拿去給朋友們看,賺來一圈贊美。兒子們的信寫得比從前更通順、字跡也更整齊了,他高興得“今天非多吃一碗飯不可”!還大力夸贊——“你們的信稿究竟有人改過沒有?像這樣進步下去,如何是好!”
聞一多是那種不輕易否定孩子的父親。他雖然一直憂心次子功課不好,卻又特地在給妻子的信里強調:“雕兒玩心大,且脾氣乖張,但絕非廢材,務當遇事勸導,不可怒罵。”
1938 年2 月,戰爭逼近湖南,長沙臨時大學再遷昆明。
出發前,他在家書中提及上回離家時與兒女們道別的情形:“那天動身的時候,他們都睡著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們,說我走了,恐怕他們第二天起來,不看見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們一一叫醒,跟他說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話沒有說完,喉嚨管硬了,說不出來,所以大妹沒有叫,實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門,現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轎子,我就哭了……四十歲的人,何以這樣心軟。”
背 影
1938 年8 月底,聞一多一家團聚,在昆明住了8 年,這是聞立鵬與父親共度最久的一段光陰。
“印象最深的畫面,是父親的背影。”聞立鵬說,“那時條件困難,一間屋子既是我父親的書房、會客室,又擠著我和妹妹的床,還有我父母的床。有時我夜里醒來,就看見父親還披著衣服、弓著背,坐在桌前刻圖章。”
1944 年, 戰時物價暴漲,聞一多的月薪僅夠一家人勉強支持10 天左右。書籍衣物變賣殆盡,他去校外兼課、寫文章、做報告,為節省炭火,在臘月帶著全家高高低低的孩子們去小河邊洗臉……直到聞一多在朋友建議下公開掛牌為人刻印,家中狀況才有所改善。
但在最勞碌的日子里,他依然是那個幾乎從不對子女發火的好脾氣父親。
聞立鵬記得,有一回,二哥聞立雕從學校拿回一塊鈉,放入盛水的茶壺,試著按課堂上教的鈉加水產生氫氣的原理制造氫氣,結果引起爆炸,傷到了圍觀的大妹。
“我們都嚇壞了,沒想到父親并沒責備我們,只是借此講了個道理,說了句英文諺語:A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thing。意思是,一知半解是最危險的事。”聞立鵬說。
聞一多會鄭重對待年幼兒女的書信,也會鄭重傾聽孩子們的意見。
有一回,聞一多的小女兒聞惠羽在家里鬧脾氣,被鬧得心煩、無法工作的聞一多一反常態地打了女兒兩下,結果被兒子聞立雕質問:“你平時天天在外面講民主,怎么在家里動手打人!這叫什么民主?”
“今天是我不對。”聞一多向兒女承認錯誤,“希望你們以后不要這樣對待你們的孩子。”
1945 年,通脹嚴重,聞一多提高了自己治印的費用,被長子聞立鶴責問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沉默良久,說:“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聞立雕曾在文章中寫過,父親是寓教育于日常生活,身教多于言教,熏陶和潛移默化多于灌輸。“例如,他要求我們每個孩子都要好好讀書,而他自己只要沒有別的事,放下碗筷就坐到書桌前,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受他的影響,我們自然也就形成了看書寫字的習慣。”
父 子
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宣告解散,師生分批返回平津。機票緊張,聞立鵬與二哥聞立雕先行飛往重慶,在那里等待與家人會合,再同返北平。
1946 年6 月29 日, 聞一多在百忙之中給兩個兒子寫信,信尾說:“我這幾天特別忙,一半也是要把應辦的事早些辦完,以便早些動身。小弟的皮鞋買了沒有?如未買,應早買,因為北平更貴。”
沒人料到,這會是聞一多的最后一封家書。
半個月后,7 月15 日, 聞一多在李公樸追悼大會上拍案而起,即席發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講演》。當天下午,他在回家途中遭國民黨特務殺害,與其同行的長子聞立鶴撲在聞一多身上試圖保護父親,身中五彈,死里逃生。
聞一多生前沒給子女們立下什么家規家訓,但聞家幾兄妹似乎都有些共同的脾性和不言自明的準繩。“要踏踏實實做人。做個真正的人,大寫的人。”聞立鵬將重音落在“人”字上,“始終堅信真理和正義,向好的靠攏,向好的學習。”
(王傳生摘自2022 年6 月17 日《新華每日電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