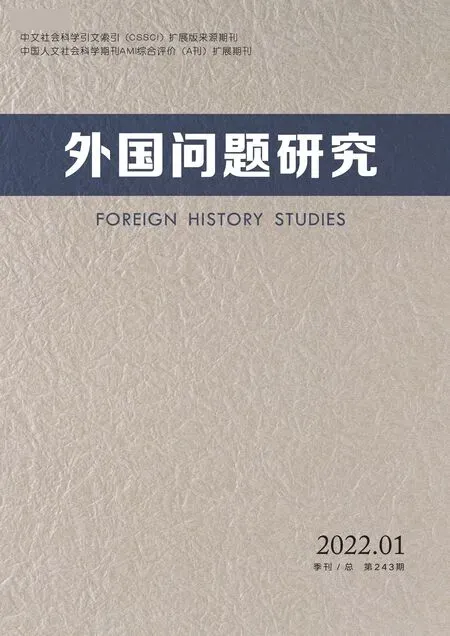“丸山模式”的東亞回響
——有關(guān)樸忠錫、韓東育的相關(guān)研究
王明兵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丸山真男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不可繞行的重要人物之一。考察目前學界對其所構(gòu)筑的學術(shù)典范(“丸山模式”)和開創(chuàng)的學術(shù)流派(“丸山學派”)的批評及其爭論,便會發(fā)現(xiàn),即便是丸山的批評者所采取的理論視角、話語形態(tài)和批評方法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丸山真男的學術(shù)影響。(1)關(guān)于丸山真男學術(shù)研究史的梳理,可參見:安孫子誠男:《丸山真男批評の諸相》,《千葉大學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33)》2000年;都築勉:《丸山真男論の現(xiàn)在》,《政治思想研究》2000年Inaugural巻;陳都文:《丸山真男論的諸相——日本學界對丸山真男的最新述評》,《世界哲學》2005年第5期;魏靈學、國薇:《中日兩國對丸山真男的研究綜述》,《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11期;苅部直:《丸山真男研究の新たな動向》,《アステイオン(92)》2020年;夫鐘閔:《丸山真男論を捉え直す:國民國家の黃昏を迎えて》,《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這一現(xiàn)象或可表明,迄今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尚未真正走出“丸山時代”或可以說處于“后丸山時代”。
雖然丸山真男主要致力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及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但學界對丸山真男及其“丸山模式”的討論,不應僅局限于丸山和日本思想史領域。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丸山以日本政治思想史為研究對象所采取的理論視野、闡釋方式和目標指向及其提煉和抽繹出的“普遍性”(“近代性”)和“個體性”(“日本性”)(2)盡管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使用了“特殊性”,但他在晚年對其進行了反思,認為使用“特殊性”易導致“日本特殊論”的誤解,故以“個別性”加以修正。參見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zhí)拗低音》,《丸山真男集》第12巻,東京:巖波書店,1996年,第128—129頁。的方法和取向具有一種可被移植、模仿的“范式(Paradigm)”意義。在此借用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中所提出的“范式”,乃是基于學界對丸山學術(shù)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分析和評價,筆者以為“丸山模式”具有“范式”所涵蓋的四大基本特征:(3)參見劉梁劍:《庫恩范式的詮釋學意蘊和默會維度》,《江海學刊》2004年第3期。(1)共享性:具有“地平線”(4)1999年度的日本思想學會以“丸山思想史學的地平線”為核心議題,對丸山的學術(shù)思想、研究方法及其影響進行了多方面的研討。參見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論》,東京:ぺりかん社,2002年,第1—405頁。之奠基性的丸山思想史學對戰(zhàn)后日本的學術(shù)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有起始和承重意義。(2)約束性:盡管丸山并非一個完全躲在書齋中的學者,但即便他參與一定的社會活動,也仍然恪守學術(shù)原則,以一個學者、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和良知進行批判性思考和發(fā)聲。(3)開放性:丸山所提出的問題、引發(fā)的爭論仍是“后丸山真男時代”所面對和力圖要解決的課題(比如東西方關(guān)系、帝國主義體系、太平洋戰(zhàn)爭、市民社會等),而且其還超越于日本時空之域?qū)|亞甚至世界都深具啟發(fā)意義和警示價值。(4)默會性:雖然丸山的思想脈絡大體上保持了一致性,觀點也很明晰,但他借助意象和形象思維來表達其最具有標識性的“原型·古層·執(zhí)拗低音論”卻陷入了一種“所知而難以言傳”的境地。這四個方面的特征,并非完全孤立或界限明確,而是前后有引申、相互有重疊、彼此有交涉,以一種交錯循環(huán)和共通論證的方式映射出丸山學術(shù)思想和理論方法的樣貌與特征。
韓國和日本同屬于中華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的東亞范圍,前近代共享以中華經(jīng)典為核心的知識體系和價值系統(tǒng)。雖然在近代受西方?jīng)_擊,各國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但在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層面仍受制于歷史傳統(tǒng)、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的潛在支配,故而其發(fā)展道路呈現(xiàn)出一種“同中有異”而又“異中有同”的有趣現(xiàn)象。對其的解釋,仁智互見。關(guān)于丸山在對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所提煉而成的“個體性”(“日本性—原型論”)和“普遍性”(“近代性”)對朝韓、中國等東亞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啟發(fā)意義和價值的討論,不可謂不少。但其中,無偶有獨的是,韓國學者樸忠錫受業(yè)于丸山真男且以丸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為“模型”所撰著的《韓國政治思想史》乃是對“丸山模式”的一次較為系統(tǒng)性的擬寫和嘗試,(5)樸忠錫曾于1963—1972年在東京大學師從丸山真男,歷經(jīng)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學習,最后以《李朝後期における政治思想の展開——特に近世実學派の政治社會と朱子學思想》(東京大學博士論文甲第2941號)獲得博士學位。氏著《韓國政治思想史》(飯?zhí)锾┤O(jiān)修, 井上厚史、石田徹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16年)是其在博士論文基礎上補訂而成。據(jù)其自述,他的博士論文及該著汲取了丸山真男“古層論”和近代化論的理論和方法,也受到了丸山的肯定;同時,他也頗自信和自豪于以其師丸山真男的理論和方法來解釋和重構(gòu)韓國思想史的問題點和發(fā)展脈絡,參見樸忠錫:《丸山先生を師として——私の學問の歩み》,《丸山真男手帖(24)》(東京:丸山真男手帖の會)2003年1月號;《丸山真男の社會科學と韓國》,《丸山真男手帖(24)》(東京:丸山真男手帖の會)2014年8月號。關(guān)于韓國學界對樸忠錫與丸山學術(shù)及其韓國思想史研究的評論,可參見金錫根:《韓國における丸山真男の思想·學問の受けとめられ方》,《東京女子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丸山真男記念比較思想研究センター報告(別冊)》2017年。尤值得關(guān)注。由于朝韓、日本和中國這樣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東亞關(guān)系實態(tài),任何一方的研究都會或多或少地牽涉到他方,故通過對樸忠錫借鑒丸山理論對韓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撰寫的考察,希望對“丸山模式”作為一種學術(shù)范式和理論方法在東亞思想史中的有效利用、自身缺陷及其改進可能等方面獲得一些經(jīng)驗教訓。同時,參酌新近中國學界、特別是韓東育對丸山的研究,以期能呈現(xiàn)對丸山學術(shù)思想研究的一些新動向,或可為“丸山學”以及東亞研究開拓出一個新的境域。
一、“近代主義—日本主義”框架下的 “檀君朝鮮”與“朝鮮實學”
黑住真指出丸山的學術(shù)和思想立基于“近代主義—日本主義”框架,其“在與西方/近代的比較中,始終如一地帶有日本的感覺,‘古層論’,便是這一思想延長線上的命題。”(6)黒住真:《複數(shù)性の日本思想》,東京:ぺりかん社,2006年,第41頁。而且,丸山的“原型論”也彰顯出日本“民族主義”的傾向。(7)參見韓東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論”與“日本主義”》,《讀書》2002年第10期。
盡管丸山真男在其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并沒有論及“原型論”,但從其萌發(fā)到提出且不斷地修正和完善也經(jīng)歷了數(shù)年的時間,大致可以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原型”而“古層”至“執(zhí)拗低音”漸次展開。(8)參見水林彪:《丸山古代思想史をめぐって》,《日本思想史學(32)》2000年。由于“原型”源自精神分析的說法、“古層”系借用地質(zhì)學的概念、“執(zhí)拗低音”取自聲樂學的專名,故從概念界定的角度而論,這一做法并不是一個能夠揭示對象本質(zhì)屬性的思維形式,內(nèi)涵不詳,外延亦模糊,如果對其沒有更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就很難把握其意象和擬物的明確所指。根據(jù)丸山真男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場合的發(fā)言,大體可作如是之概觀:日本思想史乃是不斷接受外來思想并對其加以修正的歷史;不斷接受和舍棄的外來思想和文化在日本人的心理和精神結(jié)構(gòu)中形成了不同的層次,在“新生層”和“古層”相互激蕩而發(fā)生作用的過程中,沉積于最下或最底層者即為“原型”。該“原型”由倫理意識的原型、歷史意識的原型與政治意識的原型三部分構(gòu)成。倫理意識的原型旨在說明日本善惡觀念的靈性或神性來源,歷史意識的原型意在凸顯日本人的現(xiàn)世中心主義觀念,政治意識的原型指明了日本“萬世一系”的皇統(tǒng)神政理念。(9)參見韓東育:《丸山真男“原型論”考辨》,《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而且,這三大“原型”彼此交融,相互疊加,共同發(fā)生作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具體事態(tài)中,表象和側(cè)重亦有差異。不過,丸山“原型論”的目標指向卻是非常明確,那就是要試圖究明:何謂“日本”?日本為什么是這個樣子?——即“日本性”(日本的なもの)。所以為了澄明“日本性”,需要理清“非日本”的東西。
“非日本的東西”,是相對于“日本性”(日本的なもの)而言的。從早期文明形成或文化發(fā)生學的角度觀之,日本文明或文化并不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自發(fā)性特征。所以,就相當程度而言,一部日本思想文化史也即是“外來文化”如何“內(nèi)化”而成為“日本的東西”即“日本性”固化而凸顯的歷史。由于日本在思想文化上“第一哲學”的闕失,(10)參見韓東育:《日本對“他者”的處理模式與“第一哲學”缺失》,《哲學研究》2017年第6期。所以日本需要在能夠標識自我的原始宗教和神話系統(tǒng)中獲得某種話語形態(tài)和文獻支撐。就此,丸山一方面并不否定平行從中國或經(jīng)朝鮮半島傳至日本的儒釋道文化,另一方面極力強調(diào)縱向地從天至地的“神皇”圖式(太陽神—榖靈—皇祖神—天皇)。而且,縱向的“垂直結(jié)構(gòu)”(高天原即天上—葦原中國即地上日本—根國即地下)體系在與橫向的“水平結(jié)構(gòu)”(佛教西方凈土·蓬萊國—出云黃泉國·葦原中國)相爭相合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甚至可以說是居于主導地位。為此,丸山從能代表日本國有文化的《萬葉集》《靈異記》等文學和神話文獻中提煉和萃取“日本性”。正是這些“日本性”要素,不斷將外來文化“內(nèi)化”而成為一以貫之的“日本精神”。(11)參見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zhí)拗低音》,《丸山真男集》第12巻,第136—155頁。
丸山真男“原型論”所依托的史料基本上都來自日本創(chuàng)世神話和神道文獻。由于以宗教和民俗呈現(xiàn)的這些資料和事實既無法證實又難以證偽,故只能通過闡釋來體現(xiàn)出某種可能性。所以,丸山用以凸顯“日本性”的“原型論”論述方式,不可能是一種實證性的學術(shù)形態(tài),只能是一種本質(zhì)主義或化約主義的闡釋學,方法論的啟發(fā)和價值意義遠大于其論本身。
由于樸忠錫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受業(yè)于丸山的近十年時間(1963—1972)恰是丸山“原型論”思考由提出并走向成熟的時期,盡管他在受丸山所指導的博士論文中并沒有展開“原型論”對韓國思想史研究的啟發(fā)和應用,但在其后的《韓國政治思想史》中從歷史貫通性的角度將“原型論”置于韓國思想奠基和起源狀態(tài)的書寫中。“原型論”指向的“日本性”在韓國的歷史文化和思想語境中就轉(zhuǎn)換為“韓國性”的問題。那么如何能凸顯出“韓國性”呢?樸忠錫在汲取丸山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礎上擬定了丸山的“原型—古層”在韓國的歷史文化中是以“檀君朝鮮”之創(chuàng)世神話為主要載體溢脫出“巫性”傳統(tǒng)。這一點,倒是比丸山強調(diào)作為方法的“原型—古層”所指更加明確和具體。丸山的“原型—古層”著力于“為(如何)”,而樸忠錫的“巫性說”旨在說明“是(什么)”。
盡管韓國和日本在地理空間上分屬于不同的類型,但是就思想文化發(fā)展而言,均受中國文化影響,同屬于中華文化圈。不過,在具體層面上,各自呈現(xiàn)出思想文化的獨特性和自我的身份認同。(12)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飯?zhí)锾┤O(jiān)修, 井上厚史、石田徹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16年,第24—25頁。而旨在探求民族思想文化獨特性的丸山的“原型論”不失為一個頗具解釋效力的理論范式。(13)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1頁。樸忠錫利用丸山“原型論”對韓國“原型”即“檀君朝鮮”中的“巫性”的提煉過程,亦與丸山相仿,但側(cè)重于“垂直結(jié)構(gòu)”方面。其從由韓國民族史家所獨自編纂或撰著的作品中選擇朝韓民族的創(chuàng)世和建國神話——“檀君朝鮮”予以論析,認為經(jīng)過“原型—古層”——“天”“生”“化”而使得外來自中國的儒釋道的思想文化以一種“無媒介”的方式“內(nèi)化”在韓國思想文化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韓國的思想文化雖然表現(xiàn)為儒釋道等形態(tài),但根底確有“韓國性”存在。從中國傳至朝鮮半島的儒釋道等文化形態(tài),經(jīng)“古層”這樣一種“轉(zhuǎn)化裝置”處理后,由“附著物”變?yōu)榱恕岸ㄖ铩薄V杂伞案街铩蹦茏優(yōu)椤岸ㄖ铩笔且驗榫哂小绊n國性”的“原型—古層”機制在發(fā)揮作用。在該過程中,“天”“生”“化”展現(xiàn)出了一種具有持續(xù)性的動力效能形態(tài)。在歷史層面上,新羅之始祖樸赫居世、高句麗之始祖朱蒙、百濟之始祖溫祚和“檀君朝鮮”之建國神話體現(xiàn)出“天上世界”與歷史世界連續(xù)性的“合理性”結(jié)構(gòu),而且 “在‘天’‘出’‘卵’(生)‘誕’(生),其基底‘天’‘生’貫穿其中。”(14)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64頁。在現(xiàn)實層面,“生”是最能表征韓國人日常生活基本行為的萬能動詞之一,其特征是混淆了“自然”行為和人的“作為”二者之間的界限。這種表現(xiàn)方式,雖說是韓國社會中的日常語言表現(xiàn)形式,但其卻反映出了植根于韓國歷史且受其文化慣性制約的言語、思考和行動體系特征。(15)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71頁。
“檀君朝鮮”建國神話中蘊含的“巫性”傳統(tǒng)何以成為韓國歷史的起源及如何決定其發(fā)展道路的呢?就此,樸忠錫提煉出五大方面:其一,“天神·桓因—桓雄—檀君”一系的絕對神圣系譜是神政統(tǒng)治的源泉。其二,神性使得檀君統(tǒng)治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其三,檀君既為宗教最高權(quán)威又是現(xiàn)實政治的最高統(tǒng)治者,相對于神而言,是巫;相對于被統(tǒng)治者而言,又為人間的最高權(quán)力主宰者。其四,就政治統(tǒng)治而言,兼具秩序與教化功能。其五,在社會層面體現(xiàn)出既“貪求人世”又“弘益人間”、既追求功利價值又捍衛(wèi)秩序規(guī)范等特征。(16)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166頁。這五個方面與丸山“原型—古層”含括的“歷史意識的原型”“政治意識的原型”和“倫理意識的原型”的指向較為一致,只不過樸忠錫的論述較為具體和細化一些。在丸山的論述中,歷史、政治和倫理這三大“原型”也非涇渭分明,而是彼此之間存在一定的交融和共疊。樸忠錫力倡“巫性”這一學術(shù)范疇,試圖以此來概括支配和影響著韓國思想文化以及韓國民族思維方式的底層邏輯和精神內(nèi)核,其學術(shù)功用和目的,與丸山的“原型—古層”論,并無二致。
比起“原型—古層”論來,“近代化”論貫穿于丸山學術(shù)思想的始終。丸山在曼海姆和法蘭克福學派思想的啟發(fā)下,確定了“近代思維”的對立、矛盾和悖論性的“二元”特征,如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近代(現(xiàn)代)、外來與本土、正統(tǒng)與異端、內(nèi)發(fā)與外發(fā)、普遍和特殊、非近代和近代等系列“反語”。當把“近代思維”作為評判標準來審視日本江戶時代的各個思想流派時發(fā)現(xiàn),由古學派思想家荻生徂徠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徂徠學派是最富有“近代性”色彩的思想流派。由于徂徠學派是“近代思維”在日本德川思想中的表征性存在,那么與徂徠學派相對立的或受徂徠學派批判的思想流派自然是不具有“近代思維”特質(zhì)或作為一種與“近代”對立的“傳統(tǒng)”而存在。而由于徂徠學派主要是在批判和解構(gòu)朱子學的過程中表達自己的看法繼而建構(gòu)自身的理論體系和話語形態(tài)的,那么,朱子學無疑就是不具有“近代思維”的一種思想體系。按照丸山對朱子學的定性說法:“朱子學的理,既是物理,亦是道理;即是自然,也是當然。在這里,自然法則和道德規(guī)范已連為一體。……值得注意的是,連接著的雙邊關(guān)系并非對等,而是從屬,即物理對道理、自然法則對道德法則的無條件服從。”(17)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第25—26頁。在被賦予“連續(xù)性思維”和“有機統(tǒng)一體”特征的朱子學體系中,自然、經(jīng)濟、歷史、政治和倫理等渾然于一體,在思維形態(tài)上呈現(xiàn)出一種混沌性、模糊性、靜態(tài)性、整體性等特點。而且,由于朱子學作為政治社會意識形態(tài),內(nèi)嵌于國家權(quán)力體系中,故在根本上缺乏走向“分化”和“獨立”的可能性。而徂徠學在批判和解構(gòu)朱子學的過程中,諸多具有“近代性思維”的“二元”對立漸次展現(xiàn),比如天人相分、政教相離、圣凡相對、公私相別、物我相異等。(18)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73—118頁。可以說,整個日本江戶政治思想的演變,就是由藤原惺窩、林羅山等建構(gòu)起來的作為德川政權(quán)意識形態(tài)的朱子學體系,被反朱子學的“古學派”(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貝原益軒、荻生徂徠、太宰春臺、海堡青陵等)和“國學派”(賀茂真淵、本居宣長)漸次取代從而使得朱子學體系瓦解的過程。該過程,不僅是日本德川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崩潰的過程,還是日本逐漸從傳統(tǒng)走向“近代化”的過程。
樸忠錫悉數(shù)汲取了丸山的思路和方法,對韓國政治思想史進行了系統(tǒng)化的構(gòu)建,認為韓國的政治思想史是一部接受朱子學并使其正統(tǒng)化,后經(jīng)反朱子學的“實學派”的沖擊瓦解,繼而又在“外力”的沖擊下,傳統(tǒng)解體和“近代觀念”在挫折中得以生成和發(fā)展的歷史。在該過程中,“朝鮮實學”是最具有“近代思維”特質(zhì)的、且也是最富有“民族性(韓國性)”的思想流派。高麗末期為了對抗佛教,引朱子學入朝鮮半島,將其作為朝鮮王朝的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并經(jīng)朝鮮儒者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以退溪學派和栗谷學派為代表的“性理學”。同時,由于朝鮮被納入“朝貢—冊封”體系,政治外交上的“事大”取向和觀念上的“小中華意識”朝鮮失去了“自律性”及其“力”的支撐,從而導致了“壬辰倭亂”(1592年)、“丁卯胡亂”(1627年)和“丙子胡亂”(1636年)接連發(fā)生。(19)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298—299頁。面對內(nèi)憂外患和統(tǒng)治危機,出現(xiàn)了重視“經(jīng)世致用”的柳馨遠和李瀷、強調(diào)“利用厚生”的湛軒、燕嚴和楚亭、追求“實學功利”的丁茶山以及具有“政治現(xiàn)實主義”傾向的崔漢綺等“實學派”。(20)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18—430頁。“實學派”學者們不以或少以具有“元哲學”性質(zhì)的“性理”“理氣”為思辨對象,而更多地對政治治理、經(jīng)濟建設和民生日用等諸方面的“問題”提出看法或解決方略。
在這些“實學派”思想家當中,樸忠錫將丁茶山類比于荻生徂徠,(21)盡管樸忠錫對茶山思想特質(zhì)的概括與丸山對徂徠思想特質(zhì)的概括“大同小異”,但令人不解的是樸忠錫在論及茶山“實學”思想源流時,僅提及了戴震考據(jù)學對茶山學術(shù)思想的影響,而未提及徂徠對茶山的影響;只是在引用茶山《論語古今注》中的“仁者,人與人之盡其道也”時,在括號內(nèi)標注“仁斎と似る―丸山”(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89頁)。事實上,茶山的學說受徂徠學派不小的影響。在茶山的《論語古今注》中,引用荻生徂徠43處、太宰春臺112處,而伊藤仁齋僅2處。參見姜智恩:《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guān)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蔣薰誼譯,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266頁;李基原:《朝鮮儒者における徂徠學——丁若鏞の〈論語古今注〉を素材に》,《日本思想史學(38)》2006年。認為茶山在韓國思想史上可以說是“從根底上動搖了傳統(tǒng)的儒教政治思想”“開創(chuàng)近代政治社會之道”的人物。(22)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99頁。茶山的工作,在哲學思想層面,使得朱子學體系中渾然一體的“道理”和“物理”,“天理”和“人道”,“人性”和“人情”發(fā)生了分離,從而使人獲得人的“自主之權(quán)”;(23)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81頁。在政治社會層面,由重內(nèi)在的“仁”向重外在的“禮”“法”發(fā)生轉(zhuǎn)變,其體現(xiàn)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規(guī)范主義指向”和“以人的能力為基礎的政治社會結(jié)構(gòu)的構(gòu)建”意涵。(24)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90頁。總而言之,在茶山的思想中,比起道德更重視政治統(tǒng)治和秩序規(guī)范,比起“自然”更重視人的實踐和“作為”,比起身份更重視人的能力尤其重視人的“自律”和“自主”等能動性。(25)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396頁。
朝鮮王朝雖在明清鼎革時期出現(xiàn)過短暫的“華夷變態(tài)”思想的波動,但就整體而言,一直遵奉“華夏正統(tǒng)”,履行“朝貢—冊封”,以“事大事小”原則,處理東亞區(qū)域國際關(guān)系事務,直至“日韓合并”,以“被殖民”的方式卷入近代世界。樸忠錫注意到了無論是朝鮮朱子學家還是“實學派”均會或多或少地涉及“‘中華’主義的國際秩序觀”問題。從朝韓“民族自立”和“現(xiàn)代國際關(guān)系”的角度出發(fā),樸忠錫特別凸顯了“實學派”對其的批判。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從天文物理學的角度,對“中華(朱子學)”體系中的“天圓地方說”進行批判。李瀷認為“天圓地圓”“地球乃天體之中心”,洪湛軒主張“地轉(zhuǎn)說”;其二,從現(xiàn)實功利主義的角度,“利用厚生派”中的燕嚴和楚亭等“北學”一系強調(diào)“真學問要能為人帶來實質(zhì)的利好”,提出了通過生產(chǎn)、商業(yè)、流通以及海外貿(mào)易等“富國”的主張。這些“學問觀”上的變革和“國富論”主張,為朝鮮19世紀后半期在歐美和日本強迫下的“開國”準備了“內(nèi)在的‘開國’邏輯”。(26)樸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第448頁。
盡管樸忠錫預設了“朝鮮實學”對朱子學的沖擊和瓦解作用,但在其闡釋中亦可發(fā)現(xiàn)“朝鮮實學”并沒有實現(xiàn)對朱子學的真正“解構(gòu)”。由于日本沒有科舉,朱子學與德川政治并沒有實現(xiàn)意識形態(tài)上的徹底“統(tǒng)合”,而朝鮮與中國一樣,實行科舉取士,奉行朱子學的兩班階級是朝鮮王朝的權(quán)力、知識和財富的壟斷和占有者,具有十分強烈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朝鮮“實學派”的思想家,雖然并不是完全被排除于政治體制之外,但是被邊緣化、不處于統(tǒng)治階層中的權(quán)力中心,可謂屬于“在野派”。“朝鮮實學”表現(xiàn)出來的“事功”“厚生”“經(jīng)世”等“功利主義”色彩,或可劃歸于儒學現(xiàn)實主義派別。
二、理論框架下的學術(shù)和非學術(shù)問題
樸忠錫借鑒丸山理論對韓國思想史的研究,特點明顯,貢獻巨大,(27)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本稿僅就樸忠錫借鑒丸山“原型論”和“近代性”兩大支點以對韓國思想史的解釋進行探討,故其他方面將另撰他文予以討論。但亦出現(xiàn)了丸山理論和方法自身固有的問題。其最為顯著的是以“近代主義—韓國主義(韓國性)”框架去剪裁韓國思想史,以“檀君朝鮮”和“巫性”對應“原型—古層”來凸顯“韓國性”,以“實學派”對應“徂徠學派”來凸顯韓國“近代思維”或“近代性”。事實上,“檀君朝鮮”“巫性”“實學”之學術(shù)話語形態(tài)均是自“日韓合并”后朝韓民族反抗殖民、追求民族獨立進而要在東亞世界中自我定位的產(chǎn)物。故而,當以某種理論、政治立場和價值訴求來支配學術(shù)研究時,不可避免地將出現(xiàn)以論代史、遮蔽甚至曲解史實以及視野逼仄等問題。樸忠錫以丸山理論框架對“檀君朝鮮”“巫性”和“實學”這三大核心問題的闡釋大有可商榷之必要。
(一)“檀君朝鮮”問題
揆諸史實可知,關(guān)于朝韓歷史的起源,存在三種在不同歷史階段或被視為史實或被當作神話且認知態(tài)度迥異的“朝鮮”:箕子朝鮮、衛(wèi)滿朝鮮和檀君朝鮮。其中,對箕子朝鮮和檀君朝鮮的評價,反差最為明顯。在前近代,作為中華藩屬體系一員的朝鮮,呈現(xiàn)出對“箕子朝鮮”的高度認可和崇拜,以至于在朝鮮王朝的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實踐中“箕子”受到空前的重視:在政治層面,以“箕子”為信仰,通過“朝貢—冊封”以強化與明清的藩屬關(guān)系,從而確立朝鮮王朝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如世宗所言:“侔擬中國,殆盡二千余年,惟箕子之教是賴。”(28)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四十,世宗十年四月辛丑,漢城:東國文化社,1956年,第126頁。在社會層面,以箕子為信奉對象的箕子墓、箕子祠堂與箕子廟從漢城到道州府等地方廣泛存在且出現(xiàn)建制化的祭祀現(xiàn)象。在學術(shù)和文化層面,涌現(xiàn)出不同體裁和內(nèi)容的“箕子”主題文獻及其相關(guān)歷史著述,比如尹斗壽編《箕子志》、李珥著《箕子實紀》、韓百謙撰《箕田考》、徐命膺纂《箕子外記》,并將箕子譽為“太祖文圣大王”,其地位遠超箕子在中國史書《尚書》《逸周書》《竹書紀年》《史記》《漢書》中的地位。與其適相對照的是,朝鮮王朝對檀君朝鮮和衛(wèi)滿朝鮮不甚注意,即便有其一二,也是疑慮重重,就連世宗都言“檀君統(tǒng)有三國,予所未聞。”(29)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三七,世宗九年九月己丑,第90頁。
而真正對于“檀君”的崇仰和提升“檀君朝鮮”歷史地位的做法,是在“日韓合并”之后、日本殖民朝鮮時期,而且其始作俑者亦非韓國學者,而是那些鼓吹“日鮮同文同種一體論”的日本學者。其目的是通過淡化甚至否定“箕子朝鮮”來抹殺歷史上朝韓和中國的歷史關(guān)系從而為日本殖民統(tǒng)治服務。“檀君朝鮮”的高揚,雖然是日本殖民韓國以對抗“中國”的產(chǎn)物,但“‘檀君’作為朝韓民族的始祖和民族象征”這一觀點,也迎合了韓國追求民族“主體性”的自立愿望,逐漸為韓國學者所接受。可以說,在其民族存亡之際,“檀君信仰成為韓國民眾抗擊日本殖民者的一種重要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得到極大發(fā)展。箕子因為系來自中國的,對于韓國的民族獨立并沒有太大的凝聚作用,在追求民族獨立自主的20世紀,箕子信仰最終被韓國拋棄了。”顯然,“對韓國古史中檀君朝鮮和箕子朝鮮歷史的解釋,從肯定到否定,此消彼長,正可以看出現(xiàn)實的需要。”(30)孫衛(wèi)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和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復旦學報》2008年第5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經(jīng)過數(shù)次對“檀君朝鮮”與朝韓民族起源的學術(shù)爭論,至1997年將“檀君建立古朝鮮”作為定論寫入韓國歷史教科書。該行為表明“檀君朝鮮”由“神話”被政治定性為“歷史”,是一個無須再爭辯和討論的“常識”了。苗威認為,這是一種以“血統(tǒng)”來論說“政統(tǒng)”方法,目的在于實現(xiàn)“與今天的民族國家進行對接”。(31)苗威:《關(guān)于朝鮮半島歷史話語的解構(gòu)》,《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1期。其實,如果將其放入世界范圍內(nèi)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gòu)的歷史和現(xiàn)實來看,確定較為清晰的民族起源和延續(xù)路徑與提煉和倡揚某種獨特的民族精神等行為,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獲得“獨立”和“自立”的較為“普遍性”的做法。
(二)巫性問題
巫,不僅存在于朝韓民族文化體系中,還是一種植根于中華文化深層的“人文根性”,亦廣泛存在于世界諸多民族的風俗禮儀和日常行為習慣中,具有“普世性”特點。不少的人類學成果都已表明巫及巫文化的存在具有時空上的恒久性和廣泛性。弗里茨·格拉夫認為:“古典時期,巫術(shù)活動無處不在。”(32)弗里茨·格拉夫:《古代世界的巫術(shù)》,王偉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頁。從中華文化圈或東亞文明的角度觀之,巫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根本底色。魯迅指出“中國本信巫”,(3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頁。李澤厚認為中國文化存在一種“巫史傳統(tǒng)”。(34)參見李澤厚:《說巫史傳統(tǒng)》,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第10頁。王振復認為:“巫性為中華文化的遠古人文根性。”(35)王振復:《巫性:中華文化的遠古人文根性》,《學術(shù)月刊》2016年第4期。從有關(guān)“巫”的文字學、神話學、史載和考古,均可證明巫對中國歷史文化影響巨大,已為影響政治組織、社會生活以及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大小傳統(tǒng)。(36)關(guān)于中國的巫問題,學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宋應麟:《巫與巫術(shù)》,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胡新生:《中國古代巫術(shù)》,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澤厚:《說巫史傳統(tǒng)》,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高國藩:《中國巫術(shù)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王振復:《中國巫文化人類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
朝鮮半島的文化是中華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韓國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調(diào)查和研究也表明,巫及巫術(shù)文化亦廣泛存在于朝韓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生活習俗中,迄今在一定程度上仍制約著人們的語言表達、日常行為和思維方式。韓國的巫文化研究,發(fā)軔于20世紀初日本殖民朝鮮后所進行的“滿鮮調(diào)查”及其文化項目。其間,一些韓國學者也參與到了對朝鮮半島本土宗教和傳統(tǒng)習俗的人類學調(diào)查和民俗采風活動中。日韓學者通過田野調(diào)查、民俗采錄和史料整理,并借歷史實證主義和神話學研究的現(xiàn)代科學方法,在巫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業(yè)績,基本認為韓國巫俗源于“檀君朝鮮”之建國神話,特別一提的是崔南善總結(jié)出的“巫俗是朝鮮文化的根基,‘檀君’是上古‘祭政一致’時期的巫覡”的觀點奠定了韓國巫文化研究的基調(diào)。可以說,其后的韓國巫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學術(shù)立場均未溢脫出此觀點的輻射范圍。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伴隨著韓國“國學”復興,韓國學者對巫文化的研究益加精細化,也有了更為明確的問題意識和價值訴求。學者們參鑒西方民俗學、宗教學和精神分析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希望通過對巫的原型、祭祀儀式及其民間信仰的研究,揭示出韓國人獨特的民族心性和精神結(jié)構(gòu)。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從跨學科和比較研究的視野,對巫文化進行全新的研究和闡釋,比如從女性主義、文化傳播、影視文學等進行交叉和綜合研究,同時還將巫與薩滿教、西方巫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不可否認韓國巫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豐厚成果,但“韓國學者為主導的韓國巫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主要是‘尋根’”。(37)張國強:《中韓巫文化研究的回顧與比較》,《東疆學刊》2021年第1期。韓國的巫文化研究不乏學術(shù)研究的廣博和深刻,但彰顯出受探尋韓國民族的歷史起源、民族心性的生成邏輯及其精神結(jié)構(gòu)等“自我文化定位”的“自立性”驅(qū)動。也正因為有超乎學術(shù)之外的價值預設和目標追求,故在韓國巫文化的研究中“民族主義”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三)“朝鮮實學”問題
在朝鮮王朝后期所出現(xiàn)的具有經(jīng)世致用、現(xiàn)實批判、注重發(fā)展、實事求是等特點的“實學”思潮中,并不乏理性、功利性和批判性等與“近代性”相似的要素,但問題是“近代性”(38)此處的“近代性”,并非吉登斯、哈貝馬斯和福柯等人的近代性指代,而是指前近代步入近代化之前的某種近代要素和可能性。并不等于“近代化”。當這些“近代性”要素并沒有達到激發(fā)朝鮮王朝向“近代化”發(fā)生根本轉(zhuǎn)變的濃度和飽和程度時,這些被韓國史家所念茲在茲的“近代性”要素僅僅只是“要素”而已,只具有“可能性”。當史家以某種現(xiàn)實立場和價值情感把這些具有“可能性”的“近代性”要素有意識地放大或夸大的時候,“可能性”就被幻化為“必然性”,“近代性”也就等于了“近代化”。包括樸忠錫在內(nèi)的不少韓國學者,在借助“近代”特別是“二元對立”思維解讀李朝后期的“實學”思潮時,往往把尊為官學的性理學當作與“實學”對立的反面存在。問題是,即便是遵奉朱子學的退溪學派和栗谷學派諸人也從沒主張過自己的性理學不屬于“實學”,而是“虛學”。
從“實學”的起源來看,其最早可溯及唐代,真正將“實學”作為一種學術(shù)形態(tài)提出來的是宋代的程朱理學家們。宋代理學家面對“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都歸釋氏”(39)釋志磐:《佛祖統(tǒng)紀》,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第1949頁。的思想局面,為了對抗佛教,竭力闡揚出自孔孟荀及《禮記》中的“實學”傳統(tǒng),一方面否定當時風靡一時的佛老“虛無”之學,另一方面也反思漢唐經(jīng)學中過分重視辭章的“空疏”之風。朱熹自詡自己的理學為“實學”,還把最富有形而上學色彩的《中庸》當作“實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其味無窮,皆實學也。”(4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頁。作為“實學”的朱子學,從外在而言,以反對佛老“虛無”;從內(nèi)涵和目標指向而論,強調(diào)思想之“理”與社會之“事”的實踐性結(jié)合,追求以理行事、事中有理,事理合一。
朱子學傳入朝鮮半島,一方面是自身理論體系足可對抗佛教,另一方面其“修齊治平”觀念可謂前近代東亞世界最好的意識形態(tài)和秩序規(guī)范理念。就此而言,作為朝鮮建國理念的朱子學,當為“實學”無疑。16世紀中葉以李滉和李珥為代表的退溪學派和栗谷學派諸人,將李朝朱子學推至高峰。雖不可否定其對朱子學理論體系的深化和推進,但也以“朱子定論”的方式使得內(nèi)容豐富、體系龐大的朱子學出現(xiàn)僵化、甚至極端化傾向。1592年發(fā)生的“壬辰倭亂”、1627年發(fā)生的“丁卯胡亂”和1636年發(fā)生的“丙子胡亂”,以最為極端的戰(zhàn)爭形式使得朝鮮王朝陷入統(tǒng)治危機。但與此同時,居于統(tǒng)治階層的一批學者卻“各抱地勢、鉤心斗角”以不同的學派和門派勢力,主動參與或被動卷入到朋黨之爭中。在看似具有學術(shù)爭辯性質(zhì)的“南人”“老論”和“北學”之爭背后,無不隱藏著黨同伐異、排除異己的政治性操作。北學派的洪大容、樸趾源和樸家齊等人隨燕行使團赴中國,認識到承嗣“華夏中國”的清朝之民富國強,了解到清朝的考據(jù)之學,也接觸到了由西方傳教士帶至中國的天文、地理、數(shù)學、醫(yī)學等新興科技,隨之將清代“實學”引入李朝,在對李朝僵化的性理學的批判中,進一步擴展了“朝鮮實學”。盡管北學派和星湖學派對“實學”的關(guān)注和側(cè)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同出自退溪和栗谷學脈,思想的根底也均在朱子學。可以說,其“實學”是對朱子學反思和調(diào)整的結(jié)果。(41)參見川原秀城:《朝鮮朝后期實學家的朱子學研究》,《復旦學報》2016年第3期;侯美欣:《論李朝后期從朱子學到“實學”的嬗變》,《孔子研究》2019年第4期。如果將其視作朱子學的絕對對立性存在,那么也未嘗不是對“朝鮮實學”的一種扭曲和誤解。對此,姜智恩對韓國百年來儒學研究后的發(fā)言倒頗具啟發(fā):“包含反朱子學派在內(nèi)的多元學派登場并挑戰(zhàn)了朱子學,這不是一個正確捕捉朝鮮儒學史的觀點,或許它根本就是一種無法得到眾人認可的架空觀點……因為過度注目挑戰(zhàn)朱子學的人物或著作,會導致對朝鮮過去最為興盛的朱子學考察或評價得不夠充分。并且,在朱子學和反朱子學的對立架構(gòu)中,無法準確掌握耗費一生學習朱子學的朝鮮儒者的本質(zhì)。”(42)姜智恩:《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guān)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第39頁。
如何以及以何在東亞世界甚至更大的世界文明體系中定位韓國的歷史發(fā)展和民族精神是自20世紀以來包括但不限于樸忠錫在內(nèi)的不少韓國學者的一大心結(jié),而且民族主義、殖民史觀、近代化論和后現(xiàn)代主義等多種觀念交織在一起深深地制約著韓國學術(shù)的客觀化程度。受現(xiàn)實立場和價值訴求影響的“韓國性”研究,折射出韓國以“民族主義”為導向的知識生產(chǎn)和學術(shù)研究陷入了多重困境。
三、克服與超越:韓東育關(guān)于丸山研究的啟發(fā)
由于日本和韓國對丸山的研究和借鑒,大都受現(xiàn)實政治、價值取向、理論預設以及史料實證等多重因素的支配和制約,而且不同學者所依憑和固守的史料和史觀、理論和現(xiàn)實、政治和倫理等方面不無矛盾之處,所以那些“丸山派”與“反丸山”論辯中的不少問題,最終要么戛然而止或不了了之,要么成了意氣之爭和態(tài)度之爭。而丸山曾就此有過自省和警覺性質(zhì)的表述:“當思想被人們從思想家的骨肉中分離出來以后,被當作‘客觀對象’進行把握的瞬間,就開始‘獨自’行走。倘若它受到思想模仿者的贊美和崇拜,那它本身所內(nèi)含的張力就會松動,其棱角亦將會被磨損至光滑,其充滿活力的矛盾就會被強行地‘統(tǒng)一’起來。或者,因為其個別側(cè)面被繼承而使它喪失原本的活力,進而僵化。”(43)丸山真男:《福沢·岡倉·內(nèi)村》,《丸山真男集》第7巻,第367—368頁。
近年來,中國學者對丸山真男重要著作的翻譯出版、相關(guān)學術(shù)會議的召開、專題研討文集的編纂以及發(fā)表的大量論文等,或可表明中國學界出現(xiàn)了一股“丸山熱”。(44)參見魏靈學、國薇:《中日兩國對丸山真男的研究綜述》,《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11期;許紀霖、劉擎主編:《丸山真男:在普遍性和特殊之間的現(xiàn)代性》(知識分子論叢第16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34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韓東育對丸山真男長達二十余年鍥而不舍的“熱情”——始終以丸山為對決和論戰(zhàn)對象,既“克服”丸山學術(shù)思想中的存在問題和缺陷,又在對其問題理解的基礎上將相關(guān)議題深化和擴展,繼而開拓出新的問題領域和闡釋空間。按照劉岳兵的說法,韓東育將中國的丸山研究及日本思想史研究推到了一個嶄新的“范式”高度。(45)參見劉岳兵:《中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種學術(shù)史的回顧與展望》,《南開日本研究》2013年第1期。由于韓東育對丸山的研究仍處于持續(xù)的推進過程中,所以暫無法對其作出一個定論性的評判。故在此僅將韓東育迄今為止對丸山的研究工作做一宏觀概述,以期能描繪出他對丸山學術(shù)思想的解讀、修正和推進工作,同時也希望揭橥其研究中的歷史實證主義方法和東亞視野對未來學術(shù)研究的借鑒和啟發(fā)意義。
韓東育對丸山的關(guān)注和研究,始于其在東京大學留學時期撰寫的關(guān)于徂徠學派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及其后出版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46)參見韓東育:《徂徠派経世學の研究:“日本近世新法家”の展開》,東京大學博士論文(甲第16576號),平成13年(2001年)7月26日,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書誌ID:000004324384); 2003年由中華書局以《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為題出版了該論文的中譯版;2020年10月中譯本作為氏作《從“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來“化道為術(shù)”之格致過程》中的“上篇”部分由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出版發(fā)行。丸山從“近代性”出發(fā),將徂徠學定位為“朱子學分解過程中的最終完成者”,且賦予徂徠學以“近代思維”的特質(zhì)。而韓東育則直言道:“如果說,徂徠學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早期近代化的思想基礎這一觀點可以被視為事實言說的話,那么,當人們進一步追問事實背后的根據(jù)時,丸山的解釋卻嚴重地背離了事實,而成為異常明顯的‘假說’或曰‘附會’。”(47)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第390頁。那么,丸山到底背離或扭曲了怎樣的事實呢?韓東育以對中國古典的諳熟敏銳地覺察到,丸山通過對西方功利主義學說的強調(diào)而刻意回避了中國先秦的荀子和韓非思想在荻生徂徠及其后學太宰春臺和海堡青陵在徂徠學派形成過程中的“祖型”作用。他在對徂徠、太宰和青陵文本與義理解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證實荀韓思想乃是徂徠學派對朱子學展開批判并脫離儒家學派的主要理論依據(jù)。徂徠學派完成“脫儒入法”的歷史過程,也即是“日本近世新法家”登場的過程。就此,黑住真評論道:“徂徠學派經(jīng)由作者之手,首次從它與東亞思想資源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中得到了正確的復原。”(48)黑住真:《〈日本近世新法家〉序言》,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第2頁。可以說,韓東育對徂徠學派的“經(jīng)世學”定位,廓清了丸山以西方“功利主義”標簽對徂徠學的穿鑿附會,同時,該作亦為重新審視中國先秦的荀子韓非一系的法家學說展示了別樣洞天。對此,中國“新法家”(49)參見宋洪兵:《“新法家”在叩門:〈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二十一世紀》2003年第3期;王悅:《相爭與互補的內(nèi)情》,《讀書》2007年第10期。的評價并非過譽之詞。
關(guān)于丸山學術(shù)研究中的“中國”問題,黑住真指出丸山“只是把西歐和日本捆綁在一起,而中國卻未被連接。……中國不但被輕視,連最初還有的對中國和亞洲的關(guān)系,也消失了。”(50)黒住真:《複數(shù)性の日本思想》,第40頁。而澤井啟一認為丸山由于缺乏“東亞”視域,所以只能故步自封于德川儒學。(51)參見澤井啓一:《丸山真男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論》,第148—156頁。澤井將其原因歸結(jié)于丸山研究視域的逼仄和狹小的做法,雖稍顯武斷,但不失明銳。其實,察丸山文集及其對談錄等可知,丸山并不是完全無視“中國”,而是力有不逮。所以,丸山在其晚年提煉出的“原型—古層”論的構(gòu)建上,尚缺乏更為縝密的歷史實證。樸忠錫利用“原型—古層”在《韓國政治思想史》中,將其具體化為“檀君朝鮮”及其“巫性”傳統(tǒng)。由于“檀君朝鮮”的神話性質(zhì),故其論亦如丸山將“原型—古層”奠基于日本記紀神話和《萬葉集》那樣,從學術(shù)研究的角度而言,至少史料實證方面是不充足的、且大有問題的。丸山和樸忠錫對丸山“原型—古層”之“古道”的把握和解釋,時間上有限;且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僅從本國出發(fā),故在空間上其研究視域未免有逼仄和狹小之感。那么,丸山“原型—古層”之“古”到底作何解呢?韓東育將丸山的“原型—古層”延伸到荻生徂徠的“夏商古道”說,參以白川靜的“殷商古制”說,指出日本文化源自中國東夷之“殷商”,“夏商古道”決定了日本的深層文化邏輯和精神結(jié)構(gòu),且規(guī)定了日本文化中的“崇神尚武”“崇利尚力”等底色。而且,韓東育以“寧失不經(jīng)”的學術(shù)擔當,將丸山“原型—古層”以歷史實證主義的手法具體化為“夏商古道”,從而將其“所知而難以言傳”或“意會不可言傳”的“執(zhí)拗低音”予以了清晰化的解讀:“(夏商古道)應指形成于夏商時期、以原始‘天人合一’世界觀為基礎的生產(chǎn)方式、價值理念、政治原則和民風民俗。”原本產(chǎn)自中國的之所以會成為日本“原型”和核心要素,而丸山之所以敢在“原型”上標注“日本”,只能歸因于“禮失而藏諸野”的“歷史”發(fā)展。(52)參見韓東育:《關(guān)于日本“古道”之夏商來源說》,《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3年第9期;《丸山真男“原型論”考辨》,《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1—125頁;張崑將、董灝智:《東亞史研究的新格局:讀韓東育〈從“請封”到“自封”〉》,《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孫衛(wèi)國、秦麗:《日本實現(xiàn)“去中心化”與“自中心化”之始末經(jīng)緯——對〈從“脫儒”到“脫亞”〉〈從“請封”到“自封”〉之解析》,《外國問題研究》2018年第4期。惹人注目的是,韓東育在對“夏商古道”的客觀實證中,對金文甲骨資料的運用、對先秦古典文獻的掌控和對日本神話的讀解尤見學術(shù)功力,不失“多重證據(jù)法”在學術(shù)研究中的一個完美案例。
丸山從不諱言自己之所以對日本政治思想史傾注極大熱情的深層原因,那就是對20世紀40年代日本知識界方興未艾的“近代超克論”“國民道德論”和“日本精神論”等理論熱潮的厭惡與反感,甚至產(chǎn)生了一種“近乎生理上的厭惡感”。(53)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391—398頁。丸山在日本“戰(zhàn)前—戰(zhàn)中—戰(zhàn)后”均以一個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對日本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以及市民社會建構(gòu)進行過批評,但在丸山的學術(shù)思想中也并非沒有“民族主義”和“日本主義”等非學術(shù)性的價值立場。(54)日本學界對丸山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日本主義”的評論,可參見酒井直樹:《丸山真男の陥穽——ナショナリズム、レイシズム、ヒューマニズム》,《大航海:歴史·文學·思想(24)》1998年第10期;井口吉男:《丸山真男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大阪経済大學教養(yǎng)部紀要(17)》1999年;植村和秀:《丸山真男の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批判》《日本學研究(9)》2006年;渡邉憲正:《丸山真男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観》,《関東學院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年報(34)》2012年。韓東育早期在對丸山“原型”論和徂徠學的研究中就已發(fā)現(xiàn)丸山學術(shù)背后的“日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預設立場和價值傾向。(55)參見韓東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論”與“日本主義”》,《讀書》2002年第10期。而在日本戰(zhàn)敗后,丸山認識到如果任由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感肆意膨脹,現(xiàn)代世界會遭遇更大危機,民族主義必須借助民主主義的力量化解其“現(xiàn)代性危機”,達成“民族主義的合理化”。(56)參見王超:《丸山真男的民族主義論:“現(xiàn)代性危機”的反思》,《日本學刊》2020年第4期。何以丸山會處于“民族主義”和對日本軍國主義批判的兩難之境呢?韓東育將丸山置于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戰(zhàn)后作為戰(zhàn)敗國接受東京審判卻又對戰(zhàn)爭罪責“曖昧含混”的歷史脈絡和現(xiàn)實境況中,既入乎其內(nèi)又出乎其外,去探索丸山龐大學術(shù)思想體系的內(nèi)在機理、原初動力和終極規(guī)定,繼而為重新審視丸山學術(shù)思想的發(fā)展開辟出了新的研究維度。如果理解無誤的話,那么他的問題意識和目標指向應該是:丸山學術(shù)追求的內(nèi)在支柱抑或治學動力究竟何為?丸山的學術(shù)研究為何能成為現(xiàn)代日本學術(shù)研究的一座高峰或一個坐標?丸山何以會是丸山?……這是一些具有根本性和整體性的“元問題”。問題雖宏觀,但對其的解答需要微觀和具體,即要去探求丸山的“變中之不變”和他要求人們對其本人的“內(nèi)在理解”。韓東育通過對丸山文集、對談錄和回顧錄等多種文獻的細致梳理,發(fā)現(xiàn)丸山學術(shù)的一生都是在為青少年時期被日本特高警察抓去遭受訊問而受到的羞辱和心理創(chuàng)傷求解:日本為什么是這個樣子?換句話說,丸山學術(shù)追求的一生都是在為遭受特高警察的“那一巴掌”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創(chuàng)傷尋求“治療”,只不過“治療”的方式是“學術(shù)研究”,所以丸山才表現(xiàn)出對“‘近代超克論’的特別態(tài)度、朱子學歸謬的技術(shù)路線和本國近代說提煉的行動指標”。(57)參見韓東育:《丸山真男的學術(shù)研究與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思》,《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丸山的一生(1914—1996),經(jīng)歷了日本戰(zhàn)前、戰(zhàn)中和戰(zhàn)后全部的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而丸山的學術(shù)研究范圍從古代的記紀神話到現(xiàn)代民主再造和市民社會等多個方面均有涉及,所以一定程度上而言,丸山是濃縮了的“日本”。讀懂了“丸山”,也就泰半理解了“日本”。
韓東育的丸山研究甚至可以說他的整個的學術(shù)風格,獨特而鮮明。其中,歷史實證主義方法和“東亞”視野尤為明顯。從客觀實證出發(fā),他力圖克服理論預設和價值訴求對史料的硬性剪裁甚至有意或故意無視;從“東亞視野”出發(fā),他將相關(guān)研究不局限于日本或韓國等一隅之地,通過“東亞”的連帶聯(lián)動,見微知著,“小題大做”。而在他的研究中,歷史實證和“東亞”視域又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因視野闊達,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史料,助于實證;反過來,實證又可夯實“東亞”的內(nèi)外和異同關(guān)聯(lián),二者相得益彰。
在丸山的學術(shù)思想中,固然存在“近代主義”“民族主義”“日本主義”等理論預設和價值先入的問題,亦有與之相伴而來的“東亞”視野逼仄和客觀實證受限等情況。而這些問題,或多或少地都已被學者們所注意到,且對其有不少的批判。但如何在對丸山學術(shù)思想深入理解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的繼承和闡揚,仍是丸山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和出發(fā)點。樸忠錫受業(yè)于丸山,亦服膺丸山學說,將丸山的理論和方法應用到韓國思想史的研究中,強化了對韓國思想存在的政治和社會背景的研究,也充分注意到了韓國歷史和思想受中國影響的歷史事實,可以說其對韓國思想史的構(gòu)建不失為繼承和闡揚丸山理論和學術(shù)方法的一次有益嘗試,不過,也繼承了丸山理論和方法的固有缺陷,同時在相當程度上又放大和凸顯了“民族主義”和“以論代史”的問題。韓東育則是對丸山的“內(nèi)在”理解和“外在”超越來既理解“丸山”又解讀“日本”的,同時藉此深化對“東亞”的認知甚至要創(chuàng)構(gòu)一種既非東又非西卻既東又西的“第三種文明”形態(tài)。(58)參見韓東育:《東亞研究的問題點與新思考》,《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1年第3期。其中體現(xiàn)出的歷史實證和“東亞”視野尤具啟發(fā)意義,就從學術(shù)研究的本質(zhì)而言,至少可以讀解出這樣的延伸意涵:學術(shù)研究應該是立足于證據(jù),盡最大可能地理清已然之事,即便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絕對,也要在最大限度上去逼近歷史事實的真相。盡管學者可以參照某種理論或自身的思想駕馭語言,組織敘述,但首要的是不應曲解甚至遮蔽某些相關(guān)史料和證據(jù),亦不應牽強于某種理論而操控史料,更不應該以某種民族立場和價值觀念而過度闡釋某類史料。雖然學者及其學術(shù)研究無法避免時代和個人因素的影響,但更應該以此為戒,保持足夠的自我警覺和自我批判,以一種超然和客觀中立的立場,以澄清事實和真相為學術(shù)研究的第一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