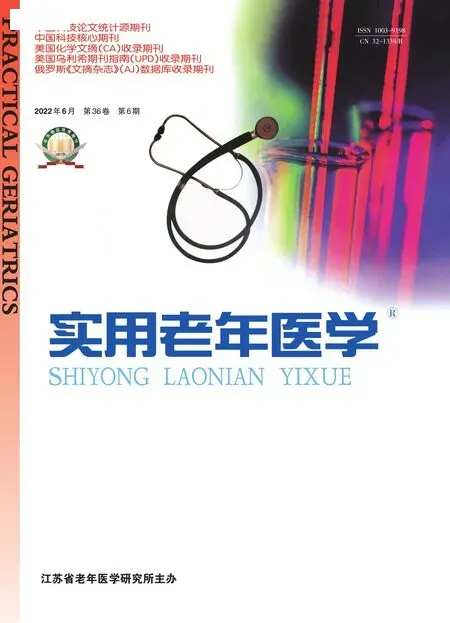老年人共病與衰弱的研究進展
李倩 肖謙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8.70%,65歲及以上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3.50%。根據聯合國對老齡化社會的定義(≥65歲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我國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人類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越來越多的人呈現出與衰老相關的特征,特別是身體衰弱和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增加。由于老年人多器官功能退化及疾病易感性增加,多病共存目前已經是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共病與年齡增長等因素有關,共病可導致多重用藥、醫療負擔增加、老年人的功能狀態和生活質量下降,進一步可導致不良事件和死亡風險顯著增加。衰弱也可導致不良事件和死亡風險增加。本文主要圍繞老年人共病、衰弱及二者間的關系進行綜述。
1 老年人共病
共病是多病共存的簡稱,是指≥2種慢性病并存[1]。老年人群中慢性病流行態勢嚴峻,疾病負擔沉重,已成為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國外一篇系統評價顯示,老年人共病的患病率為66.1%,其中共存≥3個及≥5個慢性病的患病率分別為44.2%和12.3%[2]。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共病患病率為17.0%[3],60歲以上住院病人共病患病率為69.3%[4]。而另一項針對療養院70~89歲老年人的研究數據顯示,其共病患病率高達98.75%[5]。老年人共病可導致多重用藥比例增加、醫療負擔增加,機體功能狀態下降,入院頻率增加,健康相關生活質量下降。美國一項調查表明,共病增加了不良健康后果,如死亡和殘疾的風險[1]。
2 老年人衰弱
衰弱是指具有多種原因和病因的醫學綜合征,其特征在于力量、耐力的下降和生理功能的下降,從而增加了個體殘疾、住院、死亡的風險[6]。未來我國將會面臨龐大的老年人群,然而對于這一特殊人群,實際年齡不足以預測疾病預后或死亡,而衰弱概念的引入,可以更確切、客觀地反映老年人慢性健康問題和醫療需求,還可以解釋疾病預后、康復效果和生活質量的差異。衰弱的測量工具目前國際上沒有統一的標準,應用比較廣泛的是Fried標準、Rockwood臨床衰弱量表、FRAIL量表、蒂爾堡衰弱指標、社會脆弱性指數、HALF4量表、自陳式社會衰弱狀態問卷、社會衰弱指數等。其中Fried標準簡單、易于操作,可以幫助醫務工作者快速識別衰弱或衰弱前期病人,是目前一個比較優越的衰弱篩查工具。Fried標準包括不明原因體質量減輕、感到疲乏、虛弱(握力下降)、步速減慢和體力活動減少,滿足以上5項中的3項及以上即可確定為衰弱,滿足1~2項即為衰弱前期[7]。由于對衰弱的定義、納入標準及評估量表不同,不同研究的衰弱患病率差異較大。國外報道顯示,老年人衰弱的患病率為11%[8]。國內一項對社區老人的調查顯示,其衰弱患病率為23.77%[9],而針對住院老年人的研究顯示,其衰弱患病率為48.3%[10]。另一項針對養老機構60歲以上老年人的研究發現,衰弱的患病率為60.6%[11]。衰弱使老年人更容易在住院期間發生不良事件,可導致一系列與入院原因無關的并發癥,而這些并發癥可能導致住院時間延長、機體功能下降和死亡率升高。與無衰弱的老年人相比,衰弱老年人平均死亡風險增加15%~50%,若能采取相應的措施來干預衰弱,可以延緩3%~5%老年人死亡的發生[6]。
3 共病與衰弱的關系
衰弱和共病是相互關聯,但又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概念。衰弱不等同于衰老、殘疾及共病,但又與其相互重疊,其可對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生理及心理等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就目前對共病與衰弱的關系研究結果進行初步總結。
3.1 共病種數與衰弱的關系 周莉華等[12]的研究表明,衰弱的患病率與共病種數無關(P=0.613)。而英國一項研究發現衰弱與共病種數明顯相關[13]。靳秋露等[14]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絕大部分高齡住院病人患有2種以上慢性病,進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共病種數多為衰弱的危險因素。劉俊含等[15]對65歲以上老年人的共病情況及衰弱程度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調查對象平均患有慢性病(3.5±1.5)種,青老年組(65~74歲)與中老年組(75~85歲)的共病種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老老年組(≥85歲)的共病種數顯著多于青老年組(P<0.01)和中老年組(P<0.01);此外,老老年組的衰弱嚴重程度顯著高于青老年組與中老年組(均P<0.05),且老年人的共病種數與衰弱程度呈正相關(r=0.362)。李靈艷等[16]對老年住院病人共病及多重用藥與衰弱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衰弱前期組和衰弱組病人的共病種數多于非衰弱組(P<0.01),衰弱組共病人數比例明顯高于非衰弱組和衰弱前期組(P<0.01),且住院老年人的衰弱程度與共病種數呈正相關(r=0.308)。
目前我國對于共病種數與衰弱之間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隨著共病種數的增加,衰弱程度是否無限制增大還不清楚,甚至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兩者無相關性,因此,兩者之間的確切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3.2 共病嚴重程度與衰弱的關系 崔月等[17]對1671名社區≥55歲人群進行橫斷面調查,采用Fried衰弱表型量表進行衰弱評估,采用查爾森合并癥指數(CCI)進行共病嚴重程度評估,結果發現CCI評分高是衰弱的危險因素,提示共病嚴重程度是衰弱的影響因素。然而目前我國對于慢性病的嚴重程度尚無統一的評價指標,且該方面的研究較少,同一疾病在不同研究中的嚴重程度劃分不一致,因此,共病嚴重程度與衰弱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3.3 共病類型與衰弱的關系 衰弱和共病是相關的,但臨床個體卻截然不同。針對老年人的許多研究結果都支持慢性炎癥和免疫激活對衰弱的發展有影響,特別是慢性炎癥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機制(如肌肉骨骼、內分泌和血液系統)導致衰弱[18]。目前我國對于老年人不同共病與衰弱之間互相作用的機制及臨床研究較少,但患有DM、肌少癥、骨質疏松癥、高血壓、COPD、骨關節炎、抑郁癥、CHD、心力衰竭(HF)、慢性腎臟疾病(CKD)、周圍血管疾病等老年人常見慢性病的病人更容易出現衰弱,尤其是以上疾病共存時。
DM是老年人中最常見的慢性病之一。DM導致衰弱的機制包括激素、炎癥、神經系統因素、營養和活動因素,但胰島素抵抗或胰島素缺乏可能是DM病人衰弱發生的重要影響因素[19]。許多研究均表明DM與衰弱有關。希臘某醫療機構對老年人的一項橫斷面究結果顯示,與沒有DM的同齡人相比,DM病人衰弱者更多[20]。此外,西班牙一項研究顯示,DM使老年人衰弱風險增加了32%[21]。
抑郁癥和衰弱經常并存,抑郁癥通常表現為在心理和社交領域沒有足夠的應對資源,老年人可能對體育和社交活動失去興趣,從而增加了身體機能下降和跌倒的風險。在衰弱的老年人中,抑郁癥的患病率高達46.5%[22]。患有抑郁癥的老年人比沒有抑郁癥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現衰弱[23]。老年抑郁癥病人體內IL-6水平升高,其與肌肉質量和力量下降有關,并且對中樞多巴胺能功能產生負面影響,這可能導致抑郁癥、疲勞、認知功能障礙及運動減慢,從而導致衰弱的發生。老年抑郁癥病人的前額葉白質高信號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衰弱的關鍵因素[24]。巴西一項針對315例老年門診病人的隊列研究顯示,無論使用何種抑郁問卷,抑郁都與衰弱明顯相關[25]。國外一項研究亦表明,抑郁癥使老年人衰弱發生風險增加了59%[26]。
肌少癥是一種老年綜合征,其特征是骨骼肌力量和質量的下降[27]。在年齡≥60歲的老年人中,肌少癥的患病率大約為10%[28]。肌少癥與衰弱關系密切,這可能與他們的某些發病機制相同有關,比如氧化應激作用、骨骼肌氧化能力降低和線粒體功能障礙等。飲食中蛋白質的總量會調節蛋白質的合成與肌肉代謝,高蛋白質攝入與老年人衰弱呈負相關[29]。一項對≥75歲老年人的橫斷面調查研究結果表明,衰弱者與肌少癥者存在很大程度的重疊[30]。國外一項對平均年齡為(69.98±6.28)歲老年人的描述性橫斷面研究結果顯示,肌少癥與衰弱前期有關,衰弱程度與肌少癥之間存在明顯關聯[31]。
此外,患有COPD的病人更容易出現衰弱。美國一項針對COPD病人的系統評價顯示,COPD病人衰弱的發生率較非COPD病人增加了2倍[32]。洪晴晴等[33]的研究結果顯示,老年COPD病人的呼吸困難嚴重程度能預測衰弱程度。
衰弱還與CKD的所有階段有關,尤其是與中度至重度CKD。腎功能不全可以通過增加氧化應激直接導致炎癥介質(如CRP、IL-6等)水平升高。Wilhelm-Leen等[34]研究發現,當病人估算腎小球濾過率(eGFR)<45 mL/(min·1.73m2)時,衰弱的發生風險明顯增加。宋良晨等[35]的研究結果顯示,eGFR<45 mL/(min·1.73m2)和45~59 mL/(min·1.73m2)的老年男性CKD病人發生衰弱的風險比eGFR≥60 mL/(min·1.73m2)者分別高1.02倍和0.84倍,說明衰弱與CKD嚴重程度有關,CKD病情較重的病人更容易出現衰弱。
綜上可見,DM、COPD、肌少癥、抑郁癥、CKD等均與衰弱明顯相關,它們作為老年人中的常見慢性病,當其共存時,危險因素相互疊加、放大,作用機制相互重疊也更為復雜,從而導致衰弱的發生率增加,使老年人再發其他慢性病的概率也進一步增加,相互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增加老年人不良事件及死亡風險。
4 小結
我國目前對老年人共病與衰弱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慢性病之間的關系尚未明確,也無統一的衰弱調查工具,對早期衰弱的識別欠缺有效手段,并且缺乏對共病與衰弱之間互相影響的發病機制及臨床觀察的研究,對共病種數、共病嚴重程度與衰弱關系的臨床研究也較少。下一步需要探索更具有實用價值的研究工具,區分衰弱老人與非衰弱老人,控制老年人共病與衰弱的危險因素,深入了解老年人慢性病及多病共存現狀,對老年慢性病病人進行綜合管理,制訂疾病預防控制的優先領域,最大限度減少不良事件的發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促進健康老齡化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