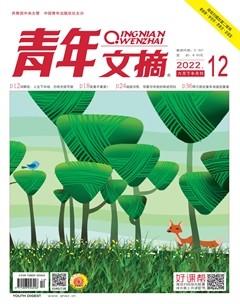窮而后工
常小仙

相傳為東漢蔡邕所編的《琴操》一書中,《水仙操》這節講了一個故事:俞伯牙跟著成連先生學習彈琴,學了多年都沒有出師。成連說:“我的老師方子春住在東海,他能幫人把情感灌注到琴聲中,我帶你去找他吧。”于是,兩個人坐船來到海上的一座小島。成連讓伯牙上島后,就自己駕船離開了。伯牙在海島上苦苦等待,一直不見老師回來,他四顧無人,但聞海水洶涌,林岫杳冥,眾鳥啁啾,于是悄然而悲,感嘆說:“老師已經觸動我的感情了!”說著拿起琴來創作了《水仙操》。這首曲子后來果然四海流傳,成為天下名曲。
伯牙學琴的故事,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一個文藝創作的秘密:好的文藝作品,往往出自深刻的生命體驗;而深刻的生命體驗,又往往來自極端的境遇。宋代文學家歐陽修提出了“詩窮而后工”的文藝理論:“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大凡讀書人胸中蘊藏著才智和抱負卻不能在當世施展的,總是喜歡浪跡于山巔水邊,看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等自然萬物,往往會探究它們的奇形怪狀,而內心懷著憂思積郁,就會出言怨諷,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寫出人難以言說的感受,境遇越糟糕,往往寫得越真切動人。
伯牙在日常普通的環境中,雖然也努力學琴,但琴聲始終少一點真正動人的生命力量。而當他來到空無一人的海島上,獨對蒼穹,感受到自然的強大、個體的渺小,宇宙的無限、生命的短暫。于是,他的藝術不再單薄無力,不再平庸乏味,而真正有了動人心魄的力和美。這就是“絕境”逼出的藝術靈感。
偉大的文藝多與庸常絕緣,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也常常是不幸的,就像屈原、司馬遷、杜甫……磨難不一定造就文藝,但文藝往往出自磨難。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像病蚌一樣,用肉體、心靈的疼痛,打磨出一顆顆流光溢彩的文藝“珍珠”。作為個人,他們非常不幸;但作為人類心靈的杰出代表,他們是文明之光、生命強音!
(本刊原創稿,洪鐘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