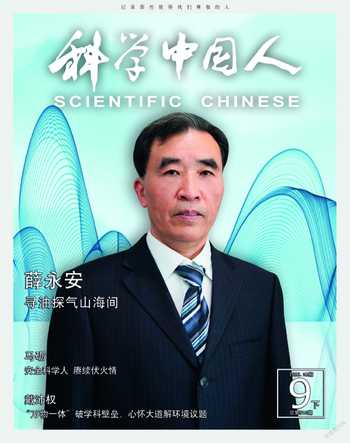“萬物一體”破學科壁壘,心懷大道解環境議題
戶萬
正如《莊子·齊物論》所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如果從環境科學家的角度看世界,也會發現,天地萬物渾然一體,充滿了哲學意味。如今,打破學科壁壘,甚至跳出學術界,直接與政府和社會對話的跨學科研究正在成為潮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港中大”)理學院地球與環境科學課程的副教授戴沛權正是這種“萬物一體”思想和跨學科研究的倡導人。
農業與森林生態系統是地球系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闡明農業、森林與大氣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地球系統科學的前沿焦點,對解決空氣污染、氣候變化、糧食保障及生態危機等嚴峻問題亦至關重要。戴沛權長期致力于結合高性能地球系統模擬及創新的多元統計方法,深入了解農業、森林生態系統與大氣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著力從跨學科角度解決與之密切相關的環境問題。
近年,戴沛權的研究成果多次得到國際同行認可,先后有多篇論文發表于《自然·氣候變化》(Nature?Climate?Change)、《自然·食品》(Nature?Food)、《大氣化學與物理學》(Atmospheric?Chemistry?and?Physics)等大氣、環境與食品科學領域期刊,在地球系統科學前沿領域中占得了一席之地。相關研究一方面為地球科學模式尤其是GEOS-Chem化學輸送模型和CESM地球系統模型的開發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為預測和解決空氣污染及糧食短缺等嚴峻問題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方法與觀點。
“你可隨意挑選一個關心的議題,我們都有辦法設計出相應的模型來探討這些問題。”在戴沛權看來,環境問題雖復雜難辨,但亦環環相扣,通過科學的系統設計,大多數人們想要了解的宏觀議題都能應對。
看見需求,當地球的醫生
要說香港占地最大、風景最秀逸的校園,非港中大莫屬。校園依山而建,面海而居,從山頂到山腳,遍布百余座大樓。生態豐富,處處花木扶疏,中西風格的建筑掩映其間,盡得詩意。其中,“環境與持續發展”更是港中大四大策略研究范疇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譽。
早在2003年讀高中時,戴沛權就與港中大有過交集。當時他在父母的殷切期盼下,一度想要成為醫生,并獲得了港中大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然而,面對唾手可得的機會,他卻猶豫了。“我從小就喜歡動植物,熱愛大自然。我那時想到,這世上有許多醫生,人身體不舒服,就可以走進醫院接受診療救治,但長期以來,卻少有人研究地球環境問題。環境持續惡化,最終影響的便不只是地球生態,還會造成更多的人類生病。”戴沛權心里升騰起強烈的使命感——“也許我可以做地球的醫生,這樣既能治理環境問題,又能讓更多人類避免因環境惡化而患上疾病。”
于是,懷著熾熱的理想,戴沛權孤身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環境工程科學專業。本科時,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書籍文獻。他運用化學、物理、生物等基礎科學知識,不斷觀察、解釋和認識大千世界,嘗試從理論映照真實的自然變化,從變化的自然中總結出可靠的觀點。其間,他逐漸意識到,若有好的理論框架,科學家是可以解決地球正面臨的環境問題的。“于是,我認定了,這就是我未來想要走的道路。”
然而,環境工程科學涵蓋范圍如此廣,到底要從哪里切入呢?2007年戴沛權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工程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尋找答案。博士前半年,他一直在實驗室工作。“可我發現,做實驗不是我的興趣,我更喜歡跟計算機技術相關的工作,我還喜歡涉及全球的這類大尺度的研究。”于是戴沛權當機立斷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運用電腦模擬系統研究大氣科學的領域,探索氣候轉變對懸浮粒子及空氣質素的影響。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第一手數據,了解世界不同地方正在發生的變化,這個過程令他非常享受。
在哈佛深造期間,戴沛權的表現一如既往地出色。他兩獲哈佛大學頒發的卓越教學獎,并將霍華德·T.費希爾(Howard?T.?Fisher)卓越地球信息科學獎收入囊中。2012年,博士畢業后,戴沛權又獲“裘槎博士后研究獎學金”,到母校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后研究。此時,戴沛權在國外的科研生涯正是風生水起,但一年后博士后出站時,他卻沒有絲毫留戀地選擇了回國。
對此,戴沛權認真解釋道:“雖然做科研在哪里都可以,但我首先是中國人,是香港人。我要為祖國和家鄉的科研事業、社會發展作貢獻。”另一促使他回國的原因在于,“我希望回去幫助那些同我一樣,在學生時代、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感到迷茫的年輕人。通過我的成長經歷和心得,引導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激發他們的熱情。”就這樣,戴沛權由己及人,心懷“大道”,在闊別十年后,帶著前沿的理念和成果,走進了港中大。
打破壁壘,做跨學科研究
如今,戴沛權不僅是港中大理學院地球與環境科學課程的副教授及地球系統科學課程的主任,還是大學通識教育部的副主任,以及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港中大校訓“博文約禮”,與戴沛權廣泛涉獵,以跨學科知識和全局視角做研究的理念不謀而合。
大氣科學作為地球科學的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覆蓋整個地球的大氣圈。它與水圈、冰雪圈、巖石圈、生物圈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其組分、結構、運動,存在著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造成了科研的復雜性。打破學科壁壘,開展跨學科研究,勢在必行。
戴沛權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學術思路,是以人為排放、土地利用、糧食生產與消費等人類活動為背景,探究空氣質量和氣候變化、農業與森林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各個領域中的變量相互影響的模式,尋找綜合的適應與管理策略,為環境的保護、社會的發展提供科學的建議。
在跨學科研究中,難點在于如何高效地溝通。戴沛權說:“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傳統,有些方法為外界不解,甚至不被接受。所以,當我跟生態學家、農業科學家、公共衛生學家、經濟學家等談我們的模型時,他們起初常常感到不可思議,難以相信。做跨學科研究,肯定要突破這些難關。面對不同領域的專家,要虛心交流,互通有無,揚長避短。”
跨學科研究的觀念和心態建設起來了,下一步則要做好案頭工作。“我需要真正深入對方的研究領域去,花大量時間閱讀他們的論文、專著。經濟學的、生態學的、農業科學的……通過這個過程,幫助自己建立宏觀的知識體系。一方面,當我在進行跨學科交流時,可以使用對方熟悉的術語,表明誠意,迅速推進合作關系;另一方面,我可以事先設計好跨學科的研究思路,然后尋找對應的專家合作研究,有的放矢。”
懷著這樣的想法,自2013年加入港中大以來,戴沛權不斷探索那些鮮有人涉足的領域,尋求新穎的角度,積極開展創新研究。在一次次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中,他形成了三大研究主題,包括:臭氧與植被的相互作用對作物與森林生產力和空氣質量的影響;氣候、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化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可持續農業與飲食模式對糧食安全與環境健康的多重效益。以諸多項目為依托,戴沛權廣泛聯合各領域專家,為關乎人類福祉的環境問題尋求答案。
跳出傳統視角,挖掘新鮮觀點
2018年以來糧食危機席卷全球,面對這一重大議題,科學家往往從單一環境因素入手,鮮有人注意到不同因素之間的協同作用對其產生的影響。戴沛權則視角獨特,從臭氧污染和全球暖化的協同作用對農作物生產的影響出發展開研究。他采用先進的計算機模型,模擬未來一系列的環境變化及人類活動,從而預測將來的氣候和空氣質素,并精確地把地球系統中物理和化學成分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也計算在內。在充分考慮各種可能的情況后,他得出結論,在未來數十年里,氣候變化和空氣污染惡化問題將可能導致全球農作物生產量大減,令營養不足的人口比例上升,嚴重威脅全球糧食安全和公眾健康。最壞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營養不足人口將于2050年前增加約五成。然而,嚴格控制空氣污染,可部分抵消氣候暖化對農作物的影響。同時,配合種植更耐熱農作物品種,或許可以扭轉局面。戴沛權的研究顯示了臭氧污染和全球暖化的協同作用超過二者單獨對農作物生產的影響,對世界各地的農業及空氣污染政策制定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考。
此外,在空氣污染問題上,許多人都會想到,是工業污染導致了空氣污染加劇。戴沛權則針對氣候暖化對空氣污染的影響開展研究,發現在過去30年,中國及周邊地方的地表平均氣溫在夏季提升最高達3℃,令夏季地表臭氧濃度增加了2~10ppbv。臭氧濃度增加,所造成的最直觀的危害就是,它將導致因長期吸入臭氧引致呼吸病癥而過早死亡的人數增加。因氣候暖化而導致的臭氧污染加劇,可使整個東亞地區,每年過早死亡人數增加約6000人。相比之下,廣為人知的燃燒化石所制造出的人為排放,也不過令臭氧濃度增加最多30ppbv,導致每年過早死亡人數增加約6萬人。由此可見,除工業排放之外,氣候變化對中國人口的健康亦有重大損害。戴沛權又指出:“氣候暖化及二氧化碳濃度上升,一般會令植物于夏季生長得更茂盛,促進植物透過葉氣孔吸收更多臭氧,可以抵消部分氣候暖化及排放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因此,他呼吁,未來控制空氣污染的政策,必須將氣候及生態系統的影響納入考慮因素之內。
近年來,人口快速增長,導致對糧食尤其是肉類的需求不斷提高,這一變化是否會使地球環境產生連鎖反應?為了探究這一問題,戴沛權課題組以1980年至2010年中國食品生產和消費模式的變化為基礎,并綜合電腦模型進行實驗。結果顯示,過去中國飲食模式的改變,尤其因肉類需求量大增,使農業氨氣排放量增加6成多,年均細顆粒物濃度增加達10ug/m3,而這個從飲食改變而來的增長約為同一時期來自所有細顆粒物污染源的兩成,導致每年約9萬人過早死于空氣污染相關疾病。具體來說,就是飼料作物生長過程中含氮化肥過量使用、牲畜排泄物又向空氣釋放大量活性氮,聯合導致含氮污染物增加,影響環境健康,亦使一氧化二氮等溫室氣體增多,進而加劇全球變暖。
戴沛權和團隊通過實驗發現,如改變目前過度吃肉的飲食習慣,改為《2016年中國膳食指南》推薦的較健康、多菜少肉飲食模式,則可減少兩成農業氨氣的排放量及6ug/m3細顆粒物,并可避免每年7.5萬人因空氣污染而過早死亡。這項研究,是全球首次發現,廣泛采用多菜少肉的飲食模式,可成為減輕中國嚴重空氣污染問題的對策之一。不僅如此,戴沛權還研究發現,間套作系統作為一種可持續農耕模式可減少空氣污染,在促進糧食安全、環境與人類健康各方面均具有多重效益。所以,綜合來說,改善農業生產模式和國民飲食習慣,除了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幫助國家邁向碳中和,亦可作為減輕中國空氣污染的重要策略之一。
如今,在“碳中和、碳達峰”的戰略背景下,環境問題越發重要。戴沛權響應號召,計劃更深入探究空氣污染對森林的影響,進而為國家制定科學的發展路線提供參考。此外,他還將繼續可持續農業與飲食模式的研究,致力于建立對環境更友好的飲食文化,并以此推動農業技術的改進,將制造和需求相結合,最終實現多贏的局面。對戴沛權來說,環境研究從來不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紙上談兵,而是深入社會和自然,體察發展需求和難點,于迷霧中抽絲剝繭,找出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且更切實可行的方案。多贏,是他最樂見的局面。
助人者,人恒助之
基于累累成果,戴沛權于2014年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RGC)的“杰出青年學者獎”,2015年獲聯合國頒發的“世界氣象組織青年科學家研究獎”,成為香港首位獲頒這項研究獎的科學家;更于2018年獲選“香港青年科學院”的創院成員及義務秘書。
面對榮譽和獎勵,戴沛權表現得謙虛和感恩,希望繼續為社會作更多貢獻。然而,回首這十余年,他坦言,曾經差點就放棄了科研。一直以來,對戴沛權而言,工作中最主要的兩個難點,一是如何說服其他領域的專家開展合作,二是如何將尺度如此之大的理論成果應用于實際社會。“有段時間,我發覺工作很難推進,一度萌生了離開科研界的想法。最后,是作家弗雷德里克·布赫納(Frederick?Buechner)作品里的觀點啟發了我。”布赫納在書里說,人生的目標應是兩樣東西的交會處,一樣是能給予你最深刻的喜悅的事物,一樣是這個世界上所最急需的事物。戴沛權恍然意識到,這不就是自己正從事的科研和教學?
“我享受在科研中求知、解題的過程,享受在教學中幫助和影響學生的過程,享受在探究環境問題的過程中為百姓謀求更好的生存條件,向政府、企業和公眾宣傳,引起他們的關注和重視的過程。我希望大家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吃什么、消費什么、使用什么,都能影響到這個世界。”戴沛權由此深深意識到,自己對環境科學的熱情,再也沒動搖。
在哈佛大學讀博時,戴沛權的導師常常對大家說,“When?you?share,you?gain?a?lot?more?than?if?you?don't”。意思是,當你分享時,你得到的比不分享時多得多。后來成立團隊,戴沛權也向成員強調要保持開放和互助的精神。助人者,人恒助之。正是基于這種文化,戴沛權帶領團隊與外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結交了真誠的伙伴。他興奮地補充道:“不僅如此,因為大家都互相分享、協同合作,到最后并非只是某幾個人獲利了,而是所在領域的科學進展更快了、更有影響力了。”
科研之余,戴沛權喜歡音樂和書籍。有時工作疲憊,他就坐在鋼琴前彈一曲。助人的理念,不光體現在科研中,在生活中,他也總是不吝余力發揮才能。“聚會上需要我的地方,我都愿意去彈琴,陶冶自己,也陶冶別人。”那雙用來采集戶外信息、操作計算機設備、設計科學實驗的手,在彈奏樂器時,同樣靈動而自如。即興的、反傳統的、融合混搭的爵士樂,同樣為戴沛權所鐘情,正如對科學研究的品味一般,他喜歡那些不走尋常路、耐人尋味的事物。而廣泛地閱讀書籍文獻,則是他建立跨學科思維和進行跨科學研究,提高文化修養和專業素質的基礎,對戴沛權來說,亦是尤為重要。
(責編: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