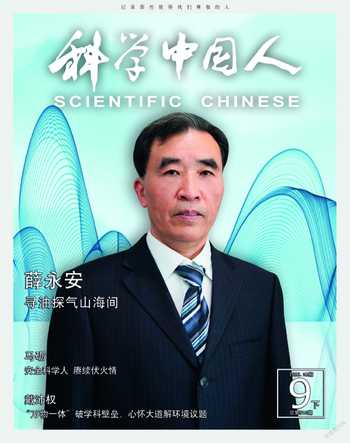龍門石窟
鄭心
龍門石窟,生病了。
自北魏(公元493年)始建以來,“剝落、風化、滲水”三大“病害”就開始在星霜屢變中日復一日地威脅著龍門石窟這座聞名世界的中國藝術寶庫。雖然在社會穩定后,國人對龍門石窟的保護工作一直未敢掉以輕心——1961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還是無法阻止自然對龍門石窟的侵蝕。龍門石窟研究院數代研究人員、工匠連同天南海北慕名而來的游客一起,親眼見證著佛像表面一點點生出由死去的苔蘚與滲水侵蝕、鈣質沉積渲染出的黑白斑駁。
終于,自2011年起,龍門石窟大修籌備工作陸續啟動。國內外30多名文物保護專家集聚洛陽,集體“會診”龍門石窟,尋找最佳的修繕與保護辦法。經過數次考察和研討,這些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單位的專家認為,此次修繕應重新制訂科學的保護規劃,采用新材料對巖體裂縫注漿加固,對溶蝕形成的空洞充填修補,科學有效地清除佛龕上的沉積物,以從根本上解決石窟“剝落、風化、滲水”等問題。據專家介紹,石窟區位于龍門山—香山裂縫地層,彼時許多洞窟上方及周圍已現出多條縱橫交錯的裂縫,其中潛溪寺有25條,賓陽北、中、南三洞有36條,古陽洞有29條,奉先寺的藥方洞也有7條。此外,伊闕佛龕之碑、極南洞外碑刻等露天石碑上的字樣,也已逐漸湮滅在歲月的滾滾風塵之中。樁樁件件都向世人表明:防治石窟“病害”工作已是刻不容緩。但如此龐大規模的修補工作,籌措規劃終非一日之功。
“望聞問切”
如果你曾在2021年12月以后到訪過龍門石窟,或許會為難見盧舍那大佛的神秘微笑而惋惜,但同時也許會為能旁觀國寶的“手術現場”而驚嘆:《“十四五”石窟寺保護利用專項規劃》發布的同時,龍門石窟奉先寺大型滲漏水治理和危巖體加固保護工程正式啟動。通高超過17米的碩大佛像周圍相繼布滿了“支架”,套上了面積約為6900平方米的綠色“手術衣”,新時代的能工巧匠們穿梭其中,力求用高科技設備幫助飽經風霜的佛像重新煥發容光。不僅如此,此次相關研究團隊還在奉先寺前方的廣場上布設了詳盡介紹此次大修的展板,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全社會了解、參與石窟大修,拉近公眾與國寶之間的距離。
項目計劃總歷時約228天。而事實上,這并非龍門石窟的首次“就診”。
往遠看,早至宋代,朝廷便設有專門負責文物、建筑的保護和修繕的“八作司”。龍門石窟中留有宋代題記多則,均與修復佛像有關——在盧舍那大佛佛座位置刻有“東八作司胡副使一十人修佛記”,明確記錄了當時修復大佛的10個人的名字和時間;就近瞧,50年前,1971—1974年,國家文物局牽頭實施奉先寺搶險加固工程,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內首個大型石窟維修加固工程。據當時參與此工程的石匠介紹,當年的佛像經過多年戰亂已是殘破不堪,洞窟千龕中幾乎每座佛像均有不同程度的損毀,狀況慘不忍睹。這一階段的加固維修有效防止了石窟圍巖和造像的倒塌崩落,使奉先寺群雕的穩定性得到了保證。
但昔年的科技條件畢竟有限,50余年間,危巖體與滲漏水問題依舊困擾著業界。簡單來講,危巖體是指石體經過風化產生的松脫現象;滲漏水則顧名思義。“龍門石窟的造像是雕在石頭上的,如果石頭‘生病,文物也會受到影響。危巖體不僅會威脅到文物安全,也可能砸傷往來游客,龍門石窟附近的巖體主要為石灰巖,受水的溶蝕作用影響明顯。”龍門石窟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中心主任馬朝龍補充道。
既然要“治病”,依照我國傳統中醫理論,那就先要講究個“望聞問切”。為精確識別、精準治理,在勘察設計與資料收集階段,龍門石窟研究院就組織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浙江大學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多學科專家學者參與其中,并啟用探地雷達探測、紅外成像技術、3D掃描測繪數字化技術等前沿手段,旨在為奉先寺設計一個量身定做的“診療方案”,力求修舊如舊。因此,雖然“修復手術”還未真正開始,但各種尖端工程設備已在各司其職:探地雷達利用天線發射和接收高頻電磁波來探測地下介質的物質特性和分布規律;微光圖像增強器用光電陰極將微弱的可見光和近紅外光圖像轉換成相應的電子密度圖像;熱像儀用若干個分離探測元組成的探測器列陣將紅外光轉換成電信號;最后由3D掃描測繪技術進行匯總編制……多方聚力之下,一幅滿載新時代科技成果的《奉先寺裂隙及滲水病害調查圖》應運而生,至此,諸多“病害”已無處藏身。
切脈問診,“病歷”已成,接下來便要對癥開具“藥方”。根據奉先寺地形地貌和裂隙滲水機理,研究團隊在慎重思考、縝密溝通后,決定采取封堵與疏導排水相結合的措施,并據此宗旨開具了“五大藥方”:利用大佛右上角的天然溶洞截斷和疏導裂隙水;在奉先寺山體頂部進行裂隙灌漿封堵,鋪設膨潤土防水毯;對山體頂部兩條規模較大的構造裂隙帶進行開鑿封堵治理;修整神仙洞內排水系統,把山體滲水沿自然垂直溶洞引導到伊河里;使用修復砂漿修整盧舍那大佛窟檐缺失部位,修整窟檐滴水線防止雨水倒流……“君臣佐使”,環環相扣,共同撐起了防止龍門石窟滲漏水的一把“保護傘”。
在“抓藥”上,施工人員同樣匠心獨具、玄機暗藏。他們特地將此次裂隙封堵材料換成了偏高嶺土類灌漿材料與新型修復砂漿,將加固的錨桿更換為含玻璃鋼纖維的新型錨桿。“這些材料近些年在龍門石窟日常維護工作中被普遍使用,經驗證,效果都比較好。如果像50年前,只用普通的水泥砂漿,配出來的灌漿材料含堿量會比較大,時間長了,再加上雨水侵蝕,容易發白,還會有鹽分不斷滲出來,覆蓋在文物表面,會對石像造成一些破壞。而普通的合成鋼,是目前市面上非常常見的材料了,與玻璃鋼纖維這種非金屬無機材料相比,耐高溫、腐蝕及強度上均處于下風。這就說明,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益處在工程上是可以得到直觀體現的。”龍門石窟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子龍說。
“上工治未病”
唐朝名醫孫思邈曾在《黃帝內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的基礎之上提出:“上工治未病之病,中工治欲病之病,下工治已病之病。”這不僅是在言懸壺之法,更是一語道破“未雨綢繆”的處事智慧。因此,龍門石窟研究組此次在對奉先寺進行大修的同時,還聯合多個院校和科研院所組成科研團隊,對奉先寺展開了詳細而全面的石窟寺考古工作,為下一次整修奠定理論基礎。
科研團隊運用了考古學的基礎理論與方法,并采用多種高科技設備,如微波水分儀、X射線熒光光譜儀、拉曼光譜儀、紅外成像儀、磁化率儀、筆氏硬度計、地質雷達及采用地震共振頻率成像、超聲波無損檢測等技術,深入探測并分析了盧舍那大佛表層含水率、表面顏料成分、巖石礦物成分、不同時段佛身表面溫度和佛身各部位磁化率、硬度、表層修補層厚度及佛身巖石完整性等表征文物本體客觀存在狀態的技術參數。令人驚喜的是,仰賴給石窟“體檢”的高科技手段,研究人員在大修之余竟然還真的收獲了多個考古新發現。
研究人員不僅在盧舍那大佛表面首次發現了金、銀等元素,還在奉先寺普賢菩薩表面發現了保留的不明白色物質,其厚度均勻,與巖石結合緊密,后經現場X射線熒光初步分析才知道,其主要成分為鉛白。鉛白,即堿式碳酸鉛,古代稱為胡粉、鉛粉或水粉等,在《天工開物》《本草綱目》中有確切記載。值得一提的是,鉛白是古代畫圖和化妝品的重要原料,因其自身具有化學穩定性高和耐候性好的特點,不但能為顏料附著、金箔黏結提供良好界面,也很可能為抵御自然風化發揮了一定作用。
不僅如此,調查結果還顯示,普賢菩薩的右眼保留了完整的琉璃眼珠,且為一整塊琉璃;而左眼眼珠是由兩塊琉璃拼合而成,如今只保留下外側一半,靠近鼻子一側的半塊已經脫落、遺失,且表面被一定的風化物所覆蓋。經過清理后可看出,琉璃呈暗綠色,質地均勻,熠熠生輝。根據初步測試,琉璃眼珠的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硅(石英)和鉛,與古代琉璃一致。琉璃素來被譽為中國五大名器之首、佛家“七寶”之一,奉先寺造像竟能跨越千年保存下大塊片狀唐代琉璃實物,絕世罕見。
這些發現讓世人第一次意識到,龍門石窟佛像在建造之初很可能“化了妝”,不僅涂了“粉底”,化了“彩妝”,甚至是戴了“美瞳”。而現如今,石像已被光陰賦予斑斑古跡,但即便如此,總會有人前赴后繼,為華夏瑰寶的延續而不懈努力。
重獲新生
在萬佛洞前室南壁,一名游客拿出手機對著一尊殘損的觀世音造像進行掃描,很快手機上就出現了一尊光彩奪目的造像——這尊觀世音像是國內首件通過數字技術虛擬復原的石質造像。
這座建于唐永隆二年的造像,歷來以其窈窕婀娜的身姿、細膩流暢的雕刻被參觀者譽為“龍門最美觀世音”“網紅觀世音”。京劇大師梅蘭芳當年游覽龍門時,就被這尊觀世音像觸發過創作靈感。
可惜這尊觀世音像的發髻下部至鼻子以上部位早已損毀不見,最能體現觀世音神態和氣度的五官部分缺失,極大影響了參觀者對觀世音菩薩慈悲與莊嚴的完整感知。“即使再高明的維修技術,也無法在石窟上再現這尊觀世音像當年的風采。”工作人員語氣中難掩惋惜。
但最終,還是科技讓昔日光華的復現出現了轉機。龍門石窟研究院信息資料中心主任高俊蘋帶領團隊,以20世紀初一些國外的探險家、學者、攝影師等人拍攝的觀世音像被破壞前的照片為依據,以學術研究為基礎,融合三維數字化技術、顏色檢測分析技術、傳統雕塑藝術等手段,結合同時期同類型造像特征,按照一定規則,對此觀世音像龕進行了造型的虛擬修復及色彩的虛擬復原,這才得以讓我們在手機上一覽佛像的“前世今生”。
令人振奮的是,這僅是近年來龍門石窟數字化的一個縮影。“數字龍門”是基于深厚的學術研究,將石窟考古、歷史、文化研究和現代技術融為一體的數字化工程,同時借助虛擬修復、增強現實、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手段,多方式再現窟龕造像的宏偉與精美。近年來,龍門石窟陸續完成了“龍門最美觀音像虛擬修復展示項目”“龍門石窟流散文物虛擬復位研究展示項目”“賓陽中洞窟頂藻井色彩復原項目”等重要的數字化項目,取得了豐碩成果。下一步,研究人員還將通過三維數字化技術,全面采集石窟文物信息,建立數字化考古級別的數字化檔案,實現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可以說,文物的保護與修復工程延續了古代珍貴遺存的生命,數字化則賦予它們“新的生命”。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們相信文物保護的效果會越來越好。并且,在這些滄桑的石像身上,人們可以看到時間流過的痕跡,這種痕跡也很美。歲月是一種力量。”龍門石窟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中心主任馬朝龍說。
“歷史是鮮活的、生動的,所以才是有趣的。通過文物數字化,我們可以把曾經失落的美好找回來,讓它永遠燦爛,永遠有生命。”龍門石窟研究院院長史家珍說。
而盧舍那大佛沉默不語,豐頤秀目,嘴角含笑,依舊端坐在如歌歲月之中。
(文章轉載自《科學家》2022年7月刊。責編:楊思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