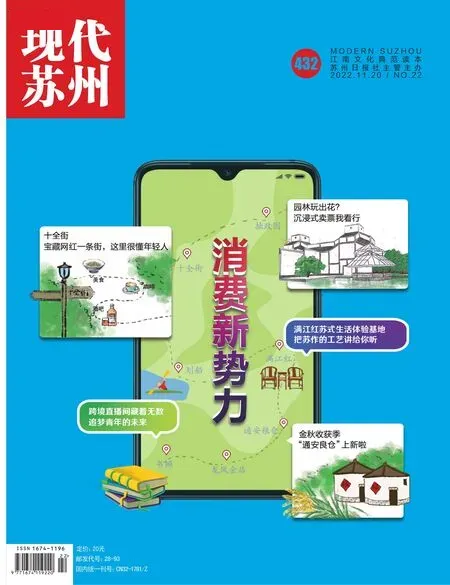新青年消費,從一只帆布包開始
記者 鄒孝聽

著名精神分析學家艾里希·弗洛姆曾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分析過現代社會的人都太孤獨了,充滿了不安全感、焦慮感和內疚感,而精神上的空虛最終只能靠物質上的不斷獲得來填補,這就導致人們通過被動消費、通過不斷購買新東西后來獲得滿足感和完整感。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也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出類似的世界:“今天能得到的快樂,絕不留給明天。”
消費主義在物質生活水平日趨飽滿的當代,似乎從未缺席。但近些年年輕人的消費觀卻在悄然發生改變,從過去的炫耀式消費到現在的個性化消費,哪怕只是一只旁人覺得再普通不過的帆布包,在主人眼里或許就是獨一無二的“私屬”,“正因為你我不同,方能顯示它的特殊”,你會發現,無論是消費方式還是消費習慣,當代新青年或多或少都帶有些個人印記。
拒絕消費內卷
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心理咨詢師岸光認為,職場人容易焦慮,往往是因為收入來源太單一,失業后,坐吃山空往往會令人沒有安全感。而對于岸光來說,就不會有這樣的焦慮,因為他的收入來源構建得較為多元,即使斷了一條路,也不會陷于沒有收入的狀態。
從職業初期用錢去體驗、學習、開眼界,到后期慢慢開始有存錢的意識,投資、理財、兼職……存款越來越豐厚,從10萬元、20萬元,直到存夠50萬元,岸光才有了些安全感。盡管50萬元算不上一筆大錢,但對于職場空窗期的他來說,可以支撐至少兩年的日常開支。在個人消費方面,他只買適合自己的,“有錢才有底氣,但也沒必要陷入消費內卷,自己喜歡就好。”
媒體人李不苦也是如此,擁有獨立的消費理念,每當在辦公室討論“啊呀,你皮膚那么好,用的什么品牌的護膚品”這類問題時,李不苦說出來的品牌總讓眾人漠然,因為那是一個國外的小眾品牌,早年間,李不苦出國讀研,所在的城市空氣十分干燥,一次偶然的嘗試,她用了這個品牌的護膚品覺得很適合自己,之后就一直回購。對于護膚,她有著自己的經驗,“大可不必盲目跟風,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這兩年,她攢到了一筆錢,即將投入新房裝修。
從盲目跟風到理性消費
拒絕跟風,才是理性消費的正道。
今年上半年,蘇州受疫情影響,很多人喜歡囤貨以獲取安全感,小詩也不例外,囤了很多零食,她說看見身邊的人都在瘋狂囤貨,總感覺自己不買點啥就很吃虧,但是東西囤得越多,消耗得就越多。“就像吃零食,本來完全可以不吃,但看見那么一大堆,就想去消耗掉,甚至有點故意要去消耗,這樣才給‘囤積’找到合理化的理由。”
再回頭看那段特殊的時光,小詩開始反省,“我們很多人可能平時都不太吃蔬菜,卻在疫情期間,一下子囤了很多蔬菜。其實真的沒必要,東西都是有保質期的,有很多東西,最后的歸宿都是垃圾桶,其實不用囤貨,按需購買,才是理性消費的正道。”

文藝青年丁一笑以前消費沒有節制,屬于享受派,用他的話來說,當賺錢很容易的時候就會想去體驗各種新鮮事物,吃好、玩好,也沒有考慮過儲蓄。但當事業受挫,斷了收入來源,“荷包”越來越扁,焦慮就會愈演愈烈。現在的他,消費趨于理性,“有多大能耐辦多大點事,當精力和財富都達到一個高度,再去把喜歡的事情做到極致。”
數字經濟催生新消費觀
從滿大街的同款名牌包到獨一無二的數字藏品,不得不說,數字經濟催生了新的消費觀。
小黃出于獵奇,在吳文化博物館的公眾號平臺購買了“又見江南”傳世盲盒的數字藏品,抽到一款影青小獅燭臺,實物是元代景德鎮窯采用二元配方原料后產品,二次創作后的數字藏品,只需要29.9元。“當時純屬瞎買,沒想到插畫還挺好看,30元的小快樂。”
丫丫,虛河藝術創始人,受疫情影響,從線下商業管理轉型線上業務,試圖以數字藏品模式作為流量突破口,打通線上線下閉環,用熱度較高的元宇宙數藏項目去賦能更多的實體經濟。
今年1月份,丫丫在阿里巴巴的數字藏品平臺“鯨探”購買了一款由四川博物院出品的“東漢陶狗”,售價19.9元,這是她第一次購買數字藏品,在她看來,這個模式可以很好地讓年輕群體接觸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探索中華五千年歷史瑰寶,數字藏品用更親民更有趣的方式,讓大家覺得藝術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博物館館藏,而是可以走進尋常百姓家的“收藏清單”。
事實上,數字藏品是“見山非山、見水非水”的藝術衍生版權作品,具備較強的收藏價值及社交屬性。“舉個例子,我們辦的首屆張大千數字藝術展。其中每一幅實物原作都是以億為計算單位,但是在我們把畫作經過二次創作后的發行價格都在百元以內,奢飾品具備較高的品牌價值及收藏價值。”丫丫如是說。

王大仙:貴的便宜的我都會買,喜歡就好
王大仙是出了名的美女,但凡見過她的,無不贊嘆她的樣貌。俗話說:“人靠衣裝,美靠靚妝。”王大仙從不濃妝艷抹、花枝招展,哪怕是素顏,一身黑白棉麻衣物,也能讓人賞心悅目。這大概就是不爭不搶,淡然自若的生活態度,練就了這般清新迷人的氣質吧。
人生開始做減法
讓她講講消費觀,她笑稱,貴的、便宜的我都會買,只要是喜歡的,看看賬上的錢,夠支付,那就不會多加考慮,人生難得,對自己好一點。“對自己好一點”是王大仙一直以來都秉持的觀念,只是這兩年她的人生開始做減法,喜歡的東西還是會買,但會考慮這件東西到底實不實用、能用多久?因為年輕時候的沖動型消費習慣讓家里多了很多“廢物”。
“上大學的時候,我很喜歡買衣服,學生時代沒什么錢,衣服買得也很便宜,一兩百元一件的,每個季度都會買。工作后,自己開始賺錢了,就去買那些快時尚品牌,款式新,平均兩周就有一次更新,性價比很高,我沒事就跟同事去逛街。隨著年齡增長,漸漸也有了一些財富積累,對衣服的品質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后來就會去逛買手店,可能在快時尚品牌能買十件衣服的錢在買手店只能買一件,但走在路上撞衫的概率幾乎為零。”
王大仙的穿著看上去很簡單,但每一件單品都搭配得恰到好處,年輕的時候喜歡各種新款,現在喜歡黑白灰基礎款,她說:“簡單的、經典的東西才能走得更遠。”
花出去的錢更值得了
或許是受職業的影響,王大仙的消費理念和習慣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改變。她原本是一名護士,偶爾的機會接觸到茶藝,從此與茶產生了緣分,辭職后,她開了一家小茶館,生活節奏慢了下來,她有更多的時間去找茶、品茶,茶葉的品質越來越高,茶具的價格也從最初的幾百元進階到一把壺就要上萬元。
與茶的緣分讓她更貼近生活、享受生活、感受生活,也對消費有了更深層次的認知。“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不同,現階段的我,相較于追趕潮流,更愿意把錢花在愉悅精神的事情上。我每年都會去山里找茶,找器具,這種尋找的過程讓你的花錢路徑變得更有意義,感覺花出去的錢都更值得了。”
王大仙最近購買了一把古琴,她說這把琴的價格足夠買一個名牌包包,但每當她彈起琴的時候,那種天人合一的境界,讓她的內心無比得平靜。
浮于表面的往往缺乏內涵
其實有些錢并非不舍得花,而是想要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去年裝修新房,她特意讓施工師傅留白閣樓外的露臺,一個人將五百斤的土一點一點地從一樓搬到四樓,一步一景,打造出一個絕美露臺。很多朋友都不相信這樣一處雅致小院完全沒有設計師的痕跡,然而這些的確全都由王大仙一個人完成的,甚至包括地板都是親自拼接的。
王大仙會不會花錢?會花。但她對消費有獨立的認知和規劃,“年輕的時候喜歡打卡網紅店,去了多了就會審美疲勞,千篇一律的裝修風格,這些網紅店好似‘內卷鼻祖’,浮于表面的東西往往缺乏內涵,一家沒有靈魂的店也就失去了再次造訪的意義。”
采訪末,B&O音響正在播放著20世紀90年代的金曲,經典之聲深入靈魂。

阿爆:消費觀的改變是因為變窮?當然不是
“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為錢犯過愁,想要的東西總能得到。在別人眼中,‘這個人不食人間煙火,對金錢沒有概念’,的確,基于對數字的不敏感以及骨子里的無欲無求,我在錢方面一直落落大方。只不過,近兩年我的消費觀發生了改變,起初我以為是自己越來越窮導致的,后來發現,根本不是,消費觀這種東西,其實是印刻在骨子里的。”阿爆如是說。
消費觀的養成,啟蒙于父母
從小到大,阿爆都是同學羨慕的對象,零花錢最多,一年四季總有穿不完的衣服,每次和同學出去玩,她總會搶著買單。阿爆是富二代嗎?其實并不是,她說是父母的消費觀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自己,“在我小時候,我的父母絕對不算是有錢人,但他們舍得花錢去體驗生活。”
在阿爆心里,有著這樣一幕記憶猶新的畫面:有一年,親戚的小孩10歲生日宴,宴席結束后,我爸媽包了4輛出租車,帶我親戚家的兄弟姐妹們“殺”到上海去吃夜宵,在那個不是人人都有車的年代,出租車都很少有人會坐,更別說跨城市打車了。
“我還記得我們去的餐廳叫‘紅子雞美食總會’,里面的服務生都是穿著溜冰鞋傳菜的,這在20世紀90年代絕對算是趕時髦。那時候我都不滿10歲,但如此新奇的體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爆說,長大后回憶起往事,爸爸告訴她那時候其實自己身上總共就2萬元,幾乎全花掉了,他當時沒有考慮很多,只是想讓大家一起盡興,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搶著跟男朋友買單的女人
的確,父母的帶領,讓阿爆比同齡人的生活多了一些別樣的滋味。她第一次有金錢的概念,大概是在小學的某個階段,零花錢突然緊縮,她不清楚具體原因,依稀聽父母提及家里財政或許面臨危機,“記得當時看見同桌在吃上好佳,特別饞,原本擁有很多零花錢的我,當下竟然連買一包零食的錢都沒有。”阿爆并沒有沮喪,而是有一些失落。
這樣的境遇很快就過去了,盡管后來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但阿爆的消費觀其實早已形成。大方,是給她最貼切的標簽,甚至對朋友比對自己還要大方。
“我出門有主動買單的習慣,因為我的父母是那種非常大方的人,總會把最好的東西分享給別人,哪怕只是陌生人。剛談戀愛的時候,和男朋友出去吃飯,我搶著買單,兩個人一推一搡,還把錢散到了地上,真的很好笑。后來我男朋友每次和別人講起這事的時候,總會說‘第一次碰到女人搶著買單的’。”阿爆笑道。
“拿鐵因子”下的消費降級
一向大方慣的阿爆,近兩年卻發現自己變得“摳門”了,“有一次我花了近3000元買了某品牌電吹風,寄來之后我發現顏色沒那么喜歡,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完之后竟還竊喜又省了一筆‘巨資’。”
很長一段時間,阿爆深以為是因為自己越來越窮,所以花錢才變得謹慎。買新衣服的時候不再會喜歡的款式連買幾件;逛超市的時候不再因為包裝好看買回一堆永遠不會開封的食物;以前三四千一瓶的護膚品閉眼買,現在只用基礎款……
但是,某些方面,她又是“花錢不眨眼”,比如為了喝一杯咖啡或者找一樣心愛的物件,她愿意買一張全價機票,去追尋內心的欲望。
美國金融作家大衛·巴赫在書中描述過一對夫婦,他們每天早上必須要喝一杯拿鐵咖啡,看似很小的花費,30年累計算下來在咖啡上的花費竟高達70萬美元。其實這些平日里看似不經意的花費,長年累月聚起來就是一筆不菲的財富。
阿爆讀懂了“拿鐵因子”背后的道理,開始審視自己的消費觀,其實消費降級表面上看是降級了,但實質上是另一種升華。“消費降級不是因為變窮,而是活得更通透了,想要找尋內心真正想要的東西。”

小詩:人生走到某個階段,會突然愛上攢錢和理財
老話說“衣不如新,人不如舊”。10年前,小詩在穿著打扮方面是絕不虧待自己的,衣櫥里掛著穿不完的衣服卻一直喊著“沒衣服穿”,每天一套新衣服,365天幾乎不重樣。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她無意間開始克制自己對“新”的欲望。“不是不買‘新的’,而是會把好質量關,利用好舊物,不再因為求新的習慣去拋棄那些舊物。”
小詩坦言人生走到某個階段,會突然愛上攢錢和理財,在某個拐點突然被鼓起的“荷包”驚喜到,也開始意識到,攢錢是為了把錢花到更重要的地方。
“準確地說,我是從2016年,我的小崽子降生后開始有攢錢意識的,慢慢地更進一步,學會了理財。”小詩在分享自己“硬核摳門”消費理念的時候,臉上滿是竊喜,流淌著的是平和的、灑脫的氣息。
食物,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小詩和室友曾經算過,如果他倆每天各點一杯咖啡或奶茶,到80歲的時候,這個家在飲料上的支出竟然高達90多萬元,“除去蜜雪冰城之類人均10元的以及星巴克之類人均35元的,取中間值人均25元,這么一算,一年下來幾平方米的房子就這樣‘喝掉了’,這個花費著實讓我們驚掉‘大牙’。”
最讓他們感到心痛的是,錢少了,肚皮上的贅肉卻要變成“救生圈”了。這些平日里看似不起眼的十幾二十幾元的消費,不經意間就會積累成一筆巨資。“這還沒算上外賣和外出吃飯呢!七七八八的小開銷都加在一起,那么又是一部小車要和你說拜拜了。”
以前很喜歡在各種五星級酒店饕餮的小詩,疫情發生以來,和室友學會了做飯,廚藝也精進了不少。“火鍋、烤肉、蘇幫菜……我們變著花樣地做,選擇優質的食材,價格卻比外面的餐廳更加低廉,吃完也不會出現不好消化的情況。特別劃算。”
公共交通,省錢出行首選
小詩不會開車,出行基本都靠公共交通,她算了一筆賬,從家到單位打車往返最少60元,軌道交通打完折6元都不到,高節能、低耗費,上下班路上還能打個盹,性價比超高!
當然,不下雨的時候,公交和電動自行車也是很經濟的選擇,“我喜歡和老公一起坐在公交車的最后一排,欣賞沿途的風景,盡管結婚多年,但每次坐公交車,依然感覺很浪漫;我也喜歡騎著電動自行車穿街走巷,既能鍛煉身體,又能更近地感知從小生活的城市氣息。”
其實,會過日子的小詩心中早有一本賬:開車成本不僅在于落地即貶值的價格,還有每年的保險,每月的油費,尤其是今年以來節節攀升的油價,室友的日常花銷有一半貢獻于此,另外還有違章、年檢、駕駛證換證、小事故的現金賠償、停車費等,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所以,她一直秉持一個觀念:公共交通,省錢出行的首選。
省去辦卡私教,選擇適合自己的健身方式
“今年夏天劉畊宏的直播刷遍了大江南北,各種劉畊宏男孩、劉畊宏女孩在家里就地健身、跳操。很多人一套‘本草綱目’‘龍拳’的組合操跳下來,大汗淋漓。其實我覺得健身不是非得去健身房,在家也能鍛煉身體……”
“我的好友小倫曾經辦過兩年健身卡,也請過私教,但是她告訴我,自己去了不超過10次,就堅持不下去了,‘五位數’就這樣離開了錢包。”
在小詩看來,運動需要堅持,如果有擼鐵習慣的小伙伴找一個離家或者公司近的健身房辦卡,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是像她這種偶爾“動動身體”的健身小白,完全可以家跟著視頻跳跳操,或者找朋友散散步、跑跑步,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新青年消費群像
◆ 向內探索
當代青年擁有獨立的價值觀,以自我需求為中心,相較于跟風,更多地詢問內心想要什么,然后去追隨什么。
◆ 省錢行家
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差不再成為裹挾當代青年消費的決定因素,各大社交平臺的分享,都能讓你找到“平替”,久而久之,成為省錢行家。
◆ 斷舍離
斷舍離是一種重新審視自己與物品關系的方式,日本、北歐等極簡主義對當代中國青年形成了一定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做減法,刪繁就簡成為時尚。
◆ 元宇宙居民
都市里的年輕人,尤其是藝術家、創意工作者等群體,對虛擬世界有著超凡的追求。從NFT到潮玩,95后、00后作為在數字化浪潮下成長的一代,對破次元壁的消費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熱忱。
◆ 國潮擁護者
在這屆青年身上,褪去了崇洋媚外的標記,擁護并追隨國朝,成為新青年的鮮明特性。
◆ 單身經濟
中國超2億人單身,獨居、一人食、一人游……單身經濟催生出獨特的消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