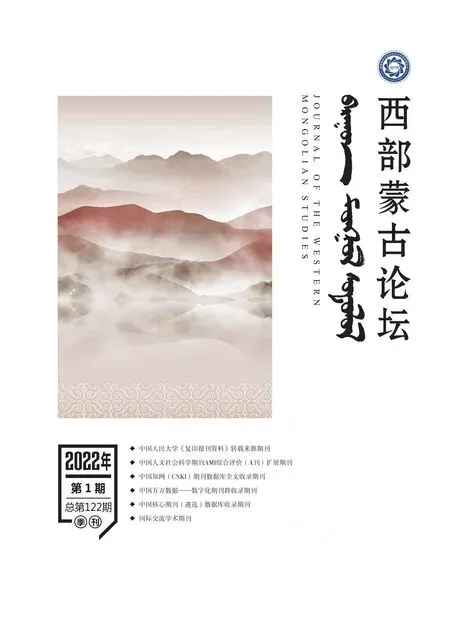國內族際通婚研究回顧與述評*
趙 靚
(西北民族大學 外國語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00)
[內容提要]本文從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兩方面對國內族際通婚的研究進行回顧與述評,重點梳理了族際通婚的通婚特征、形成因素和通婚所帶來的影響,呈現過去五十年間我國族際通婚的研究概況,以及族際通婚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積極促進作用,同時指出現有研究的成果及局限性,呼吁研究視角應結合除了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之外的其它學科,研究內容應包括更多針對婚姻質量、家庭關系的微觀研究。
族際通婚(intermar rige)是指兩個不同群體的男女個體遵循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的社會制度、文化和倫理道德規范,締結成婚姻,組成家庭。國外很早就出現了對于族際通婚的研究,產生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通婚的影響因素、通婚發生(或配偶選擇)的模式、族際通婚產生的影響,尤其以聚焦影響因素的研究最多(1)梁茂春:《什么因素影響族際通婚——社會學研究視角述評》,《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85頁。,并提出族際通婚中認同研究的重要性(2)羅紅:《人類學語境下的族際通婚與族群認同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3頁。。與國外的族際通婚研究相比,我國的族際通婚研究大多散落于族群關系、民族交往等研究主題之下,理論和方法論相對薄弱,沒有形成專門的領域。
一、理論研究
國內對族際通婚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從族群關系史入手,以族際交往和融合為主線研究中華民族整個族群關系演變的歷史。(3)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在這一針對民族關系進行的研究中,他對族際通婚進行了專門的討論,提出“雜婚”(即民族間的通婚現象)是中國各個族群之間較易于融合的主要原因。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人口遷移與流動速度逐步加快,民族關系也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族際通婚成為影響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4)宋興烈、徐杰舜:《族際通婚:一個影響民族關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龍勝里排壯寨族際通婚的人類學考察》,《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第26頁。。在引介西方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同時,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領域的學者對我國不同地域和民族間的族際通婚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
從理論方面來說,“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對族際通婚具有內在推力。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具有多元一體的特征,費孝通(1999年)指出:“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連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一體”(5)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頁。。馬戎是最早對西方社會學民族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引介的學者之一(6)馬戎:《西方民族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通過對中外族際通婚的理論和案例研究進行比較,以及對中國部分地區的族群通婚進行分析,馬戎提出了族群通婚影響因素分析的理論模型,包括族群基本特征、歷史關系特征以及兩族共處特征等三方面。族群基本特征涉及民族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族群界限清晰度、族群交往深度廣度等;歷史關系特征指族群交往關系的歷史;兩族共處特征包括族群居住格局、族群關系法律等。這一模型將個體層次與群體層次相結合,較為完整地歸納出了適合我國國情與民族實際情況的族際通婚研究理論與分析模型(7)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68頁。。陳長平(2000年)對北京牛街地區回族與其他民族混居(包括共居與通婚)的各種戶型進行了詳盡分析,并提出一種切實可行的定量分析多民族混居現象的方法(8)陳長平:《民族混居研究方法——以北京牛街回民聚居區為例所作的個案研究》,《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第55頁。。
二、實證研究
實證研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婚姻登記檔案等數據資料,針對通婚率、通婚模式的演變進行的宏觀統計研究;另一類是針對地區或族群就族際通婚的通婚率、通婚特征、影響因素、人們對待族際通婚的態度,及所帶來的影響等問題進行的微觀田野調查研究。
基于統計數據的調查表明,我國族際通婚的總量與比率呈增長趨勢,但有明顯的地區與民族差別(9)高穎、張秀蘭:《北京近年族際通婚狀況的實證研究》,《人口學刊》2014年第1期,第66頁。;2000—2010年間族際通婚戶的所占比例有所下降(10)菅志翔:《中國族際通婚的發展趨勢初探——對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與討論》,《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1頁。;其中一方為漢族的通婚率上升(11)鐘梅燕:《族際通婚與民族關系——一項關于明花鄉裕固族的實證研究》,《河西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第21頁。。另外,我國的族際通婚中普遍存在性別選擇傾向,并具有明顯的上嫁模式。而族際通婚子女對少數民族身份的選擇偏好推動了少數民族人口的年均增長率(12)郭志剛、李睿:《從人口普查數據看族際通婚夫婦的婚齡、生育數及其子女的民族選擇》,《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5期,第115頁。。
宏觀的研究還分析了影響族際通婚的因素。除了基本的民族特征、歷史關系等因素之外,還包括居住格局(13)李曉霞:《新疆族際婚姻的調查與分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第88頁。 馬戎:《西藏城鄉居民的擇偶與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35頁。、社會結構(14)何生海、白哲:《內蒙古西部地區族際婚姻的流動模式研究——以阿拉善左旗為例》,《內蒙古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第176頁。、民族間文化(如宗教信仰)差異的大小(15)馮浩楠:《新疆少數民族族際通婚的調查與研究》,《邊疆經濟與文化》2014年第10期,第54頁。、民族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民族人口流動比例以及城鎮化、女性地位的提高等(16)柯豪爽、沈思:《各民族族際通婚影響因素的統計分析》,《統計與管理》2018年第3期,第86頁。;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初婚年齡、文化程度、教育背景、職業、父母是否族際通婚者等(17)杜鵑:《從族際通婚看民族交融與發展》,《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7頁。。
除以上研究之外,很多實地調查研究從微觀視角出發,生動而深入地描述、分析了我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間族際婚姻的特征、形成因素、帶來的影響和人們的態度。這些可歸納為通婚特征、形成因素、通婚帶來的影響等三項內容,其中每一項內容都包括若干主題,詳見下述。
(一)通婚特征
1.擇偶機制發生變化
從婚戀方式、擇偶觀、民族觀以及對婚姻的滿意度等角度來看,族際通婚逐漸擺脫傳統婚姻的功利色彩而轉向注重兩情相悅、婚姻質量的模式,呈現出從實用主義過渡到浪漫主義的趨勢(18)許振明:《夏河縣拉卜楞鎮族際通婚狀況調查》,《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第194頁。。從通婚對象來看,族群身份在通婚中已非主要擇偶標準,族際通婚對象一方面呈現出以漢族為主的多元化傾向(19)鐘梅燕:《族際通婚與民族關系——一項關于明花鄉裕固族的實證研究》,《河西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第20頁。;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男多女少的新特征(20)姜海順:《朝鮮族民族通婚的調查研究——以延邊朝鮮族地區為例》,《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117頁。。
從通婚者的年齡特點上來看,馬戎在蒙古族和漢族通婚的研究中發現越年輕的蒙古族男性與漢族女性結婚的比例越高(21)馬戎:《民族與社會發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73頁。;賽汗發現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族際通婚夫婦的平均初婚年齡低于族內婚的平均初婚年齡(22)賽汗:《阿魯科爾沁旗蒙漢通婚現狀及其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研究》,內蒙古大學201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第38頁。。另外,馬戎在西藏的通婚研究中發現族際婚姻的夫妻雙方存在教育和職業的共性(23)1,即族際通婚夫婦的教育程度相近。
2.通婚率增長,通婚圈擴大
針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族際通婚研究顯示,族際通婚率呈增長趨勢,通婚圈逐漸擴大,民族文化融合增強,呈現出對族群界限的突破和對地域范圍的突破。對民族通婚的認同增強,有利于通婚率增長;多民族雜居區的族際通婚率呈現出常態化、規模化、民族多元化的特征。
族際通婚率的增長和通婚圈的擴大,一方面利于民族關系的親密與融合,另一方面也對少數民族自身的發展產生影響(24)12。需要指出,各民族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狀況差異較大;流動人口中女性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高于男性(25)13。
3.促進中華文化認同
作為衡量族際關系、文化融合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族際通婚反映族群深層次關系狀況。在通婚圈擴大化、通婚普遍化的基礎之上,族際通婚促進當地群眾的語言互動、習俗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共生的和諧局面(26)李金津:《族際通婚與文化交融——基于德欽縣茨中村的田野調查》,《邊疆經濟與文化》2020年第11期,第58頁。,而互嵌式社會結構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整個過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環節(27)張玉皎:《族際通婚與云南蒙古族的文化認同變遷——以通海興蒙鄉為例》,《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2020年第4期,第112頁。。族際通婚促進民族團結,為多民族、多文化地區人群提供了和諧共處的范例(28)董秀敏:《族際交往、族際通婚與文化交融:以拉薩“蕃卡契”為例》,《北方民族大學》2020年第5期,第62頁。,促進了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中華文化認同(29)馬富英,依烏,維色阿甲:《藏彝族際通婚與文化認同——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龍縣踏卡彝族鄉為例》,《民族學刊》2020年第5期,第36頁。。
4.族際通婚中的獨特現象
有些民族的族際通婚具有獨特的地域特色。例如,1988年在赤峰、2011年在義烏進行的通婚研究均發現,通婚雙方以各自傳統經濟活動為背景呈現出不同的“上嫁模式”(30)馬戎,潘乃谷:《赤峰農村牧區蒙漢通婚的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第86頁。,(31)馬艷:《跨國通婚、信仰與秩序——義烏穆斯林跨國通婚研究》,《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31頁。。另外,馬戎對拉薩市藏族和漢族通婚的調查發現,拉薩城區的通婚偏重于“男藏女漢”婚姻,而各鄉偏重于“男漢女藏”婚姻(32)馬戎:《西藏城鄉居民的擇偶與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39頁。。王志清發現“硬找蒙漢兼通的介紹人”等的獨特現象(33)王志清:《農區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際通婚及其演變——以煙臺營子村為個案》,《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第26頁。。斯諾發現當地蒙古族和滿族通婚中存在“族際通婚配偶原生家庭地域偏好”的獨特現象,并指出馬戎于1985年研究中觀察到的赤峰農村牧區蒙古族和漢族通婚中的“上嫁”現象在呼和浩特市的蒙古族和滿族通婚中并不存在,而這與呼和浩特市屬性以及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和滿族兩民族生產生活方式常年一致度較高有關(34)斯諾:《城市蒙古族與滿族青年族際通婚研究——以H市S區為例》,吉林大學,2015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第33頁。。
族際通婚的特征主要包括擇偶機制、通婚范圍、文化認同和獨特現象四個方面。通婚擇偶呈現出以家族利益為重到以個人感情為主的變化;通婚率增長,通婚圈擴大;族際通婚在更大范圍促進了更深層次的中華文化認同;而部分民族獨特的通婚現象體現出跨民族婚姻時代化、區域化的特征。
(二)族際通婚形成的因素
影響族際通婚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心理、自然等方面,語言、民族意識、社會地位、民族共存的生活空間及該民族在特定區域內的相對數量等對通婚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很多研究者都提出從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兩方面加以考量。
1.社會因素
(1)國家政策與民間習慣
人的婚戀行為受到婚姻制度的約束。婚姻不僅需要遵守國家政策、正式制度的規范,還要受到傳統習俗或習慣法的制約。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族際通婚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政府對族際通婚的干預也早已有之,“不同歷史時期統治集團對于族際通婚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社會場景和族群關系的不同態勢”(35)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38頁。。
中華民國初期,外族通婚禁忌在各地都很常見,族內婚也有復雜的形態。對各種民間婚俗,政府多半不與干預。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跨族通婚受到鼓勵,家庭革命等新觀念興起。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民法親屬編》和《民法繼承編》,自上而下地推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現代婚姻家庭制度,但影響范圍十分有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制定某些變通的或補充的規定,提請政務院批準施行。”1980年和2001年的《婚姻法》也設定了各民族地方可依具體情況加以另行規定的條款,政府宣傳及婚姻改革都推動了婚姻觀念的現代化發展。1980年起,一些限制、禁止族際通婚的地方政策開始松動。例如,1986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要求,婚姻登記的申請與發證之間設定間隔期;1996年,取消間隔期,任何干涉行為即為違法;民政部門需在雙方家長都不表示明確反對時才正式辦理婚姻登記手續(36)李曉霞:《國家政策對族際婚姻狀況的影響》,《新疆社會科學》2010年5期,第109頁。。支持個人婚姻自由的國家法和長期形成的民間習慣,在族際通婚上的沖突和對立,反映了族際通婚所代表的多元博弈和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國家通過運用政策的形式,創造了“和諧”“互補”以及“團體的多元主義”為特征的調適方式(37)杜社會、李劍:《族際整合中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沖突調適——以建國初期族際通婚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7頁。。
(2)人口流動與社會結構變化
城市化發展、人口流動增強、社會結構變化、經濟文化發展等因素對族際通婚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在內蒙古自治區默特地區都市化的過程中,工業化、都市化導致血緣、地緣紐帶和家族功能的衰退,使現代都市中的蒙古族對蒙漢通婚已基本趨于認同(38)麻國慶:《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都市化與蒙古族的文化變遷》,《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第91頁。。另一項研究中,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一個樣本量約一萬人的西部六城市流動已婚人口調查報告顯示,漢族被訪者中的2.3%為族際通婚,少數民族被訪者中的6.4%選擇了漢族作為婚配對象(39)馬戎:《中國西部開發中的人口流動——西部六城市流動人口調查綜合報告》,馬戎等《西部開發中的人口流動與族際交往的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66頁。。在貴州布依族村落中,通婚一方為外出務工人員的族際婚姻占很大比例(40)楊元麗、王順松:《從族際通婚看少數民族關系——以月亮河流域布依族為例》,《民族論壇》,2015年第6期,第37頁。。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蒙漢通婚夫婦的人口流動高于族內婚的人口流動,女性的人口流動高于男性的人口流動(41)賽汗:《阿魯科爾沁旗蒙漢通婚現狀及其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研究》,內蒙古大學,201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第28頁。。針對吉林省延吉市朝漢通婚的研究發現,族際通婚的增多受到文化變遷、受教育程度提高、居住格局變化及人口流動加快等因素的影響(42)全信子、王麗麗:《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研究——以延吉市朝漢通婚為例》,《東疆學刊》2018年第2期,第82頁。。
(3)文化與語言互動
在社會生活中,風俗習慣、親朋壓力及面子問題都對族際婚姻的實現產生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從青海省海晏縣的蒙藏通婚家庭來看,相似的文化習俗更容易促進族際通婚(43)元旦姐:《從族際通婚看海晏縣蒙藏民族關系》,《民族論壇》2015年第1期,第46頁。。另外,語言、民族意識也對族際通婚產生影響(44)蔡紅燕:《族際通婚背景下的苗族服飾文化認同——以云南昌寧土皮太村苗族為例》,《河池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第115頁。;地域差異和語言習慣等都是影響族際通婚的主要原因(45)阿布都哈德、馬琳娜:《“巴雜空”和“老東鄉”是歷史記憶、社會標簽還是族界標識?——基于臨夏回族與東鄉族族群關系的田野考察》,《回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頁。。
2.個人因素
影響族際通婚的個人因素,包括年齡、教育水平、職業、收入、戶口登記類別、遷移情況、掌握對方語言的能力、鄰居中是否有其他民族、有無其他民族的朋友(46)馬戎、潘乃谷:《赤峰農村牧區蒙漢通婚的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第81頁。。
綜上,影響族際通婚的因素可分為社會(客觀)因素和個人(主觀)因素。前者包括國家政策、經濟因素、社會距離、居住格局、民族文化(包括風俗習慣、宗教、語言)等;后者包括年齡、教育水平、職業、收入、戶口登記類別、遷移情況、掌握對方語言的能力、是否常與其他民族接觸等。也有學者提出,個人擇偶的因素對族際通婚的影響無足輕重,認為就跨民族婚姻而言,其族群特征和整體性影響的因素遠遠強于個體性因素;民族群體的各類特征和整體性影響的因素在族際婚姻的選擇中發揮主導性作用,這在群體性生存方式和部落制原始遺風保存較完整的民族中表現更加明顯(47)呂養正:《湘西苗漢族際婚之淤滯暨族群特征和整體性影響因素的拘制》,《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第152頁。。
(三)族際通婚的影響
族際通婚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民族關系、民族文化、人口結構等方面。
1.族際通婚與民族關系
族際通婚有利于促進民族關系、生產力提高、民族間溝通加強、感情加深,利于民族團結與融合,是現當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形成與維系的深厚基礎和重要支撐力量之一(48)魯剛、張禹青:《我國族際通婚的歷史軌跡》,《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18頁。。族際通婚可以增進民族之間的交往和友誼,但是有時也會給民族關系帶來困惑與挑戰。族際通婚中必然出現個人感情與族群文化之間的矛盾,而個體采取妥協是出于維系感情、維持族群歸屬感的需要,無數個體的妥協成為促使族群文化發生變遷的動力,有助于消溶族群邊界、跨越族群鴻溝、溝通族群心理(49)徐杰舜、徐桂蘭:《情感與族群邊界——以新疆三對維漢夫婦的族際通婚為例》,《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技版)2012年第2期,第138頁。。
族際通婚是民族關系和諧的結果,而民族關系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族際通婚的增長,兩者相互促進,互為因果。“血緣融合是族群融合的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途徑”(50)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32頁。。因此,對民間自發的族際通婚應輔之以相關政策鼓勵,為民族團結和文化交流增加一條血脈相連的人際關系紐帶(51)林超:《族際通婚與身份融合》,《民族論壇》2013年第6期,第60頁。。
2.族際通婚與民族文化
族際通婚促進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傳承,促進混合型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在多民族雜居區,各民族在保持和傳承了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吸納并融合了本地區內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呈現出多種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52)魯艷:《多民族雜居區民族邊界與民族關系研究——以湖南桑植為例》,2013年。。族際通婚促進了文化的適應與融合,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生動而豐富的機會和條件。
3.族際通婚與人口結構
大規模的族際通婚有利于民族人口數量的增長和人口素質的提高,但同時族際通婚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婚姻帶來沖擊,如未婚人口聚集、結婚年齡差距擴大等問題(53)韋美神:《改革開放以來瑤族通婚圈的變遷研究——以廣西田東縣隴任屯為例》,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第41頁。。
另外,族際通婚會帶來通婚子女身份的選擇困惑(54)李延禧:《跨越族群邊界:延邊地區朝漢族際通婚研究——敦化市個案為例》,延邊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第26頁。。一項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0到9歲兒童民族身份選擇數據的研究表明,族際通婚子女在選擇民族時,受到多個變量的影響,如民族政策、父母受教育程度、父親的民族、家庭戶口性質、家庭所在地的城鄉差異、子女出生的年份、家庭所在地是否為民族地區、通婚一方是否漢族,等等;我國的民族成分制度和民族優惠政策從制度上維系、強化了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族屬選擇的傾向性和生育的優惠政策使少數民族人口呈增長趨勢(55)高明英:《族際通婚子女民族身份認同的民族政策探析》,《廣東蠶業》2018年第1期,第127頁。。該研究指出,族際通婚子女的民族身份選擇隨父傾向與“偏少”(少數民族)“偏小”(人口較少)趨勢共存(56)周靖:《族際通婚子女的民族身份選擇狀況的統計分析》,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第15頁。。如蒙漢通婚子女多選擇蒙古族的民族身份(57)賽汗:《阿魯科爾沁旗蒙漢通婚現狀及其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研究》,內蒙古大學,201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第49頁。;裕固族與其他民族通婚時,子女的民族選擇多為裕固族(58)鐘梅燕:《族際通婚與民族關系——一項關于明花鄉裕固族的實證研究》,《河西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第24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59)習近平:《中華民族和各民族是一個大家庭與家庭成員的關系》,《民族論壇》2015年第10期,第1頁。族際通婚是民族交融的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民族團結,促進文化融合。民族關系的深化和文化的發展推動了人口數量和素質的增長,也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和凝聚力。
三、結 論
社會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人口流動、社會結構變化,民族交往增加了族際通婚的可能性,而族際通婚在全國范圍內,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快速增長,又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往與融合。族際通婚促進文化交流與融合,為新時代的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帶來有利影響。需指出的是,族際通婚的研究不能單純以通婚率來衡量民族關系狀況,還應結合通婚的婚姻質量、家庭關系等來綜合考察(60)楊曉純:《散雜居回族經濟與回漢民族關系研究——以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區為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1頁。。
我國的族際通婚大多是從民族學、社會學的視角探討,更多地傾向于考察某地區、某群體的通婚歷史、特征及影響。從研究回顧來看,除了從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進行考察之外,族際通婚的研究還需要結合更多其它學科的視角、方法,進行更加微觀的、個體層面的分析,以期獲得對族際通婚更加深入、透徹的理解,對選擇通婚的人群予以更多的社會寬容和人文關懷。同時,以族際婚姻為視角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對探討“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實踐路徑十分必要。通過族際通婚培育各民族間“手足至親”認同的重要力量,能夠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裨補助益(61)徐燕,丹曲:《西北民族走廊上的族際親緣關系研究——兼論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啟示》,《青海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