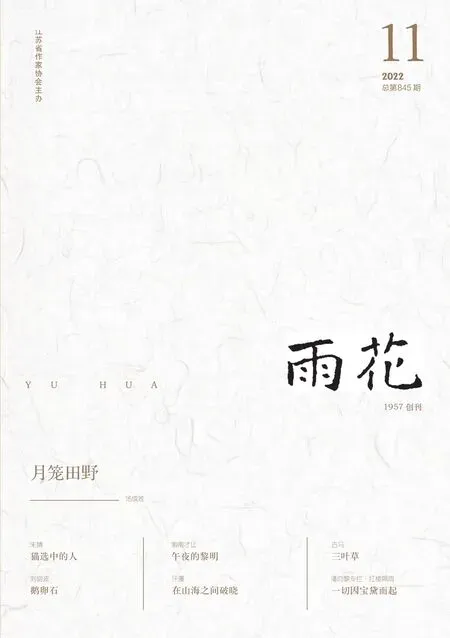蒼蠅在眼睛上爬
——說細節
翟業軍
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中有一篇《我的鄰里拉季洛夫》,寫的是“我”到地主拉季洛夫家做客的一些見聞。飯后閑聊時,不知為什么,“我”和拉季洛夫得出一個“人所共知”的見解:“一些最無關緊要的小事往往比一些極其重要的事給人的印象更深。”拉季洛夫借以佐證的例子,是他愛妻的死。他說,妻子死于難產,他難過極了,覺得自己肯定活不下去了。大家按規矩給死者穿衣服、焚香、祈禱,他也照例鞠躬、磕頭,但就是哭不出來,整個人是木的、沉的,像一塊石頭。第二天清晨,他來到妻子身邊,妻子從頭到腳被陽光照射著,亮亮的。突然,他看到她的一只眼睛沒有完全閉上,一只蒼蠅在上面爬。他一下子栽倒在地,醒來后號啕大哭,一直哭,怎么都控制不住。拉季洛夫所描述的是一個“知”與“信”從斷裂到合一的過程。一開始,他當然“知道”妻子已經死了,人死就不能復生;但他又怎么可能“相信”跟自己恩愛了三年、昨天還好端端的妻子就這么死了,她死了,他哪里活得下去?直到看到蒼蠅在她眼睛上爬,“知”與“信”瞬間合一:眼睛多么嬌嫩啊,再細小的沙子也揉不得的,而嬌嫩正是一種生命感受,越嬌嫩、越揉不得半點沙子就越說明生命感受之纖敏、細膩;可現在,蒼蠅竟然在她眼睛上爬,再多的沙子揉進她的眼睛,她都不會有什么反應了,她真死了,死透了。“相信”了妻子的死,他的世界一下子崩塌,心痛如搗。“信”所帶來的疼痛竟是如此銳利、異己,以至于在追憶“信”之瞬間的此時此刻,他還不由得哆嗦了一下——這是一種原初性、根基處的創傷,無論如何都縫合不了的。
“知”與“信”合一是一種領悟。領悟不是來自教訓,也不是來自于層層累積起來的體量龐大的苦難或者歡樂,而是來自蒼蠅在眼睛上爬這種“最無關緊要的小事”,或者叫細節。細節當然是細的,塵埃一樣,看起來“無關緊要”,實則就是矛盾,是裂縫,是爆點,從點燃到轟毀一切只需一剎那。俗話說,“針尖大的窟窿能漏過斗大的風”,想要看清楚滿世界翻騰的風,有時候必須回溯到“針尖大的窟窿”處的震顫。能漏進斗大的風的“針尖大的窟窿”,像極了我所要闡明的細節。需要強調的是,細節不細的辯證法,并非是“人所共知”,而是需要拉季洛夫或者說是屠格涅夫那樣的領悟能力和善意的。
再舉一個蒼蠅在眼睛上爬的例子,看看細節擁有何等的爆破力,是怎樣摧毀一個世界的。尤瑟納爾《東方故事集》里有一則故事,叫《柯內琉斯·貝爾格的悲哀》。柯內琉斯是倫勃朗的弟子,著名的肖像畫家,去南方、東方進行了一場漫長的游歷之后,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人們驚奇地發現,曾經那么爽朗、喧鬧的柯內琉斯突然沉默了、離群索居了,每天流連于煙霧繚繞的小酒館,只有酒精才能讓他的舌頭稍微活泛一些。更讓人錯愕的是,作為一位一輩子凝視、探索人的面孔的肖像畫家,現在的他冷漠又憤然地扭過頭去,不看任何人的臉。他甚至不再畫動物,因為動物太像人了。人們不免好奇:在游歷的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足以摧毀他、讓他再也做不回他自己的事情?小說接著說,柯內琉斯有時會來到一個狂熱迷戀郁金香的老人家中,只有他能用語言向老人描述那些看起來差不多的顏色之間的無窮差異。一天,老人向他展示了一盆世所罕見的郁金香,贊嘆不置:上帝是偉大的畫家,上帝是宇宙的畫家。柯內琉斯沒有說話,他想起自己浪游時見過的貧困住所,小酒館門口的毆斗,當鋪老板無情的臉,他的模特躺在弗里堡醫學院解剖臺上的豐腴、娉婷的身體,更想起在君士坦丁堡一個帕夏(奧斯曼帝國的總督或將軍)的大理石花園中看到的美麗得好像永遠不會凋謝的郁金香,受命展示這些郁金香的奴隸卻是一個獨眼龍,在他新近失去眼珠的地方爬滿了蒼蠅。柯內琉斯摘下眼鏡,說,上帝是宇宙的畫家,又悲哀地說,多么不幸啊,上帝不僅僅畫景色。我想,當柯內琉斯一路上看到那么多的吝嗇、愚蠢、兇狠時,他已經“知道”了上帝的不仁,但不仁的上帝不還是畫下了太多郁金香一樣的美好?有了這些美好,上帝說不定就是仁的?所以,對于自己的“知”,他并不全“信”。蒼蠅爬滿因為被挖去眼珠而潰爛的眼眶的細節就像一根毒箭射中了他,更何況這一細節還襯以完美的郁金香和永恒的花園——美好讓酷烈更酷烈、更不可承受,一個同時畫下美好和酷烈的上帝就是最不仁的上帝。“信”了上帝的不仁,他就沒有辦法再去直面人的面孔,因為人是上帝的肖像,也是不仁的,對著人,他覺得“惡心”。就這樣,一個細節摧毀了一個人的穩妥的世界,或者說,一個細節把世界的真相帶到一個人的面前,領悟了真相的人就是一個被詛咒的不幸的人。
侯孝賢電影的力量,很多時候也是來自細節的重壓。他多次說到《童年往事》中讓他一輩子都刻骨銘心的三個目光,一個目光就是一道鞭痕、一次領悟、一種成長的契機:一,母親從臺北手術回來,發現“我”亂花錢,她已不能說話,只能看了“我”一眼。二,父親去世,教友們在他的遺體旁唱圣歌,“我”哭了,哥哥回頭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說,這么壞的人,還會哭啊?三,奶奶去世,收尸人翻動遺體,看到她的背部已經潰爛,淌滿血水,便回頭看了“我”一眼。一再地潛回細節,把一些看似一地雞毛實則沉重甚至會爆燃的細節一一說給你,這就是侯孝賢的特點,更是德性。
關于細節,還有一些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說明。
從古希臘哲學開始,世界被二分為現象/本質、形式/內容,哲學的任務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分析有意味的形式以抓取被遮蔽著的神秘的內容。如此一來,哲學家就成了解謎人、掘藏者,他們的事業得以成立的前提,就在于一定有一個謎或者珍寶放在那里。謎或者珍寶甚至支撐著整個現象界,你可以質疑某個謎或者珍寶的真假、成色,但不能質疑存在著謎或者珍寶這種東西——這樣的謎或者珍寶就像是希區柯克的麥格芬之謎。到了斯賓諾莎提出“絕對內在性”(absolute immanence)概念,就一舉消解了作為現象界之根基的本質、內容,因為“一切事物在一切事物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某個外在于世界的超驗存在之中。拉康的精神分析更是一筆勾銷了主體的堅實性,“我”只不過是大他者進行詢喚、建構時所留下來的剩余、癥候。正因為“我”不過是剩余、癥候,“我”就沒有深處、背后以及那里可能潛藏著的本質、內容。探究這樣的“我”,就沒有辦法去解謎、掘藏,而是要撕開癥候,裸呈出原初的傷口。一個癥候就是一個細節,或者說,一個本真的細節一定能揭出一個癥候,這就使得細節必然具備兩個特點:一,細節就在表層,不必朝深處挖。侯孝賢多次提到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里所征引的霍夫曼斯塔爾的話:“深度隱藏起來。在哪里?在表面。”深度在表面,卻又是隱藏的,能否找到它,端賴你領悟的能力和善意。①深度在表層的道理,紀德在《偽幣制造者》中亦有闡明:“從事發掘的人,愈發掘愈深陷,愈深陷愈成盲目;因真理即是表象,神秘即是形象,而人身上最深奧的即是他的皮囊。”二,細節就是癥候,揭開癥候就是撕開原初的傷口,是疼的,沒法撫慰,需要耗盡一生去進行一場無望的修補。文藝作品中當然不乏溫情的細節,但溫情的細節大抵是枝節性、非本真的,本真的細節,就像蒼蠅在眼睛上爬,揭示的都是生命根本性的空洞,叫人如何不憂傷?
在捕捉細節方面,影像具有天然的優勢。偷拍、抓拍是對于對象的瞬間提取,被瞬間提取出來的對象就是對象本來的松松垮垮的樣子,而不是被語法編碼過的光滑、順暢的樣子。哪怕是劇情片,按照劇本走的,被拍攝的人、物依舊可能出現各種意外,從而溢出劇本的語法——侯孝賢、王家衛總是在等待可能卻又不可預料的溢出,就像是等風來。所以,影像本質上就是二元性的。二元性既是指向拍攝者和對象之間的斷裂,也是指向對象內部的斷裂,而斷裂就是癥候,就是細節。文字則不同。文字是一道能指的鎖鏈,遵循一定的語法,或者叫作者的意圖,一環緊扣一環地鋪展開去,總是光滑的、井井有條的,不會有斷裂,也不可能出現走神、跑調。這樣的文字本質上是反癥候的,因為反癥候,所以又是反細節的。就算作者試圖制造出一些細節來,這些細節也還是語法、意圖刻意露出的一點破綻、賣弄的一點風情,是淫蕩的(齊澤克的意義上)。這樣一來,一個最有力的作者就應該是一個最克制的作者:克制意圖,與語法作戰,讓對象自行呈現。布魯姆說,我們無法從屠格涅夫的“白凈草原”帶走任何單一的解釋性觀點。正因為“白凈草原”上沒有單一的觀點,才會涌現出眾聲,一個聲音就是一個癥候,就是一個憂傷的細節,就在眾聲雜沓、交錯之中,天意隱隱若現。沒有單一的觀點,并不是由于屠格涅夫的貧乏,而是出自他在天道運轉面前的絕對的謙抑,用布魯姆的話說,就是寫作時的屠格涅夫總是“被動的、充滿愛的、觀察入微的”。
解除語法、讓細節浮現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使用天真漢的視角,比如童年視角、外國人視角、傻子視角,因為天真漢沒有自身的語法,對象世界的語法還沒來得及或者沒辦法編碼天真漢,在天真漢的眼中,世界就是一個細節到處綻出的盛大的原野。1928年,沈從文在《新月》上連載長篇小說《阿麗斯中國游記》。這是一本連沈從文自己都“承認失敗”的書,歷來不為研究者重視。我卻要說,就是在這本書中,沈從文正式確立了他與湘西世界的關系:解除語法,讓自己成為“被動的、充滿愛的、觀察入微的”寫作者,于是,細節接連綻出,湘西世界開口說話了。解除語法的方法,就是用一個外國小女孩的天真之眼來看湘西——天真之眼僅止于看,而判斷是需要語法、意圖作支撐的。以天真之眼看世界,這一種作者與書寫對象的關系,幾年后的《從文自傳》有更直接、精準的總結:“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阿麗斯中國游記》中最讓人憂傷縈懷的“看”,是阿麗斯來到一個奴隸市場,好奇又驚詫地看著一樁她完全領會不了的買賣:經紀問一個看樣子不過三歲的小奴隸幾歲了,小奴隸“卻用了差不多同洋娃娃一般的低小清圓聲音”說,“朱”(苗語,六),眾人皆笑,她惱了,跟父親要證據。經紀向父親問價錢,父親為難,不敢說,她就用小得像米粉搓成的兩只手攏成環形,比擬兩百錢的樣子。為了表現自己的乖巧,她學城里的太太走路,像唱戲,走了一陣就不走了,望著眾人笑;照著拍子唱歌,是苗歌,送春的歌,雖然只有她一個人不明白歌中的用意。既已成交、畫押,阿麗思便走了,路上卻見到一個女人牽了一頭小豬過去,豬脖子上圈著一圈草繩。就這樣,沈從文揭出湘西世界的真相,真相就在湘西世界的表層,由一雙天真之眼看取,只要你看到了她的所看,你就撕開了一個個癥候,裸呈出一個個絕望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