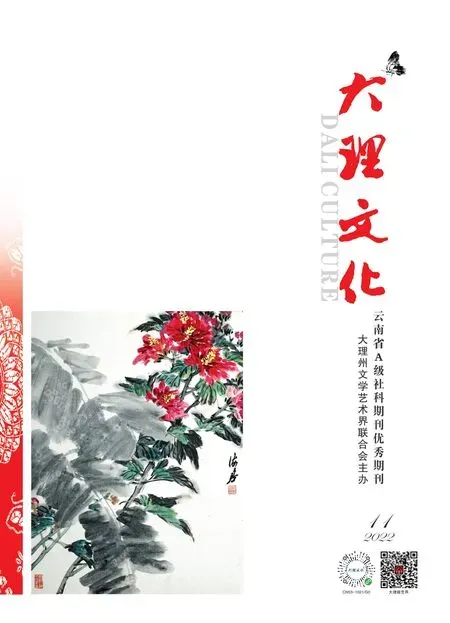宋湘與大理
●施立卓
1981年11月,正值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25周年之際,大理決定恢復州慶慶典活動。此前,我們供職于自治州文化局的幾個同好應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約,撰寫了《大理風情錄》,這本36開10萬字的小冊子,就是應當時介紹大理州情書籍缺如的急救篇。這本裝幀新穎的書一出版就深受讀者的歡迎,創下了先后接連印刷三版3萬冊的記錄。書中“歷史古跡”部分由我撰寫的《蒼山腳下“種松碑”》一文引起了廣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周錫復的注意,她專門寫信給云南出版社轉來一封信說:“讀了《大理風情錄》,很高興。因為我正在編注廣東清代詩人宋湘的詩集。他在云南待過13年,其間在大理當官。《云南通志·循吏》上有他的名字,他的詩篇不少是寫大理風情的。”1986年10月,《宋湘詩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先生專門簽名送我一冊,在前言《宋湘和他的詩》的結尾注明“云南省大理州文化局施立卓同志不遠千里寄示材料,僅此致謝”,并在引詩注中對此碑保存完好而表示欣慰。
其實在寫《蒼山腳下“種松碑”》時,我對這塊碑文并無太多研究,全是因為工作關系經常到大理古城大理一中,被校園南花廳豎立的這塊清碑的書法瀟灑自如別具一格所吸引,常常不由自主地撫摩古碑而贊嘆不已,而對詩碑的背景及其作者知之甚少。因此,周先生來信指出我的一些錯誤是情理中的事。她寫道:“你的作品中介紹宋湘的著作,如《紅杏詩鈔》以及紀滇詩集《滇蹄集》等有誤,詩集應為《紅杏山房集》,其中包含《滇蹄集》。”對宋湘的認識如此膚淺,使我汗顏。
《宋湘詩選》入選大理詩作兩首,除《卸迤西道事別蒼山洱海》外,就是俗稱《種松碑》的“三絕句”。《種松碑》的詩題很長:“前攝迤西道篆日,買松子三石,于點蒼山三塔寺后鼓民種之,為其濯濯也。今日有客報余,松已尋丈,其勢郁然成林者,予喜且感,系以三絕句。”全詩依據作者手書刻在一塊黑色大理石上,顯得十分典雅。
《宋湘詩選》前言寫道:“組詩寫于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永昌府任上,宋湘時年67歲。6年前,他代理迤西道時,曾買了三石松子,讓人種在大理三塔寺后面的點蒼山上,現在聽到那些松樹安然無恙,而且欣欣向榮、快要成林的消息,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興,但高興中又不免有點惘然若失,因為那樣如此美好的地方,自己現在卻只能‘神游’了。這組詩便抒寫了這種復雜的心情。這塊碑原豎立在大理崇圣寺三塔旁,后移置于大理第一中學校園南花廳內,至今保存完好,為當地名跡之一。”
這塊詩碑歷來名聲在外,研究者大多都認為今已不存世。據周先生的《宋湘詩選》中記載:1939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山大學從廣州輾轉遷至云南澄江縣,著名林學家侯過教授曾往游大理,專程訪《種松碑》而不得,賦詩云:“我本種樹人,來訪種樹碑。村隨斧斤盡,碑亦去何之?試問牧童言,遙指隴西祠。牧童莞然笑,老人默然思。伐木受其用,移碑留其詩;有用樹戕生,有碑詩永垂。”(《侯過詩選·訪種樹碑不得》)
侯過原名楠華,字子約,廣東省梅縣人。生于1880年,卒于1974年,享年94歲。著名林學家、教育家、書法家、詩人,中國近現代林業和林學教育事業上杰出的開拓者之一。
今天,如果侯先生在天之靈知道詩碑完美留存,他將會何等欣慰啊!
從此,宋湘及其詩成了我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課題。
嶺海天生磊落才
“嶺海天生磊落才”是嶺南人近代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并通詩文,喜藏書,搜集清代、近代詩文集近萬家2000余種的陳融在《讀嶺南人詩絕句》中對宋湘的評價。嶺海,指兩廣地區。
《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引《清史列傳》卷七二載:“宋湘(1756—1826年),清廣東嘉應人,字煥襄,號芷灣。嘉慶四年進士。由編修知云南曲靖府、永昌府。道光間,官至湖北督糧道。工詩,所作能自成一家面目。有《不易居齋集》《紅豆山房詩鈔》。”
除此之外,《廣東通志》《嘉應州志》《云南通志》《永昌府志》《大理縣志稿》都有宋湘的傳記,其中除介紹了他的生平外,還總結了他的才干與卓行。
歷史上,云南簡稱“三迤”。早在明朝就已經有了“二迤”之稱,當然真正作為行政區劃是在清朝。即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丙申置分巡迤東道,領云南、武定、普洱、曲靖、昭通、澈江、廣南、東川、開化、廣西、臨安、元江、鎮沅等十三府,治曲靖府:同時,改永昌守備道為迤西道,仍治大理府,領大理、鶴慶、麗江、永北、永昌、順寧、楚雄、姚安、景東、蒙化等十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月壬戌析迤東道屬鎮沅、元江、臨安、普洱四府往屬新設之迤南道,治普洱府。從履歷看,宋湘在云南期間曾代理廣南、大理、順寧、永昌、楚雄等府及迤西道尹,宋湘在云南為官13年,從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年)十月,抵曲靖,任知府;嘉慶十九年(1814年)秋,往廣南(轄境相當今云南省廣南、富寧縣地)任代理知府;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年)春,離開廣南;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春,赴昆明及大理;嘉慶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三月,代理迤西道員兼大理知府;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卸迤西道事;道光二年壬(1822年),代理永昌知府,后任楚雄知府。幾乎任遍了云南東南西北各地。
《云南通志》將宋湘列入“循吏傳”。所謂“循吏”,是指重農宣教、清正廉潔、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州縣級地方官,即“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的好官,也就是有卓行的地方官。在這方面,宋湘的表現是超群的,尤其是在云南期間。嘉慶丙子年(1816年),正逢云南大饑之年,疫疾流行,死者無數,就在這災情最嚴重之年,宋湘臨危受命,處理民生,在吏治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據地方志所載,宋湘在滇為官13年,他一直把精力用在吏治上。尤其是把薪俸大部用于振興地方公益事業,受到廣泛的贊揚。他初至曲靖,適水患之后,災黎遍地。不堪寓目,便領眾修城治水;后到馬龍州,見地瘠民貧,便捐出俸銀購新紡車500架和一批棉花,令其妻素云教婦女紡織,以解決人民的生活困難,人們感恩稱所織之布為“宋公布”。在廣南知府任上,見城內地高,飲用水困難,便捐款并親自勘測水源,鑿東、西二塘,引水至城,供百姓飲用。代迤西道尹時,地方大饑,瘟疫流行,他捐俸賑恤并組織百姓生產自救。在永昌府時,見永保書院久廢,捐俸銀170兩,修復之,促文教漸興。他在滇為官的治績,百姓莫不感恩戴德,當地人塑宋湘生像,建生祠,立碑祀奉。此外,“點蒼山造林”一事,尤為他最有意義的業績。
在文化成就上,宋湘還是清代卓越的人才,詩書創作皆屆眾。他的詩俊爽、沉穩,自成一家,藝術風格獨特,磊磊落落,豪放不拘。文采風流,生平著述甚豐,下筆顯倜儻雄奇之概,是清代中葉嶺南三大詩家之一,極為時人所稱頌,詩人黃遵憲曾以“我與芷灣是同鄉”而自豪。《清史列傳》:“粵詩自黎簡、馮敏昌后,推湘為巨擘。”《清史稿·儒林傳》載有其事跡,并評曰:“湘性豪邁,下筆顯倜儻雄奇之概,詩磊磊落落,自成一家。”全國著名學者、詩人錢仲聯題《人境廬》詩贊曰:“南邦屈(翁山)宋(芷灣)無前輩。”丘逢甲稱頌其為“紅杏花開第一枝”,是“嶺南詩派”出類拔萃的標桿。而且,他又是別具一格的書法家,擅長正、隸、行、草等書體,師王羲之、王獻之、米南宮集于一身,豪邁雄勁,如天馬行空,氣勢超凡,自成風格。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龍藏宋墨題詠》評曰:“芷灣長草書,章法磊落,筆致瀟灑,往往一紙書出輒為時賢所傾倒。”嘉應人黃岡壽贊道:“芷灣先生以書法名當時,零縑片紙,得之者拱璧不啻。”當時的人都以得到宋湘的親筆題字為榮,把其書法看作寶物一樣珍重。可見其書法的造詣深高。丘逢甲有詩贊他:“伯牙臺上記留題,更寫西湖五別詩。竹葉蔗渣俱妙筆,米顛書法杜陵詩。”是清代120名書畫家之一。他在大理所留的墨寶《種松碑》《蒼山詩碑》,都已成為重要文物。
總之,宋湘對云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極其熱愛。蒼山、洱海、大理三塔、滇池大觀樓、瀾滄東鐵索橋等,是他反復高吟的對象。宋湘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忘年十載此長安,閱盡榮華耐盡寒。我是何人須是我,真詩莫與外人看。”不論為官還是為文、為詩,他都用一顆真心去做;不論當多大的官,他都保持著一個“真我”,不被浮云蔽眼。當時他著名的詩作總集《紅杏山房集》及在滇所寫詩《滇蹄集》,就是滇任上(道光四年)付刻刊行的。《滇蹄集》記錄了他在云南的見聞和感受,反映出云南的風土人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滇蹄集》也揭示了邊陲民生之艱難和朝廷吏治之積弊,反映出宋湘作為儒士的擔當,可見其心憂天下并為之努力的儒士典范人格。
了解宋湘的詩作,有必要了解“嶺南詩派”。
嶺南詩派,是中國詩壇上著稱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詩派,也稱作“廣東詩派”或“粵東詩派”。前人論述嶺南詩派,每溯源于張九齡。汪辟疆稱:“嶺南詩派,肇自曲江。”曲江,指的就是張九齡,亦有學者把嶺南詩派徑稱“曲江詩派”。
宋湘是嘉應州第一個躋身于全國著名詩人行列中的佼佼者,被清朝嘉慶皇帝授封為“嶺南第一才子”,清代中期嶺南三大詩家之一,名列“梅州八賢”之首。
道光五年(1825年)秋,宋湘擢升湖北督糧道后才離開云南,道光《云南通志》載:“(宋湘)去滇時,送者流涕。”第二年,卒于任上,終年七十有一。
“蒼山洱海應笑我”
“蒼山洱海應笑我”出自宋湘卸任迤西道時《卸迤西道事別蒼山洱海》一詩中結尾的一句,最后一句是“不曾安穩作吟人”。這首詩是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他卸任滇西道赴順寧代理知府時所作,自謙因為公事而無暇對一直心儀的大理作更多詩所遺憾。
宋湘有關大理的詩,現存世的大致有《洱海行》《觀南詔碑有感》《迤西道衙齋即事》《自順寧返大理蒙化道中喜見點蒼山》《卸迤西道事別蒼山洱海》《種松碑》《蒼山詩碑》等數首,與其他幾首不同的是《蒼山詩碑》和《洱海行》并沒有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志之中,現僅留存碑刻,只有少數人知曉。其《洱海行》筆力穩健,一氣呵成,摘錄如下:
半年鹿鹿趨簿書,今日水邊提一壺。此水氣與蒼山驅,洱河洱海隨世呼。或言此水漢所摹,今昆明水非厥初。以事考之地或符,嬴顛劉蹶爭何愚。蒙氏段氏豈足道,蛟龍宮闕終模糊。書生得景且飲酒,海神勸客還烹魚。去年海魚不可廚,今年海魚鮮且腴。使君德薄口福好,禿筆力槁風格馀。瀛洲況復夙所到,神山何必拘厥墟。星辰日月天光趨,人民城郭近遠濡。蒼山數塔出天表,倒影窈窕沖瀜俱。譬如君住羅浮隅,蓬萊一股何容與。此水恨失眉山蘇,又惜老來襄陽徂。此水西湖比西子,不然虹貫滄江圖。使君來逢海色舒,海田黃稻香可租。年豐人樂坐無事,詩酒落手心膽粗。風月豈可使寂寞,山水自好誰親疏。使君長安多酒徒,南來萬里孤云孤。此邦沙子好詩手,同日李子能文儒。酒邊佳句誰最殊,神當贈之明月珠。神之言兮聽取無,江山自古人所扶。山東李白久不作,客復不飲胡為乎?城烏啞啞西日晡,高談深酌神應娛。云煙落紙擲海水,神乎謂我詩何如?
嘉慶丁丑(二十二年)十月十日程鄉宋湘,歲護迤西道篆,是日薄醉。
寫詩的這一年,宋湘代理迤西道員兼大理知府的事務,尤其是上一年丙子以來大理災情嚴重,可以說這是他臨危受命之舉。據記載,上年伊始至這一年三月,時值云南大饑之后繼以大疫,死者無數,他來到大理之后親自禱告于蒼山佛寺七晝夜,布錢散藥、捐俸銀。在詩中他寫道“去年海魚不可廚,今年海魚鮮且腴”時,特別注明:“去歲饑,有入海死者,予到榆,未忍食魚也。”因此,他哪有閑暇和心思游山玩水松散地領悟心儀已久的大理?到了這年的十月間,災情有了好轉,他才稍有閑心領悟這片被前人稱之為“樂土”的大理。金秋時節,他邀集當地二三名人在洱海西岸的浩然閣歡聚,“書生得景且飲酒,海神勸客還烹魚”,體現出一種輕松和“先憂后樂”的悲憫情懷。《洱海行》采用樂府歌行詩體,即篇無定句,句無定字,音節格律比較自由,句法長短不一,富于變化;唐以后的歌行一般用五言、七言古詩體裁格式,節奏上沒有嚴格要求,也不講究平仄,字數五言、七言為主,可參差不齊,可變韻。這種詩體亦稱古詩、古風,最能表現他此時此刻頗為輕松自由的心境。
浩然閣居洱海四岸四大名閣(天鏡閣、水月閣、珠海閣、浩然閣)之首。按李元陽(嘉靖)《大理府志》“勝覽”的記載:“浩然閣,在城東八里洱河西岸海神祠前,嘉靖十七年知府楊仲瑗建。”當時又名“天風海濤樓”。其實,這座閣歷史悠久,始建于唐代大理南詔政權時期,唐代四川名人閭丘均曾留下一首《臨水亭》詩:“高館基蒼山,微幕坐芳草。傍對野村樹,下臨車馬道。清朗發吟情,幽遐備瞻討。回合峰隱云,連綿渚縈島。氣以雪霜嚴,風為清春好。相及勝年時,無令嘆衰老。”后來浩然閣毀,清代修建為豐樂亭。這里是觀賞蒼洱風光、懷古幽思的好去處。
在《洱海行》中,詩人開宗明義說:“半年鹿鹿趨簿書,今日水邊提一壺。”他抒發了忙里偷閑的心境。此時此刻,宋湘面對浩眇的蒼山,他完全可能像先賢李元陽看到洱海時那樣抒發對歷史的感慨:“憶昔此水涯,建立多英雄。”或者如他此前的《觀南詔碑有感》那樣“自古不得人,言之涕淋浪”來臧否唐蒙段的功與過。他想以眼前的風光、友情、酒氣和魚味,以及稻谷豐收美景,營造觀光客的瀟灑和樂天。就像在《觀南詔碑有感》最后所表達的:“寄詩未游人,聊以當清話。飽餐濃淡色,一卷好圖繪。”景飽酒足,心懷愜意。詩末落款他特別提到“是日微醉”。俗語說,非酒落俗、爛醉如泥、薄酒啟神,微醉出詩意,這乃是純真性情紛沓而涌的自然流淌。
蒼山雪崦處,洱海日斜初。吏散開新甕,奴閑補舊書。清涼高樹鳥,歡喜老盆魚。欲問誰來往,詩人沙獻如。——《迤西道衙齋即事》
詩人勤政親民,尤其是他在大理期間,多事之秋只能“半年鹿鹿趨簿書”,在洱海“今日水邊提一壺”是多么難得的逍遙。《迤西道衙齋即事》則從悠然的心境反映他在公干之余的生活。衙齋指衙門里供職官燕居之處。但他不想像鄭燮《墨竹圖題詩》里那樣“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此時,嘈雜的公事已成寧靜,像往常一樣常客沙琛打開酒瓶,欣賞高樹上的鳥兒和盆中的金魚,悠然自樂。
在念天地之悠悠,思古之幽情時,他奮筆寫下了《觀南詔碑有感》:
下馬背斜陽,遺碑臥路旁。見是南詔字,抉剔苔蘚光。大半不可讀,似說武惟揚。曰詔閣羅鳳,其年天寶唐。大戰西洱河。唐兵八萬強,片甲不得返。傷哉來我疆。借問大將誰?節度使仲通;問詔一何恣?問詔一何狂。詔謂事體大,上有天蒼蒼。上數鳳祖父,事漢如事娘。下數鳳封拜,見天如見皇。叛唐而結蕃,鳳豈真犬羊。唐皇帝甚圣,唐皇帝甚明。鳳遠在絕徼,何以披肝腸。仲通爾何來,不究茲祻殃。生食張虔陀,厥肉亦不香。不問鳳所恨,不問鳳所當。長驅入我闥,不許鳳壺漿。困獸決一斗,豈曰無君王。吁嗟揭此碑,此碑何堂堂。蒼山與洱海,天地俱低昂。夷考西南夷,溯自漢所荒。是曰白子國,傳之蒙氏昌。細農羅以來,踆踆而蹌蹌。誰使并五詔,王昱實不臧。火烈星回節,遂謂雄無雙。詔從此滋大,詔從此哆張。猶喜鳳伽異,入覲聽笙簧。虔陀爾何人,天子授此邦。胡為乎株林,多藏況厚亡。仲通不解事,坐使蟲沙僵。呦呦萬人冢,鬼哭天昏黃。自爾三十年,邊患滋披猖。流血成海水,誰誅楊國忠。韋皋與贊皇,籌筆施鞍韁。稍稍靖厥氛,元氣亦已傷。此碑誰所為,苦心多慨慷。道是西瀘令,鄭回能文章。陽敘一戰烈,陰設千秋防。叛唐非得已,字字含風霜。圣人守四夷,不在略遠方。所以事羈縻,意使天下康。為胡折臂翁,痛哭云南行。自古不得人,言之涕淋浪。方今盛文軌,萬里同耕桑。此碑無所用,此義焉可忘。摩挲右手胝,城烏歸女墻。
作者在蒼山斜陽峰太和城遺址看到了字跡不清長滿苔蘚的南詔碑,這塊碑似乎表達了一種威武凌厲的氣概,“字字含風霜”地陳述了“天寶戰事”的殘酷與無奈。這引起了詩人的感嘆:“雖然‘今盛文軌,萬里同耕桑’,這場悲劇已過去了漫長的時光,‘此碑無所用’,但‘此義焉可忘’。什么義?這就是居安思危,歷史的教訓,防止慘劇重演。”如何記住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就是“右手胝”(反復邊沉思邊撫摸殘碑以致手起老繭),即詩最末一句“摩挲右手胝”。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9年),唐將李愬雪夜襲擊蔡州城,俘獲了當地節度使吳元濟,平定了歷時四年的淮西之亂。戰后,唐憲宗命作家韓愈撰寫了《平淮西碑》。立碑后,有人訴說碑文不實,憲宗就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詩人李商隱是同意韓碑的觀點的,他在《韓碑·元和天子神武姿》中抒發了韓碑流傳千古的不朽價值。詩末有“愿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我甘愿抄寫一萬本、吟誦一萬遍,哪怕是我口角流沫,右手磨出繭皮也在所不惜。希望韓碑流傳千秋萬代,好作封禪的祭天玉檢、明堂的萬世基石。)宋湘借用“右手胝”來說明南詔碑如同韓碑一樣具有不朽的歷史價值。“城烏歸女墻”,是說如果明了南詔碑的價值,那么就會回到烏鴉重回城墻的人間太平盛世。
卸迤西道事別蒼山洱海
雪鴻何處問前因?重記來時黯慘春。
佛供自憐同老婦,俸錢能救幾殘民!
半年道路無黔突,明日城門有去塵。
洱海蒼山應笑我,不曾安穩作吟人。
這首詩是宋湘卸任大理知府時所作。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秋天,宋湘卸任代理迤西道員兼大理知府時,反思任職半年來的見聞和感受,尤其是在災荒、疾疫的煎熬下廣大饑民生活的痛苦和自己工作的艱辛。他認為在有生之年有幸與蒼山洱海結識,這或許是前緣所定。他一來大理就碰上了令人黯慘的春天,無情的饑荒使生靈涂炭。于是,他只好像有憐憫心的老婦人一樣向佛爺獻祭祈禱,尋求庇護無辜的生靈。然而我這微薄的薪俸只是杯水車薪,效果有限。半年來,我就像孔子、墨子般躺的席未暖、煮飯的煙囪未熏黑,就要無功離去。啊,蒼山洱海應當笑我,沒有做一個安穩的詩人。這首詩情感沉重、樸厚率真,不惟深藏愧疚之感,且飽含勞人之怨。雖是平常之語,而情致綿緲悠長。
自順寧返大理蒙化道中喜見點蒼山
故山如故人,況復故人妙。
何能見妙人,不言亦不笑。
自我行三月,日苦亂山鬧。
今日蒙化山,始覺開展稍。
忽然見點蒼,百里外照耀。
雪光與云容,一豁一繚繞。
真乃峰丈人,西南扼其要。
豈惟氣象殊,精神可天告。
云雪亦常事,異境乃獨造。
夏杪雪微消,秋初雪已冒。
腰云初作帶,頂云旋成帽。
戎戎氣一合,漠漠峰在罩。
只言云可囊,誰知雪已窖。
凌虛出飛動,轉勢即深奧。
明入龍尾關,夕卷風頭纛。
即釣海上魚,去采山中芼。
蒼山之雪,五六月微消,間一二日,輒有濃云冒其頂,經宿云開,雪已補其所消,若不可使此山無雪也者。其為云也,無問晴雨,朝暮綿生,頃刻萬態,自吐自擁,半山以上,恒如覆被,偶一凈徹,雪故不消,又若深護其雪也者,真異境也。山上有龍池,產菜,呼為高河菜,味辛,微苦,春夏間人喜采食之。
順寧,清為順寧府,屬迤西道,駐今鳳慶縣城。宋湘三月代理迤西道員,兼順寧知府,是月往返大理和順寧之間。返回時路經蒙化(巍山),雖別離未久,然而一見點蒼山,他油然欣喜:真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幾天里他總感覺“故山如故人,況復故人妙。何能見妙人,不言亦不笑。自我行三月,日苦亂山鬧。今日蒙化山,始覺開展稍。忽然見點蒼,百里外照耀。”何等動情啊!接著以詩、詩不足以跋描繪了點蒼山的雪云異境。有趣的是還忘不了下關的風、洱海的魚、蒼山的芼(高河菜),很有情趣。這就是宋湘的大理情結。
西南雄闊地,蒼洱大名垂。眾壑雪同古,此峰云更奇。神靈趨白帝,風雨下金枝。莫問劫塵事,仙人方奕祺。——《蒼山詩碑》
過去有些詩選本將此詩歸為羅思舉所作,實際上是宋湘作并書寫,羅思舉的名字在碑刻最后并加了“識”字。所謂“識”是標記,也有作“志”,這說明詩落款“識”非作詩者。
詩首兩句寫蒼山洱海的地位,接著寫蒼山的雪和云奇觀:雪經年不消(前人稱為“太古雪”),中和峰的云更神奇。除了自然條件優越,點蒼山又是宗教名山,唐朝前期是道教名山。唐朝貞元十年,唐代大理南詔政權和唐臣“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岳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的會盟地點就在當時的蒼山神祠,即道教神祠。白帝,古神話中五天帝之一,主西方之神,“趨”指恭敬。于是,詩人寫道:在造化之神歸順的中岳蒼山煙雨景色中,使人不禁沉思。俱往矣!別去關心“劫塵的事”(佛教稱一世為一劫,無量無邊劫為塵劫。后亦泛指塵世的劫難),光陰流逝,世事變遷,就如同“柯短忘歸”的典故。“柯短忘歸”,傳說在西晉時有個叫王質的青年農民,一次上山打柴,見兩個小孩正在下圍棋。王質素好下棋,被兩位小孩精湛的棋藝一下子給吸引住了。看完一局棋后,小孩對王質說:“該回家了。”王質俯身去拾斧子,想不到斧柯(斧柄)已經爛朽,只剩下鐵斧了。王質回到村里,連一個人都不認識。經過詢問,才知道當年的熟人已經死去一百多年了。這就是《楞嚴經》所說:“縱經塵劫,終不能得。”
種松碑
不見蒼山已六年,舊游如夢事如煙。
多情竹報平安在,流水桃花一惘然。
古雪神云看幾回,十周柳大白頭催。
才知萬里滇南走,天譴蒼山種樹來。
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棵松。
何時再買三千石,遍種云中十九峰。
宋湘初到大理,矚目蒼洱壯麗山川,同時目睹往日林木蒼郁的點蒼山,變得濯濯童山,光禿孤爪,連洱海也只剩一池“死水微瀾”。于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竭盡全力,捐俸購買了松子三石,親率官吏士卒,組織民眾上蒼山植樹。幾個月后,松苗破土,茁壯成長,滿目瘡痍的蒼山披上了層層綠被。轉眼六年后熟人來信說,他種下的松“已尋丈,其勢郁然成林者”,于是他很激動,“系以三絕句”。這三首絕句被有心人刻成詩碑,流傳下來。
作者于1816年任駐大理的迤西道員兼大理知府,到接報時首尾已經六年,逝去的日子如夢如煙。朋友動情的來信。他由喜生悲,恍如離開了桃源仙境似的,感到很惆悵。這里的“竹報平安在”是指平安家信,典出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支植下》“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是作者對大理的深情。古雪神云為點蒼山勝景,“看幾回”透露出他對此的癡情。從“十圍柳大白頭催”中,我們能一窺作者的心境:“瞬間,六年前播下的松子已經成林,而種樹人隨之成了白頭翁。歲月無情啊。如今我才領悟到,千里跋涉到邊陲,原來是上天派遣我來蒼蒼種松的。”“十圍柳大”典出《世說新語·言語》:“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一枚松子種下土中,就如同道家將一粒封進煉丹爐,是多么神圣;什么時候我還有時光再買三千石松子,遍種在蒼山十九峰上呢?
宋湘對大理的深情厚誼,在詩中表達得如此淋漓盡致、磊磊落落,“蒼山洱海應笑我”只不過是謙辭罷了。
編輯手記:
宋湘,今廣東梅州人,已近花甲之年時,外放為曲靖知府。此后的十三年間,宋湘遍歷云南,并熱愛上了大理的山山水水,用筆墨記錄下他在大理的生活和感悟。本文作者熱愛于研究宋湘及其詩作,這項研究成為他“揮之不去的課題”,數十年沒有中斷。文中,作者通過對宋湘詩作的解讀,將這位清代文人對大理的熱愛呈現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