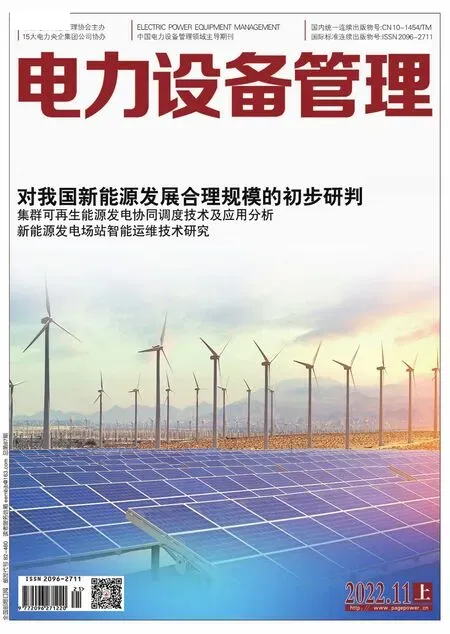數字技術推動發電行業綠色低碳轉型
山東電力工程咨詢院有限公司 尹書劍 段忠峰 張明陽
化石能源的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在全球碳排放構成中,電力及熱力行業碳排放占比42%、交通碳排放占比25%、工業碳排放占比18%。我國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約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85%,電力行業占能源燃燒二氧化碳的44%,在各行業碳排放中占比最高,控制電力行業的碳排放是推進碳減排的重要途徑[1]。
1 數字技術賦能綠色低碳發展
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全球日益興起,數字技術與各領域業務深度交互、融合,成為推動生產消費綠色化、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在“雙碳”背景下,實現能源結構的綠色低碳轉型,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已成為行業發展方向。數字技術通過與發電行業的深度融合,將在促進新能源并網消納、提升發電效率及安全可靠性、助力智慧能源系統構建、驅動新型技術創新發展等方面賦能發電行業綠色低碳發展。
1.1 促進新能源并網消納
目前新能源已成為我國裝機增長主力,風電、光伏具有波動性、間歇性的特點,轉動慣量、抗擾動能力及電壓調節能力低,大規模新能源接入將增加電力系統不確定性,對電力系統消納能力提出挑戰。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增加以燃煤電廠為代表的靈活性電源的調峰深度和負荷響應速率,優化“風光水火儲一體化”等多能互補能源基地聯合調度,促進分布式能源系統中燃機、新能源、儲能等能源的耦合度,充分發揮系統中靈活性電源的調節能力,能有效解決新能源并網消納問題。同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對天氣、電力生產進行預測,為新能源機組組合和調度做好預案,提升能源系統整體效率,促進新能源消納。
1.2 提升發電效率及安全可靠性
運行控制優化方面,數字技術能挖掘發電廠海量數據價值并加以利用,進而指導機組運行及控制。數字控制系統通過在多邊界限制條件下的參數尋優、控制優化,提高控制精度,有效提高機組經濟性和環保性的同時,避免人為失誤。設備狀態監測方面,采用先進數字技術開展發電設備狀態在線監測和故障智能預警及診斷,能有效提高機組運行的安全可靠性。基于人工智能和圖像識別等數字技術的智能機器人和無人機,已在火電、核電、新能源等領域得到應用,主要用于電廠設備狀態監測、巡檢、特種檢修、險情治理及綜合提效等方面,有效提高作業效率,增強設備的安全可靠性。
1.3 助力智慧能源系統構建
智慧能源系統是具有全面感知、全面互聯、全面智能、全面共享等特征的新型智慧生態能源系統。發電側作為電力系統重要環節,數字化轉型是助力智慧能源系統實現橫向多能互補、縱向“源網荷儲”高效互動,促進能源供給和需求的有效匹配的關鍵驅動。在源側,通過靈活發電資源與清潔能源間的協調互補,解決清潔能源發電隨機性的問題,增強系統自主可調性。在源網協調方面,通過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優化電源、電網協同運行,解決新能源大規模并網及分布式電源接入電網的問題。在源荷互動方面,基于用能大數據挖掘建立市場機制充分調用社會調峰資源,將負荷的柔性變化作為平衡電源波動的重要手段。
1.4 驅動新型技術創新發展
數字技術融合“能源”與“數據”兩大要素,有效驅動以虛擬電廠、區塊鏈、智能微電網為代表的能源行業技術發展和商業模式創新。虛擬電廠通過先進的控制計量、通信等數字技術聚合分布式電源、儲能系統、可控負荷等不同類型的分布式能源,在提高供電可靠性的同時,使更多要素參與電力市場和輔助服務市場運營。區塊鏈技術可提供公開、可靠信任體系,電力市場參與主體可通過區塊鏈智能合約參與市場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同時區塊鏈技術為創新綠色能源認證、綠色證書等新型商業模式的推廣提供可能。基于數字技術的智能微電網可有效地實現配電系統功率的平衡與控制、能量優化、分布式能源裝置故障檢測與維護等功能,提高系統可靠性和彈性,增強能源綜合利用效率。
2 數字化轉型問題及挑戰
“雙碳”目標對發電行業數字化轉型提出新的挑戰。我國新能源開發消納面臨開發布局與消納市場不匹配、發電特性與用電特性不匹配、電力系統調節能力建設相對滯后等矛盾,大規模、高比例新能源并網改變了電力系統運行機理,增加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風險。目前傳統調度運行體系、電網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尚未適應新能源大規模接入、源網荷儲雙向互動以及靈活的電力市場環境,亟需應用數字技術實現多能協同供應和供需雙側的智能交互。同時新型電力系統建設需與其發展需求相適應的算力規模、專用算法,以滿足新型電力系統的新能源預測/監控、電網規劃、電力電量平衡、頻率控制等應用需求[2]。
數據壁壘尚未打破,限制數據價值的充分發揮。行業產業鏈上下游間(如發電企業與電網企業、設備制造企業)、同企業不同企業間(如發電集團之間)、同企業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能力還有待實現。部分企業內部生產實時數據與相關管理數據在存儲、應用方面處于割裂狀態,數據、業務、管理未真正實現互聯互通。數據的關聯方交叉復雜,數據權屬不清晰,信息孤島及數據割裂狀態增加了數據共享及利用的難度,降低了可挖掘出的數據價值。如電廠設備缺陷、生命周期參數等數據與設備制造廠的設備材質、質檢、流水線信息等數據是割裂的,導致電廠難以做好設備狀態監測及壽命管理,制造廠也難以改進設備制造及性能。
尚未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數據采集質量不足。數據是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驅動要素,但是發電行業數據標準及采集工作仍有較大進步空間。數據質量及采集方式、范圍缺乏統一標準,不同廠家不同設備的通信接口及數據類型各不相同,尤其是進口設備的數據接口和數據格式封閉性較強,增加了數據標準化的難度及成本。此外,部分電廠配置傳感器數量不足、設備智能化程度不高,尚未實現實時數據的全量采集,數據的時效性、準確性、可信度不高[3]。部分企業由于相關信息系統應用時間晚,對相關數據記錄管理不足,導致數據可用性不高,在進行故障診斷、檢維修策略分析等需要知識庫的環節要依靠外購的知識庫,而各廠家也普遍將此類知識庫作為核心資產,只能通過服務的模式或有限的進行輸出。
缺少電廠數字化智能化行業技術標準。關于電廠數字化、智慧化、智能化的國家及行業標準尚未出臺。國家能源局2016年發布《智能水電廠技術導則》,中國自動化學會發電自動化專業委員會2017年發布《智能電廠技術發展綱要》,中電聯2018年發布《火力發電廠智能化技術導則》,但現有導則或綱要的權威性距離國家或行業標準仍有差距。行業對數字電廠、智能電廠、智慧電廠的名稱及內涵仍有分歧,重復研究及投入依然存在。
電力系統安全面臨挑戰。隨著海量異構設備接入,在給用戶帶來便利服務體驗的同時也造成了網絡邊界模糊的問題。海量異構設備接入,在給用戶帶來便利服務體驗的同時也造成了網絡邊界模糊的問題,,現有的安全防護體系尚無法完全應對當前逐步升級的攻擊手段。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數據、用戶核心數據經由網絡進行交互傳輸,風險防控難度加大,電力系統愈發成為黑客們高價值的攻擊目標,不僅會對能源電力企業自身的業務、信譽和經濟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甚至可能影響能源供應,進而影響生產安全、社會安全、甚至國家安全。
缺少適應數字化轉型的復合型人才。隨著數字技術在發電行業的融合應用,單一型人才已不能滿足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需要,橫跨多領域、學習能力更強、綜合素質更高、既懂發電又懂數字化的復合型人才相對欠缺。部分企業對數字化部門的職能定位為信息系統的建設、維護和管理部門,管理團隊的業務知識結構、組織能力、業務邏輯主要以企業現有的傳統業務架構為主,缺乏足夠的新模式和數字業務運營經驗,難以實現新業務模式和商業模式的突破。同時尚未建立數字人才的培養和賦能體系,內部知識沉淀和共建共享不足,缺乏對全員數字素養提升和能力提升。
3 相關政策建議
創新合作機制,推進產學研用深度協作。組建“發電行業數字化創新聯合體,采取產教融合模式,推進多學科交叉研究,實現產學研用聯合創新,實現“卡脖子”技術研發突破。在發電行業開展數字化綠色化轉型企業試點和場景示范工作,樹立轉型標桿,歸納總結領先發電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功經驗、典型模式和實現路徑,推動形成一批建設指南、標準或工作手冊,推廣標桿企業成功模式。
打破數據壁壘,構建數據共享開放平臺。基于國家級能源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運營的成功經驗,結合當前我國充分發揮數據價值、打破數據壁壘的發展需求,構建由主管部門牽頭、多方參與聯動的國家級發電行業數字化數據信息共享平臺,推動發電行業數字化深度融合發展。
補齊短板漏項,統一數字發展標準體系。結合《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十四五”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國家標準體系建設規劃》的具體要求,由發電行業主管部門與標準化主管部門聯合組織開展“十四五”發電行業數字化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
筑牢安全基礎,防范化解系統安全風險。由主管部門牽頭成立發電行業數字化安全管理部門,構建發電行業數字化安全監督管理體系,在推進立法、制定政策、細則配合等不同維度推動發電行業數字化安全體系建設,筑牢行業安全基礎。健全完善安全應急事件預警通報機制,提升發電行業數字化安全態勢感知、威脅發現、應急指揮、協同處置和攻擊溯源能力。
強化人才培養,組建梯級優質人才體系。組建發電行業數字化人才培養路徑與實施方案研究團隊,梳理我國發電行業數字化人才發展面臨的困難挑戰,對比國內外先進經驗,推進發電行業數字化人才體系建設。推動高校學科設置改革,促進發電行業與數字化行業的人才培養融合發展,加強職業院校的發電行業數字化技術技能類人才培養,深化數字經濟領域新工科、新文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