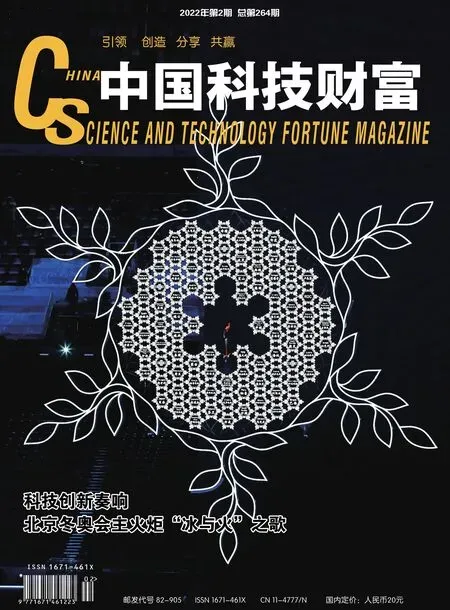社會需求驅動新科技革命
文/邵春堡

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70多年來,科技持續(xù)、全面、多點、迭代爆發(fā)。科技的發(fā)展遵循了事物演化的客觀規(guī)律,也體現(xiàn)了社會需求對科技的驅動。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從低到高有5個層次,在低層次需求滿足后,高層次需求就會出現(xiàn)。社會需求和人類愿望是現(xiàn)代科技涌現(xiàn)的源頭活水。面對科技的累累碩果,追溯科技產生的軌跡,對于理解科學家的創(chuàng)造動機,正視科技正負面影響,珍惜和應用現(xiàn)代科技具有重要意義。
尋求更便利、更廣泛的聯(lián)系
20世紀中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電子信息技術的應用和自動化生產,自然會產生大量數據,使之后升級的信息通信科技,更多地與大數據相關,突顯了數字科技發(fā)展的邏輯和地位。
殖民地國家在二戰(zhàn)后紛紛獨立,它們?yōu)榧訌姀V泛聯(lián)系,在發(fā)展電話、電報業(yè)務基礎上,尋找更便利的聯(lián)系方式,使電子通信科技發(fā)展成為社會的普遍愿望。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加速發(fā)展,跨國企業(yè)和資本,為擴張世界市場,抓住瞬息萬變的商機,對便捷的聯(lián)系方式有著強烈的期望,迫切尋求更先進的信息通信手段,數字智能科技更新迭代之快,與資本不斷地投入研發(fā)分不開。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認為,經濟全球化可被看作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信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
期待公平競爭、共享發(fā)展的解決方案
經濟實力薄弱和科技較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面對全球激烈競爭,遇到的風險和挑戰(zhàn)更加嚴峻,急需建立公平合理的經濟秩序,以保證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技術方面也期待共享發(fā)展的解決方案。現(xiàn)在的網絡共享和平臺共享,以及數字智能科技的通用性,或許就與這些需求有關,具有共享性能的科技出現(xiàn)絕非偶然。互聯(lián)網、區(qū)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起源于某些發(fā)達國家,但是它們天然具有全球性,沒有全球鏈接,沒有廣泛使用和共享,這些科技就變得非常狹隘和蒼白,也將失去技術的價值和意義。
改變環(huán)境惡化和能源短缺的愿望
工業(yè)革命以來,石油滾滾、機器隆隆、煙囪林立,都被看作是工業(yè)社會的繁榮景象。經過兩百多年發(fā)展,現(xiàn)在人們越來越感覺那些表面的繁榮,恰恰是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資源過度開采、氣候變暖的罪魁禍首,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如果繼續(xù)那樣的發(fā)展方式,后果不堪設想。除了變革發(fā)展方式外,尋求科技的解決之道,成了長期以來人們的期盼。以前有利的變成了有害的,以前毫無價值的東西,得益于科技進步,正在變成社會發(fā)展的寶貴資源,比如沙子變成了半導體,有害的大腸桿菌變成了效率最高的合成化合物工廠,陽光和風變成能量……現(xiàn)在的綠色能源科技和低碳生態(tài)科技等,也將會把人們改變環(huán)境惡化和能源短缺的愿望變?yōu)楝F(xiàn)實。
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不斷升級
中等收入群體對工具、家具、出行等,提出了超出普通消費者的要求,這些對于辦公自動化技術和快捷的信息系統(tǒng)的發(fā)展,以及現(xiàn)代化的生活起到了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新興信息科技轉化為應用工具和產品,以及相關的產業(yè)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如電子書、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服務軟件等產品,正適應了這些人的需求。20世紀后期到本世紀以來,更大范圍的新中等收入群體崛起,他們在創(chuàng)業(yè)的同時,把“追求幸福、把握生命、超越自我”作為新的消費需求,追求衣、食、住、行、娛、家、教、醫(yī)、旅、財等稀缺服務和產品。比如他們在出行方面對智能化、互聯(lián)網化、環(huán)保化的消費需求,代表了汽車業(yè)的發(fā)展方向,這些現(xiàn)實消費需求和愿景,無疑會反映在即將成熟的技術產品中,推進汽車智能技術的發(fā)展。比如他們通過基因篩查等高端健康服務,追求新潮的體檢和保健方式。比如,有些人千里迢迢到國外花幾千塊錢購買智能馬桶蓋,反映了他們對生活質量和細節(jié)的講究。近十年興起的新中等收入群體也有較高檔次的消費需求和趨勢,比如“數字單身”“輕量感日常”“IP可持續(xù)”,引領著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和產業(yè)化,推動了數字科技和制造技術的步步升級。
從追求物質利益向追求精神文化方向發(fā)展
法國社會學家鮑德里亞,1958年出版的《消費社會》一書,描述了消費取代生產、一切物品皆符號的消費社會,人們在表面富裕的陷阱中沉醉于符號與物品的消費,逐漸迷失自我,與此同時,社會整體人際關系逐漸空虛,社會不斷被物化和異化。這樣憤世嫉俗、充滿戾氣與絕望的觀點,在當時社會激起一番熱議。如今那種消費社會的場景和心理仿佛仍在現(xiàn)實中上演。這也說明過去人類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馬斯洛說的物質需求等前四個層次,越低層次的需求越容易量化,共性越大,市場規(guī)模相應越大。而規(guī)模是分工協(xié)作的前提,是舊工業(yè)范式的基礎。越高層次的需求越不易量化,個性化越強。因此,在溫飽、安全、社會、健康等基本需求滿足后,社會正逐步從物質經濟時代,有步驟地進入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數字經濟時代,這也是新科技產生的一個出發(fā)點。數字智能科技的萌芽,是否受到過這些思潮的啟發(fā)呢,比如從頂級的游戲,到虛擬現(xiàn)實、增強現(xiàn)實、混合現(xiàn)實、數字孿生,乃至元宇宙,都是人們在“萬物靜默如謎”中找到自我內心的豐盛,也都是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向著追求精神和文化的方向發(fā)展。在厭倦了對規(guī)模化喧囂和一律化的追求后,人們越來越多地享受智能手機上的閱讀、聯(lián)系、游玩,社交網絡似乎煥發(fā)出勃勃生機。在社交媒體、數字平臺和虛擬世界,一些人已無法分辨真正的現(xiàn)實和真正的虛擬,數據在透視著我們的靈魂。人們已不像過去那么從眾,即便是聚會的酒店,也不再是宏大的、豪邁的奢侈,更多地布置成分布式場景。社會上跟風和隨大流的現(xiàn)象逐漸弱下來,越來越多的人追求個性化、多樣化。中國的“85后”和“90后”,按自我意愿選擇生活方式,其中不少人每天大半時間上網,依賴互聯(lián)網進行交流與消費,對興趣相關的高科技產品充滿向往,愿意享受生活,尊重自己的選擇,擁有新潮的時尚感,他們買車不僅是為了滿足基礎需求,而且期待有新的體驗,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認知技術以及其他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新元素。這些特點都蘊含著創(chuàng)新的驅動力。現(xiàn)在不少科技產品適應了這種需求,如3D打印適合生產定制化的一次性產品,可制作假肢、人體器官,能打印食品,也常用于制作設計原型和建筑模型。未來將是廣泛自主制作的時代。3D、4D打印反映了制造業(yè)從大規(guī)模標準化生產轉向定制生產的趨勢,最終反映客戶需求的個性化、自組織化的趨勢。新科技滿足并推動著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未來科技仍然會尊重個體差異,朝著人類需求的自我實現(xiàn)、掌控生命和超越自我的方向發(fā)展。
對治愈疾病和健康長壽的渴望
疾病帶來的困擾和痛苦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它迫使人們不斷尋求解決方法,呼喚新科技的誕生。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出現(xiàn)的病人權利運動、自我保健運動、自然療法運動、整體醫(yī)學運動,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fā)展,以及70年代后期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的提出,顯示出從生物學探尋疾病的原因和治療的傾向,向著立體化、網絡化、多維度地審視健康和疾病轉變,促進了生命科學研究的深入,讓人們清楚地認識到生物機械論的局限性和人的整體有機聯(lián)系。現(xiàn)在儀器就能檢查出人們患病的幾率,預防和提前治療就可阻止疾病產生,用先進醫(yī)療器械篩查就能確定是否患病,都體現(xiàn)了科技在醫(yī)療領域的發(fā)展。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李明在2021年未來科學大獎周演講中說,有個帕金森患者群體給他來信說,“請您和帕金森患者一起點燃生命之光。多少人期盼干細胞移植和基因治療能快點,再快一點,我們有時候真的生不如死。我們需要科技工作者給我們一線曙光,哪怕給我們一個研發(fā)計劃都可以,我們太需要了。”這是令人揪心的呼聲和對科學家的期待,相信這些呼聲都注入科學家的心里,變成他們發(fā)奮研發(fā)的強大動能。
資本投向和占領市場的需求
20世紀中后期,資本與科技緊密結合,形成科技資本。資本逐利性決定了哪里有更高的受益,哪里就會聚集更多的資本,催生更高的效率。許多公司為占領和擴大市場,把看好的科技作為最好的投資,有的甚至通過壟斷新科技去壟斷市場,用資本綁定科技,科技成了吸引資本的力量,有的人幾乎把科技當成資本和企業(yè)賺取利潤的工具。這樣的方式使科技得到資本支持,刺激了科技的發(fā)展。有些科技研發(fā)在資本的支持下,只想著向科技要利潤,難以保證科技向善。當然,所有科技都希望得到資本的支持,但是大都兼顧到科技倫理和社會責任,防止出現(xiàn)惡的科技。可見,企業(yè)的市場需求和激烈競爭,促進了資本對科技的投入,一旦形成可替代的產品或開發(fā)出新的產品,企業(yè)的競爭力和市場的廣泛占有,就會帶來更大的利益,這是投資者、研發(fā)者共同的希望所在。SpaceX載人發(fā)射成功,投資者們對馬斯克燃起強大信心。據有關媒體報道,2020年6月2日美股開盤特斯拉股價上漲近1%,最高達908美元,逼近歷史高位。經過這波漲勢,特斯拉的市值接近1.2萬億人民幣。有人說,在數字經濟領域每九個月就要發(fā)生一次技術變化,原有的商業(yè)模型如在九個月內不能夠上市,很可能會走向衰亡,或者被憋死而無出口。資本充分挖掘新技術創(chuàng)富的優(yōu)勢,并加大投資力度,使資本看起來就像一種指向其自身產生利潤的力量。特別是掌握互聯(lián)網霸權的資本對信息資源的控制與壟斷實現(xiàn)了時間、空間界限上前所未有的拓展。可見科技與資本綁在一起,對科技研發(fā)的刺激和催化。
美蘇冷戰(zhàn)和軍備競賽的刺激
歷史表明,任何先進的科技大多最先用在軍事上。美蘇在核武器運載工具、多彈頭分導、潛艇發(fā)射戰(zhàn)略核武器等高技術領域武器的研制上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20世紀80年代美蘇軍備競賽刺激了太空技術和其他高新技術的發(fā)展。1983年里根提出“星球大戰(zhàn)”計劃,建立以衛(wèi)星為基地,以激光、粒子束為武器,分階段攔截、摧毀敵方來襲導彈的一個龐大的防御體系。蘇聯(lián)也加緊研制粒子束武器。
對科技刺激最強的當數美國的軍事工業(yè)聯(lián)合體,軍方向產業(yè)提供采購訂單和軍事津貼,向科研單位提供研發(fā)資金,在聯(lián)合體中處于相對核心地位。二戰(zhàn)爆發(fā)后,軍備競賽與政府研發(fā)資金的支持為冷戰(zhàn)后期技術的商用奠定了基礎,構成美國制造業(yè)的先發(fā)優(yōu)勢。在《技術、增長與發(fā)展》一書中,弗農·拉坦說:“政府資助的研究和技術開發(fā)在幾乎所有美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通用技術的發(fā)展中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甚至懷疑,如果沒有政府的采購,核能是否會發(fā)展起來。邵宇、陳達飛在《脫鉤與突圍》一文中,引用麥克雷對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與戰(zhàn)爭相關任務的闡述,認為美國創(chuàng)造并維持了一個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催生卓越的軍工技術,在和平時期的任務則是將其轉化為提升經濟競爭力的技術。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國防部啟動了技術再投資計劃(TRP)并撥款用于技術升級換代,重點發(fā)展軍民兩用技術。如沒有軍方資金的支持和軍用技術的商業(yè)化運用,20世紀80年代幾乎不可能成為信息時代的起點,蘋果公司也不會誕生。
美聯(lián)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解釋美國的繁榮與衰退時認為,最關鍵的三個方面是:生產力、創(chuàng)造性破壞和政治。創(chuàng)造性破壞是美國生產力不斷進步的動力機制,而政治則是影響該機制能否得以發(fā)揮的重要因素。技術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擴散確實有跡可循,但它并非獨立生成,而是內生于經濟和政治的社會化過程,其背后是人的選擇、意愿,甚至是強迫,尤其不能忽視政府和軍事的訴求。
戰(zhàn)爭迫使軍方有需求,國家提供資金給相關產業(yè)和科研機構,產品有急速的規(guī)模需求,科研成果受到經濟刺激很快成熟,一旦有成果便很快進入產業(yè),大量生產,投入戰(zhàn)場。這是刺激科技發(fā)展的一種連環(huán)套。雖然這種機制會給科技帶來效率,但有違科技倫理和道德原則,也是資本沖動和利益使然。
社會發(fā)展的強烈需求驅動著科技創(chuàng)新。社會關心的種種問題,或進入科技的研發(fā)項目,或由生產、生活、生命上升到因果、心物、簡復、時空,引導和推動著科技在宏觀和微觀、在數字和智能、在生命和生物、在環(huán)境和能源等方面全面拓展,縱深發(fā)展。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社會需求、國家利益、政策驅動是科技革命產生的外部動能。外部需求的驅動越強大,科技越發(fā)展。新科技革命正是在這些需求的推動下逐漸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