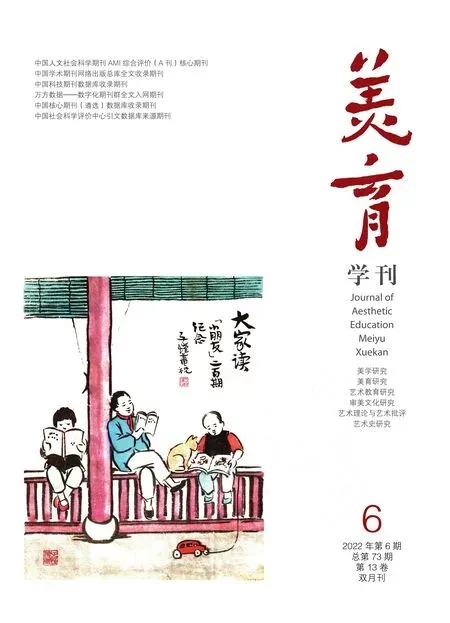現代性的自然美學及其當代價值
杜學敏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自20世紀6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在國內外環境美學和生態美學逐漸興盛且熱度不減的背景下,作為一個經典美學問題的“自然美”既明顯受到了擠壓,也在一定意義上獲得了新生,其標志之一就是“自然美學”概念的出現。以雙重自然內涵(即自然界或自然物意義上的自然與天然天成本性意義上的自然)的自然美與自然審美[1]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美學實際并非一個當代問題,它同美學學科一樣有其啟蒙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雙重現代性思想史背景(1)美學學科本身就是歐洲啟蒙運動與現代性的產物。哈貝馬斯曾指出:“要是循著概念史來考察‘現代’一詞,就會發現,現代首先是在審美批判領域力求明確自己的。”因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在許多地方都涉及現代性的美學話語,或者說,兩者在許多方面是聯系在一起的”。見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9頁、“作者前言”第1頁。關于“審美(美學)現代性”與“啟蒙現代性”的區分及其關系,可參閱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6-17頁、第48頁;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導言”第11頁。。然而,在美學研究領域提起現代性,人們一般會將目光聚焦于與啟蒙現代性同時誕生的、關于藝術美的藝術哲學美學,致使同樣處于現代性進程中的自然美學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謝林、黑格爾開辟的美學即藝術哲學的美學知識學背景下談論現代性(不管是啟蒙現代性還是審美現代性),自然美與自然審美并非必要的論域,人們更習慣于通過17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中方才正式出現的美的藝術或藝術美問題來展開其討論。因而,正像在審美發生學研究中存在重視藝術審美而忽視自然審美的偏見[2]、在美學學科內部存在重視藝術哲學或藝術美學而忽視自然美學的偏見一樣,在美學現代性研究中也明顯存在重視藝術美現代性而忽視自然美現代性的偏見。本文試圖闡述自然美學的誕生及其發展的重要關節點,并借此說明作為美學家族中一員的自然美學的產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現代性現象,而且具有重要且多維的價值。
一、自然美學誕生的相關概念證明
自然美或自然審美概念不僅意味著一種實踐活動,也意味著一種作為對此自然審美活動予以反思的理論性存在,而此理論性存在就是這里所要闡發的作為現代性學科的自然美學,此自然美學與自然審美現代性結伴前行并成為其存在的理論證明。
首先,自然美學的誕生,通過“自然美”和“美的自然”等概念的正式出現得以證明。盡管中國先秦時期的莊子已經用到類似今天自然美概念的“天地之美”等表述,人們也公認對自然美的發現或獨立意義上的自然審美在公元3世紀左右的中國魏晉時期就已經發生,但直至20世紀初之前,中國美學史上并無明確的“自然美”概念。“自然美”概念與“現代性”現象一起作為一個學術問題首先產生于西方文化史和美學史。“自然美”概念在西方究竟最早于何時由何人使用,這里暫無確切答案。可以推測,大約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所指稱的以彼得拉克為代表的“自然美發現”[3]的14世紀,西方人應該已經開始使用到“自然(的)美”或“美的自然”概念。就筆者所見文獻而言,法國建筑家布隆代爾(Nicolas-Francois Blondel,1617—1686)的《建筑教程》(Cours d’ Architecture,1675—1698)和被稱為“盧梭的先驅”[4]223之一的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費訥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的《致法蘭西學士院書》(1693)中即提到“自然美”:“我在某種程度上同意某些人的意見,他們確信存在著一種自然的美”[5];“美不會因屬于全人類而貶值,它會更有價值。稀有是自然的缺陷和匱乏。我想要一種自然的美,它不需要靠新穎來驚人,我希望它的優雅永不過時”[4]85。上述兩例無疑可作為西方人17世紀自然審美活動理論言說的證明。
更為鮮明地在美學語境下使用“自然美”(natural beauty)概念的大概要數18世紀英國經驗派美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論》(1739—1740)“論美與丑”一節寫道:“自然美和道德美(natural and moral beauty)(兩者都是驕傲的原因)所共有的因素,只有這種產生快樂的能力。”[6]同“道德美”相提并論的語境使此“自然美”的美學語義顯而易見。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美學代表作《論崇高與美兩種觀念的根源》(1757)則云:“我更確信比例(美)的贊成者們把他們人為的觀念轉嫁給了自然,而不是向自然借用他們在藝術作品中所運用的比例;因為在這一論題的任何討論中,他們總是盡快地逃離屬于植物界與動物界的自然美的廣大領域,而用建筑學的人工線條與角度來支持自己的觀點。”[7]由同“藝術作品”形成對舉之勢的語境看,此“自然美”無疑側重于指外在自然事物的自然美。博克所謂“植物界與動物界的自然美廣大領域”也可通過有學者已指出的當時文化精英所熱衷的“無人風景”得以印證:“在18世紀的英國,文化精英們共有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即圖繪的,印刷的和實有的‘無人風景’。”[8]所謂“實有的‘無人風景’”顯然有別于司空見慣的一些藝術作品中描繪的作為人物背景的自然風景,而是具有了獨立意義的自然美景本身;文化精英們對由藝術美中展示的自然美景與大自然實際存在的自然美景所構成的所謂“共同體”的想象,則無疑標志著自然審美在18世紀的英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代性存在。
據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研究,“美的自然”(la belle nature)概念在博克時代的法國新古典主義那里已經得到了提倡且已非常通用,“這一概念是從一種美術理論中抽繹而來”[9]9;提出“美的藝術”(Beaux arts)概念的巴托(Charles Batteau,1713—1780)的《美的藝術化為一條原理》(1746)在闡述摹仿說時運用“美的自然(la belle nature/beautiful nature)”概念,“把摹仿‘美的自然’作為各門藝術的一般原理”[9]21;與巴托同時代的狄德羅(1713—1784)也明確使用過“美的自然”這個概念,他提出“摹仿自然還不夠,應當摹仿美的自然”[9]66。由“美的自然”與“美的藝術”術語同時產生這一事實可以推斷,作為審美學重要范疇的“自然美”這一概念,首先是在與“藝術美”相對的意義來使用的,而且最遲在18世紀中葉已經非常流行。
其次,自然美學的誕生通過“自然美學”概念得以證明。在“美學之父”鮑姆加登(A.G. Baumgarten,1714—1762)的標志性著作《美學》(Aesthetica,1750)中,“自然美學”(一譯“天然美學”)的拉丁文形式“aestheticanatvralis”已經出現,且有專門章節予以討論。鮑姆加登在全書第1個段落給出美學定義之后,緊跟著的第2段落即指出:“在自然狀態中,低級認識能力未經任何方法的訓練,只是通過使用而得以發展,這種狀態可稱為自然美學。如同自然邏輯學一樣,自然美學可以分為先天的(指天生的美的稟賦)和后天的自然美學,后者又可以分為理論性的和實用性的。”[10]緊隨其后的第3段落又寫道:“美學作為藝術理論是自然美學的補充。”[10](2)筆者注意到最新中譯將此概念譯為“天然美學”,上引文字前面一段被譯為:“只通過運用、無需教條學說而被提升的低級認知能力的天然狀態,可以被稱為天然美學,正如人們在天然邏輯學中的習慣做法一樣,它可以被分為一種天生的即一種天生的美的天賦之美學和一種習得的美學,而后者又分為教學的和運用的。”后面一段被譯為“作為天然美學之補充而登臺亮相的技藝美學”。[德]亞歷山大·戈特利布·鮑姆加通:《美學(§1—§77)》,賈紅雨譯,載高建平主編:《外國美學》第28輯,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頁。此后,其《美學》還用大量段落圍繞此概念展開闡述。
這里有三點值得闡明:第一,鮑姆加登的“自然”明顯側重于指稱人的內在自然,因而其“自然美學”(或者“自然審美”)界說強調的是人使“低級認識能力未經任何方法的訓練,只是通過使用而得以發展”的“自然狀態”或“天然狀態”;第二,就“自然美學”同“作為藝術理論”的“(藝術)美學”關系看,鮑姆加登賦予“自然美學”同“藝術美學”相提并論甚至優先或高于后者的崇高地位(或許是因為自然美學側重于內在);第三,鮑姆加登整部《美學》建基于其“美學的目的是感性認識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認識)。而這完善也就是美”,以及關于美學/審美/美的(3)這里之所以將“美學”“審美”和“美”三個術語并列一體,是因為鮑姆加登《美學》對三者的使用雖然存在表述及其具體使用上的差異,但賦予三者的目的性內涵則完全一致,這就是沿襲自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理性主義哲學的“完善”(perfection)說。參閱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93-300頁。由此也可看到,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的美學研究中,上述三個概念之所以被經常混同使用,在這位“美學之父”這里可以找到最初始根據。下文的“自然美學/審美/美”表述與此相似。“完善”說。鮑姆加登差不多同樣強調“自然美學”及自然審美/自然美的自身內涵的完善意味,及其對于由感性到理性的完善或構建人性的特別價值。
簡言之,“美學之父”鮑姆加登的“自然美學”是側重研究人的內在自然完善的自然美學,它雖然尚未明確涉及人的外在自然及人之外的自然內涵,因而同當代語境中的“自然美學”的內涵有明顯不同,但其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覷。因為作為理性主義哲學家和美學家的鮑姆加登提出“自然美學”概念,顯而易見地存在著一種由知識理性駕馭感性人性從而使之臻于完善的啟蒙現代性并美學現代性旨趣。只是鮑姆加登始用的“自然美學”概念并未像他創立的“美學”“審美”概念一樣流行。“自然美學”概念被廣泛使用,大致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自然美學”的真正誕生,需要概念命名和學科定位,更需要學理性的學科理論建構及在不同階段的歷史演化和發展。換言之,“自然美學”一方面是經由自然美問題史上諸多自然美觀念歷史性地建構起來的,另一方面也是經由愿意涉足此領域的研究者邏輯性地建構起來的(4)從學術思想史上出現的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學著作而言,更為司空見慣的是“自然哲學”而非“自然美學”的歷史與邏輯建構。在此過程中,“自然美學”并未因自然哲學不斷被討論而在作為一門哲學分支學科的美學內部被人注意到,從而同自然哲學一樣被歷史與邏輯性地建構起來。相對于自然哲學,雖然在18世紀中葉鮑姆加登已經用到“自然美學”這個概念,但自然美學在美學成為獨立的哲學分支學科之后并未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美學分支學科。。
二、現代性自然美學發展的重要關節點
從發生學意義上講,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實乃西方美學史上第一位沒有用“自然美”概念的“自然美學家”。“自然”概念是盧梭所有作品的“紅線”,“回歸自然”則是盧梭最鮮明的思想標識。盧梭啟蒙思想中的“自然”,既是盧梭指控人類文明與現代社會的立足點,也是考驗、啟示、呼喚人類的良師益友,更是和諧完滿人性的理想狀態、生活原則與終極依據。其中,理想的自然狀態意義上的自然是盧梭“自然”概念的核心內涵。盧梭建基于上述“自然”概念的自然美觀,既重視崇高也不輕視優美,認為二者均具有有益身心的功效;不僅指向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更深刻地高揚自然本性之美的自然美。盧梭立足于趣味或審美力的自然審美觀則強調,“回歸自然”既意指回歸到大自然、感受大自然之美,也意味著回歸到一種自由狀態、過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盧梭重視甚至膜拜兩種內涵的自然美甚于藝術美,其自然美學以其審美教育理念與審美自由內涵同時表現出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特征,在西方美學史上前所未有地彰顯了自然審美的解構與建構雙重價值,從而代表著現代性自然美學的功能維度。
對自然美學率先予以事實性學科建構的人則是將自然美納入焦點且給予多維度探究的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康德多次直接使用“自然美”概念,因此成為諸自然美問題及由此形成的自然美學領域的實際創立者。這首先表現在其《判斷力批判》(1790)對“自然美”概念五重內涵在美學理論中的全面展開:(1)有別于“自然目的”的自然美,這是康德廣義的自然美觀念;(2)有別于“依附美”的“自由的自然美”,這是康德自然優美的自然美觀念;(3)有別于“自然的優美”的自然美,這是康德“自然的崇高”的自然美觀念;(4)有別于“藝術美”的自然美,這是康德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美觀念;(5)有別于“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這是康德“自然天成之美”意義上的自然美觀念。排除附屬于其批判哲學的個性化用法,康德的上述自然美觀念實際也可簡化為自然事物之美的自然美與天然天成之美的自然美這兩種基本內涵。而且,康德更看重這兩種意義上的自然美較之于藝術美的道德人性建構意味,其“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著名命題基本是針對自然美與自然的崇高而提出的。康德批判哲學中的自然美之思,同其他美學思想一樣原本是要克服其前兩大批判的巨大鴻溝,但其審美與目的論雙重視域中的“自然美”概念的五重內涵,不僅使自然美概念第一次獲得了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而且開啟了審美與道德之思在自然問題中的雙向互動關系及其現代性論域。康德之所以能成為自然美學事實上的真正創立者,除了自己的問題性指引之外,盧梭以“回歸自然”為核心的自然及自然美思想和博克明確提出的“自然美”概念及其美和崇高的分析思想也成為康德自然美學的重要資源背景。尤其是盧梭,如若缺少他包括自然美觀念及其功能價值在內的啟蒙思想的影響,很難想象會有康德對自然美問題的高度關注及其道德與目的論視域下“自然美”概念內涵的多重論證。
康德之后,按其宏大的理念論哲學體系被動進入自然美論域的是黑格爾(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盡管他在謝林(F.W. von Schelling,1775—1854)藝術哲學建構基礎上略顯武斷地將美學規定為美的藝術的哲學,從而將自然美排除于美學研究對象之外,但在其哲學及藝術哲學美學框架內仍然對自然美給予了既責難又論證的矛盾化處理。黑格爾明確貶低同藝術美相對的、自然事物之美內涵上的自然美,但他也論及并推崇自然天成意義上的自然美。黑格爾藝術哲學視域中的自然美研究,使得自然美同藝術美的關系從此成為一個繞不開的美學問題。從自然美角度而言,正是黑格爾開啟了對自然審美本質特征及其有別藝術審美的欣賞模式問題的思考方向。雖然此方向只有到當代環境美學出現之后,才真正成為被追問的對象。
以藝術哲學美學而著稱的黑格爾的美學研究,對自然美學產生了頗為不利甚至是毀滅性的影響。雖然不排除極少數學者或美學家仍然時不時會關注自然美問題——比如19世紀中后期北美關注自然問題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與穆爾(John Muir,1838—1914)和20世紀上半期的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討論過自然美問題[11]4-5,但在20世紀后期以前甚至迄今流行于西方的基本是以藝術為中心的美學體系。正如英國研究者瑪麗·瑪瑟西爾(Mary Mothersill)的《美的復歸》(1984)指出的:“現代美學已逐漸被等同于藝術哲學或藝術批評的理論,……許多熟悉的美學問題現在都已證明它們涉及的是和藝術作品的解釋和價值相關的‘關聯性問題’。”[12]3因而,“幾乎任何一本西方的美學著作都把藝術問題放在首位,即使美學家仍在以美學的名義寫書,但所寫的往往是一種藝術哲學或近于藝術哲學的東西。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對自然美的興趣已大為降低,對美的形而上學的探討也已失去往日的熱情”[12]1。譬如,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1965年7月載于《美國哲學季刊》第2卷第3期的《美學近況》[13]13-50所列英美兩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詳細的美學研究文獻中找不到一篇題含自然美的自然美專題文章。在此背景之下,即使自然美問題得到討論,也是為了映襯藝術美。可以說,自然美研究基本處于被藝術研究壓制的狀態,自然美學整體上被藝術哲學遮蔽了,沒有其獨立地位。
20世紀中葉,阿多諾(T.W. Adorno,1903—1969)的《美學理論》曾尖銳指出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康德對自然美做過敏銳的分析以后,從謝林的《藝術哲學》開始,由于人類理性的過分膨脹,西方美學就幾乎只關心藝術作品,從而中斷了對自然美的任何系統研究(5)另外,秉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只專注藝術問題研究和語言分析,至今仍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分析美學主潮,實際也充當了自然美問題被“置于理論盲區”或者“掩蓋在藝術哲學的陰影當中”的“急先鋒”。參見劉悅笛:《自然美學與環境美學:生發語境和哲學貢獻》,《世界哲學》2008年第3期。。事實上,即使是重視自然美,在其《美學理論》第四章專門討論自然美的阿多諾本人,也依舊是在藝術哲學的范圍內說這番話的,因為他明確說“對自然美的思考,是構成任何藝術理論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4]。自然美學之于藝術哲學或藝術理論的婢女身份一如其舊!因此,雖然從盧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開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中不乏關注自然與自然美問題的理論家,但基本仍然是在以藝術而非更為廣泛的審美活動為研究對象的美學研究中論及自然美的,從而整體并未賦予自然美以獨立的自然美學價值。不僅上面提到的有專章“自然美”研究的盧卡奇(《審美特性》第15章)和阿多諾(《美學理論》第4章)是如此,其他如零星卻不無新意地關注自然美問題的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馬爾庫塞(《阻礙革命和反抗》第3章“自然與革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深刻論及自然問題的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批判理論》)、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威廉·萊斯(《自然的控制》)也是如此。
當然,在阿多諾說這番話的20世紀60年代后期,情況已經開始有所改變。這就是,在現代工業發展給自然和人帶來無可補償的破壞性與危機、生態與環境問題日益凸現的現代性背景下,以英國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1927—2008)發表在《英國美學雜志》1963年第3期上的《對自然的審美欣賞》[13]365-381一文(6)此文后收入《英國分析哲學》(倫敦:勞特利奇和基根·保羅出版社,1966年)第285-310頁,但題為《當代美學及對自然美的忽視》(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在此文中,赫伯恩既不無遺憾地指出了當代美學忽視自然美的嚴重傾向及其原因,也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審美欣賞(相對于藝術鑒賞)所具有的鮮明特征與意義。由于此文論及處于環境整體中的自然對于自然審美鑒賞的意義,赫伯恩因此也被視為當代環境美學的先驅性人物。為明顯標志,自然美問題復始贏得不少有識之士的極大興趣[15]。尤其是70年代以降,傳統的自然美觀念與生態學、環境科學、環境倫理學、生態倫理學、環境美學及生態美學等學科互相影響,一批涉及自然美與自然美學問題的論文專著陸續問世。其中較為活躍的學者有羅爾斯頓(H. Rolston III)、哈格洛夫(E. Hargrove)、卡爾松(A. Carlson)、伯林特(A. Berleant)、巴德(M. Budd)、帕森斯(G. Parsons)和摩爾(R. Moore)等。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1988)和哈格洛夫的《環境倫理學基礎》(1989)強調自然本身的審美價值,并以之作為環境倫理學及環境保護運動的本體論論證與理論根據。卡爾松和伯林特是以其環境美學研究而著稱于當今西方美學界的兩位代表,分別在其《環境美學:闡釋性論文集》(1982)、《美學與環境:自然、藝術與建筑的鑒賞》(2000)、《自然與景觀》(2008)和《環境美學》(1992)、《生活在景觀中:走向一種環境美學》(1997)等著中,力圖建構一種不同于藝術美學傳統的關于自然與環境的體驗感知模式以及相應體系的環境美學。他們不僅頻繁使用自然美學概念,也深入論及有別于藝術審美的自然審美的模式等問題。卡爾松《美學與環境》的第一章標題即“自然美學”(The Aesthetics of Nature),且在此章伊始首先簡要回顧了自然美學的歷史[11]3-5。以此為基,以巴德的《自然審美欣賞:自然美學論文集》(TheAestheticAppreciationofNature:EssaysontheAestheticsofNature,2002)、帕森斯的《自然美學》(AestheticsandNature,2007)、摩爾的《自然美:超越藝術的美學理論》(NaturalBeauty:ATheoryofAestheticsBeyondtheArts,2007)為代表的自然美學研究顯得更加名實名相副,這從把自然審美與自然美學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和題目即可見出。尤其是巴德,他在述評傳統美學及環境美學家觀點的基礎上,不僅勾畫了自然美學的基本概貌,還明確提出了不同于卡爾松肯定美學模式、伯林特介入美學模式的“自然作為自然”的自然鑒賞模式,表現出建立有別于環境美學的自然美學之決心,在一定意義上成為“自然美學”獲得新生或在新時代正式登場的標志。不過,巴德也跟上述其他關心自然美問題的美學家一樣,將“自然美學”跟其他相關美學如環境美學等未作區分(比如,巴德在關于自然美學概述的“Aesthetics of Nature: A Survey”長文中不僅將“自然作為自然的審美鑒賞”,也將“環境形式主義”“介入美學”“肯定美學”等多種模式視為自然美學的構成部分[16]),也忽略了盧梭、黑格爾、馬克思、海德格爾和杜夫海納等人的自然美觀念。

人類關于自然美欣賞或自然審美的最早時間甚至可追溯到史前石器時代,人們對自然美和自然審美的思考也可謂古已有之,但只有在西方14世紀至18世紀的現代性分化進程中,在藝術美、自然美觀念同美學學科、自然美學思考幾乎同時誕生的啟蒙理性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共同發展的過程中,自然美和自然美學才真正成為一個現代現象。正像在此過程中“藝術”與“美”概念兩相結合,孕育、誕生了現代的“藝術美”概念一樣,“自然”與“美”概念結合而產生了現代的“自然美”概念。事實上,當美學學科在其創立的啟蒙時期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性的規劃議題之時,自然美就和藝術美等問題一起在第一批現代性思想家的哲學話語中嶄露頭角。可以說,最初的幾乎所有著名啟蒙思想家在發表其美學理論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發表過一定的自然美理論。現代性哲學話語的表達者同時也是現代性美學話語和本文關注的自然美學話語的表達者。
以上主要基于西方美學史來論自然美學的誕生與發展,當然也并非自然美學的全部歷史。20世紀以來,匯入西方現代性洪流的中國美學自然美之思,帶著自己的問題經歷了從外在自然物之美到生態美學的歷史嬗變[17]。隨著現代性與自然美學術的不斷成熟,貫穿于整個中國古典美學尤其是老莊道家美學中的天然天成之美[18],可謂最具更新現代性舊有動力機制的重要資源,在中國當代方興未艾的生態美學研究中受到高度關注,因而也實質性形成了現代性自然美學的中國維度。
簡言之,自然美學的幾個重要關節點是:(1)盧梭啟蒙自然美觀,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美育功能維度;(2)康德審美—目的論自然美觀,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自由維度;(3)黑格爾藝術哲學自然美論,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藝術維度;(4)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自然美觀,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根源維度;(5)現象學視域中的自然美論,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本質與經驗維度;(6)環境美學視域中的自然美論,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鑒賞模式維度;(7)從自然倫理到生態倫理的中國自然美論,代表著自然美學現代性的中國維度。
三、現代性自然美學的當代價值
綜上所述,自然美學并非關心此學科的學者們一廂情愿的虛構,它其實就以各具特色的問題向度貫穿于中西美學思想史上盧梭、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等思想家和老莊道家、馬克思主義、環境美學、生態美學等美學流派的自然美思考之中。
文藝復興以降,外在自然與人的內在自然(本性)一直是西方啟蒙理性或現代性控制的對象,上述不同思想視域的自然美觀念雖整體仍處于此啟蒙現代性框架內,卻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各具特色地對抗此控制的獨特表達,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審美現代性特征,同時對有別于其他美學分支學科的自然美學之問題系統具有深刻的構建意義。基于以上認識,本文將尋常同藝術美相提并論甚至有時被收編于藝術美學的自然美研究稱之為現代性的自然美學研究。筆者以為,此種現代性自然美學的價值,不只是針對自然美問題本身的,也是針對其他美學問題甚至是美學基本或關鍵問題的;不只限于美學學科內部的,也是跨學科或涉及整個人類思想的。
第一,現代性自然美學視域的自然美研究對于自然美學本身的意義。長期以來,流行的“自然美”概念似乎只有其表層義涵,即自然事物或自然現象的美,尤其是國內的美學工具書與教科書也幾乎均是如此界定“自然美”概念的。但有的美學家早就強調“自然美”并非一個自明的概念(7)朱光潛很早就表達了他對“自然美”概念本身的困惑:“一般人常喜歡說‘自然美’,好像以為自然中已有美,縱使沒有人去領略它,美也還是在那里。……其實‘自然美’三個字,從美學觀點來看,是自相矛盾的,是‘美’就不‘自然’,只是‘自然’就還沒有成為‘美’。……如果你覺得自然美,自然就已經過藝術化,成為你的作品,不復是生糙的自然了。”朱光潛:《談美》,《朱光潛美學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487頁。。事實上,由于“自然”與“美”概念各自的復雜性,被人們普遍使用的“自然美”概念的復雜性仍然沒有被美學界深入關注。對自然美及其本質等相關問題大有深入追究的必要:人們使用的“自然美”概念究竟有何內涵?作為一種審美與美的類型,“自然美”概念的分類依據何在?自然美的特征何在?自然美何以可能?自然美何以會成為一個美學問題?而且,它僅僅是一個美學問題嗎?自然美的意義何在?……在此種種追問之途中,有別于其他美學分支學科的自然美學得以彰顯并逐漸獲得其獨立地位,而這正是自然美研究的首要意義。顯而易見,美學史上關于自然美的概念、根源、本質、功能等問題的資源可以真正建立起獨立且更具涵蓋性的自然美學本身。
自然美學是研究雙重內涵的自然審美活動及其自然美的美學分支學科,它關注自然事物之美和天然天成本性之美雙重內涵。自然美學同環境美學、生態美學及生活美學等有不同程度的密切聯系,美學家族也不應只有藝術美學和社會美學,還應當有一般與二者區分并列、在天然天成之美意義甚至可涵蓋統攝二者的自然美學。因此,從審美分類學角度而觀,研究外在自然事物之美的自然美學同藝術美學、形式美學以及社會美學等相對,而研究內在天然天成之美的自然美學則同優美美學、崇高美學、悲劇美學、喜劇美學等相對。
第二,現代性自然美學視域的自然美研究對于整個美學的意義。通過對自然美兩重概念內涵及關系的辨析與梳理,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審美活動的人性顯現與人性建構意義。具體而論有以下幾點值得提出:
(1)從美學研究的關鍵問題看,通過“自然美”概念及相關問題的梳理與研究有助于對美的本質問題的理解或解答。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自然美曾經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而自然美之所以難以明斷,就在于它可以牽帶出美的本質問題。眾所周知,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論爭的核心即是所謂美的本質問題,而自然美又被視為是對美的本質問題解答的要害,以至被稱為“美學的難題”[19]87、“絆腳石”[20]、“危險三角區”[21]、“阿喀琉斯的腳后跟”[21]及“美學家的試金石”[21]。即便在美的本質問題不再時興的今天(8)據彭鋒研究,繼20世紀美學和藝術領域的“美的遺忘”之后,“美的回歸”一經批評家希基(Dave Hickey)在1993年提出,遂“在美學界、批評界和藝術界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美的問題重新成為美學家、批評家和藝術家談論的熱門話題”。彭鋒:《回歸:當代美學的11個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章。,只要談論美是什么的問題,自然美也仍然會成為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橫亙于研究者面前。再如,西方當代環境美學所宣示的“肯定美學”與“介入美學”就是在對自然美研究中提出的。
(2)從美學的研究對象看,對自然美的研究與重視在客觀與主觀兩層面都有一種矯枉糾偏的意義,即對長期以來美學研究對象問題上根深蒂固的“藝術中心論”有可能產生一定的沖擊。換言之,對自然美的研究“與整個美學基本理論有關,也就是說,它將促使我們對流行的以藝術為中心的美學體系做出適當的修正和調整”[22]188。此外,對自然美的深入理解,還有助于理解它與藝術美的關系,并進而深入把握藝術美乃至社會美、形式美的本質特點。事實上,盡管以藝術為中心的美學體系“幾乎不關心自然美本身,然而,在涉及對藝術經驗的分析的關鍵問題時,它卻反復地將我們對藝術品的審美態度與對自然的審美態度作比較”[13]375,而這正說明了自然美問題對于理解、解決藝術美問題的重要意義。
(3)從美學研究的根本目的看,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與現代人文學科的骨干學科,美學的終極意義在于追求與建構人類價值體系,實現人的審美化生存,而借助于自然美這一特定的問題、視角,有助于實現美學的上述意義。例如,通過對自然美兩重概念內涵及關系的辨析與梳理,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審美活動的人性顯現與人性建構意義,在一定意義上彰顯美學作為第一哲學的獨特價值。
第三,現代性自然美學視域的自然美問題研究的跨學科意義。一旦在傳統的藝術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美學或文藝心理學美學之外進行開拓,加入自然美學等非藝術學美學研究,美學的視野自然就會變得寬廣,美學本身也就具有了一種跨學科結構。具體而言,自然美問題的跨學科意義主要體現在自然美學同美學之外的其他學科及其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而促成的新的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的興起與繁榮上。如生態學、環境學、環境生態學、自然旅游學、自然哲學與美學或自然美學融合而產生的生態美學、環境美學、環境生態美學、自然審美哲學、自然旅游美學等。這既可以說明作為美學問題之一的自然美對于其他學科的貢獻,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自然美對于美學學科的意義。比如,自然美對于所謂新自然哲學的意義。人們以為存在兩種自然哲學:一是所謂舊自然哲學,它把自然作為外在的對象和存在者來認識與把握,這實際是自然科學的作風,嚴格來說已經屬于科學而非哲學;一是所謂新自然哲學,它以思考自然本身為己任,強調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關系,顯現自然、敞開自然是其任務,“新的自然哲學可能不再以一個知識門類出現,而是一種廣泛的思想運動”[23]372。不難設想,在這樣一個廣泛而全新的自然哲學的思想運動中,自然美觀念無疑會占據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再如,在曾經沉寂多年的美學與環境學、生態學等現代新興學科的相互促動而產生并興盛的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的帶動下,自然美一直可謂當前美學研究與發展中的一個學術增長點。
第四,自然美學在“第一哲學”中必然占據著一個無可替代的地位。眾所周知,美學是作為同邏輯學、倫理學并列的三大學科之一在哲學內部誕生的。自從美學獲得其獨立存在之后,就不斷有人出于種種原因斷言美學是倫理學,也不斷有人將美學推舉到第一哲學的“至高無上”地位。如果認可當前國際美學是由三足鼎立的自然生態美學、藝術哲學美學與日常生活美學構成的話,那么自然美學就是三足之一。不僅如此,任何美學及哲學都離不開對審美及人的自然性之關注,基于雙重自然美內涵的現代性自然美學完全能夠擔當起使美學真正成為大有可為的倫理學乃至第一哲學的重任或使命,因為側重內在天然天成本性內涵的自然審美與自然美在眾多審美與美中具有根本性的本體論與存在論重大價值。換言之,自然審美與自然美是第一性的,自然美學因此也是第一性的。
第五,現代性自然美學視域中的自然美研究對于推進豐富多樣的自然審美文化建設、有效解決現時代文化實踐中的各種矛盾等方面有豐富的實踐意義和現實功能。例如,自然審美與自然美本身及其研究對于理解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切實意義。的確,我們很難設想一個對山水自然、生態環境充滿熱愛、珍惜、欣賞并敬畏的人會肆意踐踏、破壞、污染它。但自然美研究的現實意義還不只限于此。眾所周知,正是在人與自然的交往過程中產生了作為人與自然關系哲學表達的種種自然觀。而且隨著人與自然交往的不斷發展升華,又使一種新的自然觀成為可能,這就是人的自然審美活動及其自然美觀念。毋寧說自然美是人的一種審美自然觀。因此,一旦不只在非人工世界的總稱內涵上理解自然,而且在包括人在內的所有事物的一種本性內涵上理解自然,一旦把自然美不僅理解為外界自然事物在審美活動中發生的美,而且理解為一切雖系人工事物及人類行為但在審美活動中卻給人以自然而然的非人工性的美,那么自然美研究的重大現實人生實踐意義就不難理解了。可以說,作為人的一種現實審美類型,更作為人的一種本真存在方式,自然審美與自然美的實踐意義即在于我們能將與自然事物照面時所真正把握到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美,自然而然地推及到人與自身,人與自然界、人生社會、藝術世界等各個人生場域。
鮑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曾寫道:“人所以追求自然是因為他已經感到他和自然分開了。”[24]116在無數巧奪天工的人工造物爆炸式地充斥我們生活的全球化時代,在人工智能技術一路高歌、突飛猛進的“互聯網+”時代,關注自然美的現實意義,正在于對自然事物與自然現象之美的欣賞中,有可能促使我們對人工造物的執著性有所警醒與節制,從而進入到本然本真而自由的存在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