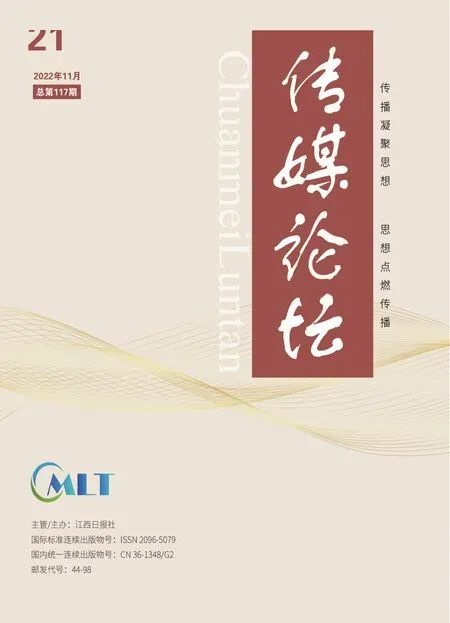虛擬、聚焦與共性:后疫情時代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轉向
林恩全 田 瑞
后疫情時代是伴隨著季節交替、國際回流等因素而產生的疫情小規模暴發的時期,此時傳播學領域內的學界研究呈現出多主體、多維度、多層級的特點,“后疫情時代和疫情時代之間并沒有明確的時間界限,很難用一條橫杠將兩個時代嚴格區分開來。”①但不斷改變的社會情境打造了新式的社會生活模式,脫域式社交活動的崛起、全沉浸式數字化體驗升級等等,加速了人類擬態化的進程,放大了日常生活中在緩慢進行的社會實踐和行為模式,重構了人們的社會心理模式,也為社會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們生活于現實與虛擬兩個社會②,現實中的信息傳播渠道不僅連接了受眾與信息,也連通了現實與虛擬,“無處不在的場景入口,使受眾可以自由地獲取可供選擇的任何信息”③,人們在網絡發表言行,打造前臺形象,撰印自身的刻板印象,個人意見的交互與統合形成網絡社會中的公意,亦即輿論。在李普曼看來,輿論并非先天自然的存在而是后天人為的創造,背后意涵著權力機構對于人性弱點的利用和操縱。早期,中國的新聞輿論觀念援引自西方,因此難逃精英主義視角,強調從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視角及以傳者為中心的框架下探析大眾思想的影響與指導作用。④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完善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自由思想成為新聞輿論研究的普世觀,正如張友漁所言:“唯有人民自己制定、執行由人民選舉并最終受到人民監督的法律才能真正保障新聞自由。”⑤國內針對新聞輿論的研究可以統合于輿論過程研究和輿論結果研究兩個范式集合,輿論過程研究注重輿論生成的主觀臆想(情感、言論、反饋等)、客觀要素(中介、議題、場域等);輿論結果研究則從社會實際現象出發,以輿論反轉⑥、輿論引導⑦、輿論危機⑧等為闡述主體或論述對象,注重于社會現實需求,對現實社會未來發展、網絡生態建構及網絡社會治理提供有力支撐。
一、后疫情時代下的網絡新生態
(一)現實到虛擬:可供性助力沉浸式新聞生產
沉浸式新聞(Immersive Journalism)是指以虛擬現實技術為依托,通過攝像機采集新聞現場信息,再現新聞事件全過程的擬態場域,用戶可以通過佩戴相應的設備融入其中,從而增強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它所實現的傳播效果是“讓人看不到、摸不到、覺不到的超越時空的泛在體驗。”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央視特別推出“全景看戰疫前沿”報道,而該報道正是通過VR技術360度還原疫情現場,讓民眾對新冠肺炎疫情有了全面的了解。通過這種沉浸式新聞所帶來的臨場感的傳達,助推我國防疫政策的實施,為我國各項防疫活動的開展掃除了障礙。
從現實播報到擬態場域再現,可供性充當了有力的推手,詹姆斯·吉布森最早對其進行定義,指代環境屬性所帶來的人們實施某種行為的可能性。而伴隨人類能動性在環境屬性變動中的作用增強,媒介可供性、技術可供性等一系列可供性研究范式逐漸出現。我國學者潘忠黨于2017年首次將“媒介可供性”概念引入我國傳播學界,并統列出了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動可供性三個要素。首先,從生產可供性視角中審視沉浸式新聞,其背后體現的是網絡通信技術的升級,更大的傳輸渠道、更快傳播速度優化了現有的新聞內容生產格局,凸顯用戶個性的自由視角出現,而“云采編”場景的建構更推動了行進式新聞內容的生產與分發。其次,在社交可供性視角下,沉浸式的新聞敘事不再是單向的新聞信息傳遞而是行為主體與敘事場景的互動,實現了媒體可傳情、可致意的功能。最后,在移動可供性的視角下沉浸式新聞突出表現為“在場”,通過簡單的連接設備就可以實現個人在過去或未來敘事情境中的“在場”,推動虛擬與現實的結合。
(二)分散到聚焦:主流媒體的話語權回歸
社會化媒體的出現使得每個人擁有了發聲的機會,主流媒體對于輿論事件的報道也往往被多方話語所沖淡和解構,難以形構主流輿論場地。而后疫情時代的當下,從新冠肺炎疫情陰霾中走出的人們,對國家政府及官方媒體更加信任,使得主流媒體的話語權逐漸回歸。網絡輿論代表著網絡社會大多數網民的集體意見,而在輿論發展演化的過程之中,主流媒體的及時發聲是輿論引導關鍵的環節,尤其在突發事件中,網民往往被單一言論所裹挾,無法從全方位的視角去審視事件的經過,只能從各類媒體網站中取得分散性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所具有的分散性特征又會帶偏甚至極化信息接收的個體或群體,因此及時的發聲止謠是主流媒體的應然之態和必然選擇。
謠言止于智者。主流媒體的發聲意味著多數網民對突發事件整體情況有了相對精確的把握和統一的認識,實現了話語的聚焦,輿論場的統合。例如在此前出現的“西安孕婦”事件中,西安衛健委的及時介入調查以及官方媒體的及時發聲使得網民對該事件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及時撫平了網民的極化情緒。
(三)個性到共性:關系鏈下圈群屬性凸顯
媒介技術的可供性讓社交媒體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展和轉變,近年來網絡社會也逐漸由各自為營的松散型節點向更為緊密的組織型發展,呈現出圈群化的發展趨勢⑩,這種新生的網絡組織形式引起了傳播方式的變革,原本松散離散的個人節點依賴技術可供性提供的圈群化可能實現了聚合,這種技術的可供性體現于社交媒體社會關系鏈建構下的好友添加選項;建立于意見領導和情感認同之上的關注與訂閱按鈕。每一個選項和按鈕的點擊背后都意味著一個新圈群的產生。
國外學者托夫勒將社會發展劃分成四階段,即史前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而學者劉明洋在此基礎上提出各個社會時期圈層建立的內部邏輯意涵著“血緣邏輯、地緣邏輯、業緣邏輯和趣緣邏輯”?。網絡圈群建構的內部邏輯除了上述所說的血緣邏輯、地緣邏輯、業緣邏輯和趣緣邏輯,還應包含網緣邏輯和閃緣邏輯。血緣邏輯所建構的網絡圈群是依附于個人強關系鏈條的親朋好友的集合;地緣邏輯是嵌合成員地理層級要求的網絡集合內層邏輯,建構地理位置要求的人的集合;業緣邏輯構筑的是個人社會角色關系鏈集合;趣緣邏輯在當下互聯網社會展現出強大活力,它是用戶離身化網絡活動中所表現的情感認同、價值取向的深層邏輯,通過相同的興趣愛好和價值觀建構相應的網絡圈群。網緣邏輯是指網絡技術革新帶來的擬態空間的群集可能,具有依托于網絡節點的泛在性。除此之外,本文還提出建構網絡圈群新的內部邏輯——閃緣邏輯,它建立在學者提出的泡沫圈群?的基礎之上,意指一種隨時建構或隨時消散的圈群聚集邏輯,具有邊界模糊、虛實交錯的特點,但卻可以通過用戶個人的收藏、轉發或再檢索完成再定位,從而實現由虛擬向實在的轉變。
網絡圈群的建構意味著傳播方式的變革,后疫情時代人們和社交媒體呈現出慣習式的生存樣態,這更加劇了傳播模式的革新速度。圈群化傳播,既描述了傳播的基本單位也說明了傳播的概念形式。人們基于一定的邏輯需求構建起網絡圈群,圈群之間的信息傳遞依靠不同圈群中相同成員的涵化來實現,圈群傳播的傳播效果受到傳播主體的信度和效度影響。如圖1所示,圈群A中的信息接受者是圈群E中的傳播主體,他將在圈群A中所獲得的信心傳輸到圈群E或者其他圈群中。傳播效率越快,效度越高,圈群越聚合,效率越慢,效度越低,圈群越離散。傳播主體信度越高,傳播效果更好,刻畫的傳播主體形象越高大,越容易出現在圈群的中心,反之亦然。圈群化的傳播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新冠疫情信息,而處于該圈群中的人們往往會將該信息發送到家族群、老鄉群或者朋友圈。后疫情時代圈群化的傳播方式仍然延續,這種傳播方式的嬗變橫亙于技術發展和時代變遷的整個時期,變現出歷時性和動態性的特征。

圖1 圈群化傳播可視化模型
二、后疫情時代下的輿論特征
(一)沉沒螺旋引致單向度格局
后疫情時代下,社會化媒體平臺成為輿論發聲的新陣地。不同于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社會化媒體平臺所具有的包容屬性為普羅大眾提供了自由言論的平臺。而在這樣一個缺乏權威管理的自組織言論集群中,沉默螺旋效應尤為凸顯。沉默的螺旋最早由學者伊麗莎白·內爾-紐曼提出,指代人們在意見發表過程中存在的多數觀點壓過少數觀點,使持少數一方意見的人逐漸趨于沉沒或轉向多數意見的社會現象。在社會化媒體平臺中,受制于平臺對評論內容的設置,人們往往綜合精力成本選擇閱讀被多數人所認可的意見而放棄后置于評論尾部的少數意見,難以全面地看清整個輿論,從而產生了一種意見趨于統一但正確性不明的單向度格局。
(二)網絡低門檻推動主體多元化傳播
從最初的2G通信技術到現在的5G通信技術再到未來即將登上時代舞臺的6G通信技術,這不僅單純代表網絡帶寬的擴寬,更代表著與其相配套的現代技術的變革與演進、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而技術的不斷發展進一步降低了用戶接入互聯網的準入門檻,媒介形式的更朝迭代馴化人們的使用習慣,移動手機設備成為人們的寵兒。社會化媒體平臺的建設為用戶提供了在網絡社會中發聲的機會,擬態化的網絡社會的所具有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網絡人士群體來源和影響力的廣泛性。?人人擁有網絡社會的發聲話筒,可以在“兩微一抖+快手”等的新媒體平臺發表自己的觀點,可以根據自身習慣選擇圖文、音頻、視頻等多元化的媒介形式利用平臺本身所具有的分享功能進行多級傳播,從而助推輿論群體多元化傳播,營造網絡社會獨樹一幟的輿論格局。
(三)疫情陰霾形構權威認同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速效化應急處理機制贏得了國際認同及稱贊,激發了集體使命感強烈的國人的家國情懷。集體記憶回涌達到個人情感的認同的高潮,加上新聞報道的量化呈現及國家治理的優劣對比,強化了人們對于國家政務機構舉措的認可和官方媒體話語的信任,從而形構了后疫情時代下的權威認同。
三、后疫情時代下的輿論引導困境
(一)網絡匿名、算法加持帶來的主觀難題
互聯網成為當下的主要輿論場,不僅是因為網絡社會所帶給我們的豐富的信息資源,還有它所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但是網絡匿名性的存在使網絡社會中的用戶可以不受法律或道德約束地發表不負責的言論,提高了輿論監測的成本。而突發公共事件的輿論也極易在這種不負責的心理引導下演變成非理性的群極事件。
除了網絡社會所具有的匿名性,平臺算法的加持也增加了輿論管控的難度。時下的多數社會化媒體平臺通常是以信息內容的流量屬性為推薦依據,即信息收獲的流量越多,越會被更多的人關注。但這種“流量至上”的推薦方式忽視了社會化媒體平臺該有的社會責任,阻礙了輿論的有效引導。
(二)危機索引、群體狂歡帶來的客觀難題
“索引性”是理解網絡輿論與社會危機之間關系的關鍵概念?,后疫情時代突發事件具有了與以往不同的傳播效力和影響力,用戶主觀層面的危機索引成為輿論引導的客觀性難題,其內部是對個人好奇心、信息知識索引的統合,主動的索引意涵著用戶對輿論的關注,危機索引致使的輿論凸顯使用戶重新卷入輿論的漩渦。
學者巴赫金提出狂歡理論,并將其換分為三個層級:狂歡節、狂歡式和狂歡化。狂歡節是現實層面的對于世界感受的意涵,狂歡式則是對于精神層面的信仰和儀式的崇敬,狂歡化則是身體與思想的解放,意涵著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例如現在的電商直播間營造的便是狂歡化的氛圍從而誘導受眾消費。群體狂歡使人們的言行更趨感性,注重于言語情感的陳述而忽視了事實真相的揭露,因此突發事件發生的輿論發酵不僅是真相浮現的過程也是解構狂歡重回理性的過程。
四、后疫情時代下的輿論引導策略
(一)創建實時主流輿論場并統合好其他輿論場
互聯網時代賦能個人參與輿論傳播,建構了不同意見主導的輿論圈子,圈內同聲意見相互影響,深化人們已有的觀念及認知,通過將社會場、媒介場、政治場與受眾的心理場融合在一起,產生互聯網輿論場?,意見領袖、議題、成員及傳輸渠道構成了動態發展的輿論場所。因此,后疫情時代下,針對突發事件所產生的輿論,主流媒體應當建立輿論源頭探索和及時發聲機制,堅持人本主義思想,理清輿論產生內因,對源頭問題進行彌補或解決。
此外,主流媒體還應不斷提升輿論掌控的話語權,議題的產生展現的是擬態社會潛在問題的涌動,議題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取向及相關程度是輿論走向的基礎,因此主流媒體不僅要提升話語傳播的效度還應增強輿論管控的力度,加強對意見領袖的引導,統合好其他輿論場的主導意見,營造良好的輿論生態。
(二)搭建非常態化的應急傳播體系
后疫情時代,受制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復,社會呈現出風險常態化的時代特征,同時網絡社會所具有的擬態化、離身性等特點,驅使人們爭相涌入,致使現實與虛擬逐漸分離,凸顯于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逐漸失衡、網絡亞文化的浮現等等。現實社會也因獨特的時代屬性,呈現出特殊的情境和語境,疫情相關的衍生報道成為后疫情時代下的主流傳播內容。
德國社會學家爾里希·貝克曾提出:“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而構建應急傳播體系是對風險社會認知的肯定。構建應急傳播體系首先要確定好政府機構及政務媒體的主體地位,只有樹立正確的輿論引領者,才能引導輿論正向發展。
應急傳播體系要具備系統性,即針對不同性質的突發事件,要統籌多種傳播機制,尤其注重在自然災害引發的突發事件輿論中物理傳播機制的建設,隨著應急廣播體系建設被列入“十二五”規劃綱要的文化事業重點工程,應急廣播公共服務?成為應急傳播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非常態化的應急傳播體系在實踐中實現了自身的不斷升級與完善。
(三)建立三級輿論引導格局和監管機制
三級輿論引導格局,即社會主流媒體立足于時下的輿論,把握輿論發展的關鍵節點,建立有效的意見領袖溝通機制,通過網格化管理增強輿論引導的效力。首先在關鍵節點把控方面,監控輿論趨向,審時度勢發布權威言論,及時引導輿論向常態化方向發展;其次,對輿論呈現出的流量節點進行掌控,及時與相關意見行為主體進行溝通,向其說明輿論問題的嚴重性及所關注輿論事件的具體走向。對于發聲人即輿論發生起點的情況,相關部門要及時調查輿論背后所呈現的具體問題,及時解決民眾問題或對謠言主體所產生的消極影響進行懲戒;再次,結合網絡社會所凸顯的社群屬性,通過入圈入群的方式去爭取受眾、獲得關注、傳播開來?。最后,建立智能化網格城鄉管理機制,通過政府帶頭,由上到下、全員落實、實時更新、智能填報和檢索,從而實現現實情境中的輿論引導。
建立個人、平臺和國家政策的三維監管機制。個人層面,受眾自身首先應當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對于從網絡中獲取的信息,一定要辨別真偽。同時,對于網絡上的謠言及時監察舉報。平臺層面,要深化議程設置,強化內容審核,推行網絡實名,出現問題及時發現并治理。最后,國家層面要加強主流思想的引導,出臺法律法規或政策決議指導輿論監管過程中存在的無法可依、無據可查的問題。提升政務媒體新聞信息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注釋:
①丁柏銓.后疫情時代的新聞輿論工作與社會治理[J].新聞愛好者,2021(05):4-9.
②李普曼.輿論學[M].林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③張成良:《融媒體傳播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頁.
④朱清河,宋佳.中國共產黨早期新聞思想的理論探索及其當代反思——基于張友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形成背景的考察[J].新聞春秋,2021(04):87-96.
⑤朱清河,宋佳.中國共產黨早期新聞思想的理論探索及其當代反思——基于張友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形成背景的考察[J].新聞春秋,2021(04):87-96.
⑥王國華,閔晨,鐘聲揚,王雅蕾,王戈.議程設置理論視域下熱點事件網民輿論“反轉”現象研究——基于“成都女司機變道遭毆打”事件的內容分析[J].情報雜志,2015,34(09):111-117.
⑦計永超,劉蓮蓮.新聞輿論引導力:理論淵源、現實依據與提升路徑[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23(09):15-26+126.
⑧王國華,魏程瑞,楊騰飛,鐘聲揚,王戈.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的網絡輿論危機應對研究——以上海踩踏事件中的@上海發布為例[J].情報雜志,2015,34(04):65-70+53.
⑨李沁.沉浸傳播——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43.
⑩崔家新.網絡社群的圈群化轉變:動因、影響及應對[J].寧夏黨校學報,2020,22(04):105-111.
?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黃明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劉明洋,王鴻坤.從“圈層傳播”到“共同體意識”建構——基于2011—2018年“十大流行語”的話語議程分析[J].出版發行研究,2019(09):56-62.10.19393/j.cnki.cn11-1537/g2.2019.09.024.
?張成良,王國蕓.云端社群:虛實泛化中的關系研究與模型探索[J].中州學刊,2021,{4}(06):161-166.
?劉騰飛.新時代網絡人士統戰工作研究[J].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21(04):61-64.
?焦玉良.危機索引與資源約束:網絡輿論的功能分析——對紅十字會危機的解讀[J].新疆社會科學,2016(02):131-136+162.
?趙姍.互聯網輿論場視角下主流話語引導力提升的精準化設計研究[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3):12-19.
?烏爾里希·貝克著.何博聞譯:《風險社會》.[M].上海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李曉北.應急廣播:現代化應急治理體系的創新[J].青年記者,2021(17):16-19.
?丁建庭.“圈群”時代新聞媒體在應急傳播中的作用[J].青年記者,2021(17):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