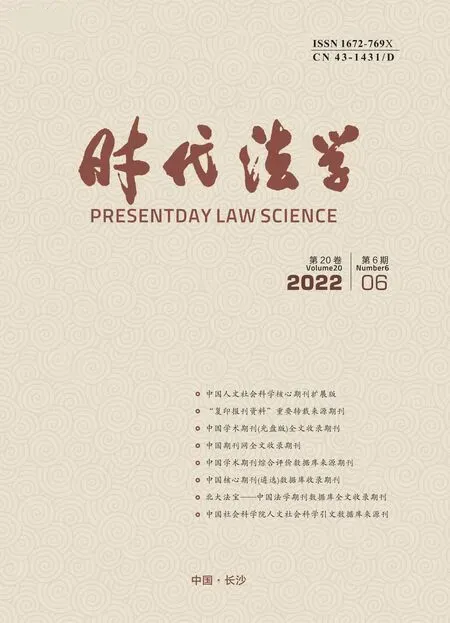論受賄犯罪的法益:職務行為不可交換性說的提倡與檢視
鄭澤星(中南大學法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2)
受賄犯罪的法益保護一直是刑法學研究中被廣泛探討的問題。近年來,學界對于受賄犯罪保護法益的關注度日益提高,但并未形成理論上的統一定論。在我國,受賄犯罪法益學說先后經歷了“國家機關正常活動說”以及目前占據通說地位的“廉潔性說”,近年來,隨著學界對于德日刑法理論的繼受,“不可收買性說”和“公正性說”已經形成了對“廉潔性說”的夾擊之勢。此外,仍有學者提出新的理論主張,如“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不可交易性說”以及“公職不可謀私利說”等等。各種理論學說之間互相辯駁,但究竟應采何種觀點,學者們難以形成共識。本文認為,“不可收買性說”存在解釋論上的缺陷,應當對其進行修正,具體方法是以職務行為不可交換性的表述代替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表述,從而賦予“不可收買性說”更豐富的內涵,以應對反對論者對于“不可收買性說”的詰難。為厘清受賄犯罪法益之爭并提倡“不可交換性說”,本文將梳理受賄犯罪法益的不同學說并分別作出評析,然后嘗試從不同學說的相互辯駁中探尋確定某一犯罪法益應當考察的基本要素并據此對不可交換性說進行教義學上的檢視。
一、受賄犯罪法益學說梳理
我國學界關于受賄犯罪法益觀點始于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說[注]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2.,對于受賄罪法益的真正討論則始于廉潔性說,之后學者們又提出了“不可收買性說”“公正性說”“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不可交易性說”以及“公職不可謀私利說”等學說。
(一)國家職能正常實現說
“國家職能正常實現說”又稱“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說”,持該說的學者們認為,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為國家職能的正常實現。腐敗行為對內危及國家的正常秩序,對外損害公眾對于公共決策公正性的信賴[注]Loos. Welzel-FS:890.,進而導致國家的正常職能難以實現。德國學者多林(D?lling)將公務人員的義務分為一般義務和特別義務,所謂一般義務是指公務人員依照客觀準則無私地履行其職務,公正地實現其任務以服務于國民全體。特別義務則是指禁止公務人員在職權行使范圍內謀取私利。一般義務履行只在從正面維持國家職能的正常實現,特別義務的履行,則通過防止職務行為與私人利益的互換,從而避免公務人員違反義務實施職務行為的可能性,進而從反面維持了國家職能的正常實現[注]D?lling.Jus 1981:574.。
(二)廉潔性說
“廉潔性說”發端于法益學說引進之前,“受賄罪的直接客體就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嚴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上的貪婪,也就是國家設置受賄罪的宗旨所在”[注]郝力揮,劉杰.對受賄罪客體的再認識[J].法學研究,1987,(6):55.。對于何為廉潔性,持該說的學者有不同的闡釋:一種觀點認為廉潔性即職務行使的合規性,它要求國家工作人員依據法律和有關制度規定承擔國家賦予的特定義務,正確行使國家賦予的特定權力[注]孫謙,陳鳳超.論貪污罪[J].中國刑事法雜志,1998,(3):36.。另一種觀點則從廉潔本身的含義出發闡釋職務行為廉潔性的內涵:廉潔的本質含義就是“在金錢方面沒有欺詐或者欺騙行為的”“不損公肥私、不貪污”,所以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從其字面含義來理解,應當是兼有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和職務行為的公正性[注]呂天奇.賄賂罪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120.。又如,有學者指出,除應得的合法報酬之外,國家工作人員不能以作為或者不作為為由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否則即構成對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害[注]曲新久.刑法學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56.。顯然,后一種觀點在廉潔性說的支持者內部占絕對多數。雖然對于廉潔性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刑法學者多持“廉潔性說”。
(三)不可收買性說
“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說”(Unk?uflichkeitoderUnentgeltlichkeit der Amtsführung)首先在德國帝國法院的判決中得以確立[注]RGSt 63:369f.,該說認為,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受來自于第三人用作收買利益的“私人利益”的影響,并因此違背了對國家的忠誠義務而損害了公眾對于職務行為“公正性”的信賴[注]Henkel.JZ 1960:508.。在我國,“不可收買性說”是學者在批判廉潔性說的基礎上提出的。在支持的學者內部,存在對于“不可收買性說”基本內涵的不同認識。部分觀點認為,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即為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兩者之間沒有本質區別,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的[注]劉艷紅.刑法學(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449//葉良芳.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一種實用主義闡釋[J].浙江社會科學,2016,(8):31//李少平.行賄犯罪執法困局及其對策[M].中國法學,2015,(1):16.。有學者則突出了“不可收買性說”與信賴說的關聯,認為公眾對于職務行為客觀公正性的信賴是以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為前提的,“不可收買性說”和信賴說只不過是觀察角度不同,二者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注]孫國祥.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其實踐意義[J].法律科學,2018,(2):133.//王春福.受賄罪法益之展開[J].人民檢察,2009,(21):54.。一般認為,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與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具有內在關聯,兩者存在類似于目的與手段的關聯,同時兩者又相互區別。受賄犯罪侵害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或者說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與財物的不可交換性[注]張明楷.刑法學(第5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03.。也有學者提出受賄罪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易性的觀點,其大致主張與“不可收買性說”類似,在此不再分別列述[注]孫國祥.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其實踐意義[J].法律科學,2018,(2):133-136.。
(四)公正性說
“公正性說”又稱“純潔性說”“純粹性說”,該說最早由德國帝國法院在判決中確立,該說認為受賄罪侵犯了職務行為的純潔性(Reinheit der Amtsausübung)。早在1938年,德國帝國法院即在判決中確定了“維護職務行為的純潔性是對公眾而言極為重要的法益”[注]RGSt 72:237//BGHSt 10:241f; BGHSt14:131; BGHSt15:96.。該說認為,當職務行為與不被允許的利益相連結時就危及到職務行為的純潔性,并間接影響到公眾對于職務行為的信賴[注]D?lling.Die Neuregelung der Strafvorschriften gegen Korruption.ZStW 112:335.。在我國,有學者認為《刑法》第388條擴張了受賄犯罪的成立范圍,因此也波及了對受賄犯罪保護法益的理解,因而主張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應為職務行為的公正性。按照公正性說,將收受賄賂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的目的在于:防止在職務行為與賄賂之間建立對價關系,從而使得職務行為被不公正地實施。而賄賂犯罪所處罰的對象,正是收受賄賂這種行為所引起的對職務行為公正性的侵害及其危險[注]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條的解釋[J].法學研究,2017,(1):71.。
(五)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
張明楷教授針對學者們對“不可收買性說”的批評而對其予以修正,部分接受了“公正性說”和“信賴說”的觀點,區分受賄犯罪的不同類型而分別確定其保護的法益:“認為普通受賄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加重的普通受賄的保護法益則可能還包括職務行為的公正性;斡旋受賄的保護法益是被斡旋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以及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的不可收買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以及國民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注]張明楷.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J].法學研究,2018,(1):148.。
(六)公職不可謀私利說
“公職不可謀私利性說”最早由德國學者多林(D?lling)提出,其最初的表述是“為了確保公職人員對于職務的忠誠,應當將公共職務與私人領域相區隔”[注]D?lling.(Fn.8):C 49 f.。公職與私人利益相區隔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與社會相區隔的具體化,后者對于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注]Greco.Ann?hrungen an eine Theorie der Korruption. GA2016:251.。在我國,有學者提出了相近的觀點,認為在賄賂犯罪中體現了交換關系,但交換并非發生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而是發生在受賄人的職位所蘊含的公權與其所撈取的私利之間的交換。因此,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應當定位為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注]勞東燕.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J].法學研究,2019,(5):118-137.。
二、受賄犯罪法益學說的反思
正如上文所展示的,受賄犯罪的法益學說眾說紛紜。上述學說中,國家職能的正常實現說已經鮮被國內學者提及,對于廉潔性說的批判似乎也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因此本文將重點反思不可收買性說、公正性說、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以及公職不可謀私利說。
(一)“不可收買性說”反思
“不可收買性說”較“廉潔性說”更為具體地揭示了受賄犯罪“錢權交易”的本質,從而將賄賂犯罪法益與貪污罪的侵害法益相區分。但是,對于“不可收買性說”也不乏批評,主要集中在其無法對我國刑法實定法層面的部分受賄犯罪類型予以合理解釋:在斡旋受賄的場合,實際實施的職務行為并不是被收買的對象,因而不可收買性說無法說明其處罰依據問題[注]鄭澤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賄賂之范圍[J].蘭州學刊,2011,(12):65.;在利用影響力受賄和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場合,受賄主體和行賄對象并不一定是國家工作人員,“不可收買性說”無法對賄賂如何能夠左右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進行合理解釋[注]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條的解釋[J].法學研究,2017,(1):71//黎宏.職務行為公正性說與事后受財行為的定性[J].中國法學,2017,(2):234.;在索賄的場合,索賄行為侵害的應當是職務行為的不可出賣性,這顯然無法涵括在不可收買性的語義射程之內[注]孫國祥.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其實踐意義[J].法律科學,2018,(2):133.//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0.。也有學者從“不可收買性說”的立論基礎對其予以反駁,認為職務行為并非當然無酬, “大部分由國家提供的服務和國家行為都是要付出費用或者提供對價的,因此不可收買性說立論的基礎即已不存在。”[注]Graupe. Die Systematik und das Rechtsgut der Bestechungsdelikt:95// Henkel, JZ 1960:508; Schr?der, GA 1961:290.此外,在德國刑法的視角下,受賄罪的利益包含了非物質利益,因而有德國學者提出,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說”并不能涵括此一部分非物質利益,因而不能作為受賄罪的適格法益[注]Nazanin Sporer. Die Auswirkungen der T?uschung im Rahmen der §§ 331,332 StGB:36.。
事實上,“不可收買性說”所表達的含義與職務行為的無酬性以及職務行為與財物的不可交換性是一致的,只不過采“不可收買性說”的表述使這一學說無論在語義內涵還是在解釋力方面都受到局限,因此本文認為應當以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代替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作為受賄犯罪的法益。下文將作進一步的闡釋。
(二)“公正性說”反思
相較于“不可收買性說”,“公正性說”從更高的層面描述受賄犯罪的法益,因而從表面上看來解決了“不可收買性說”涵括性不足的問題。但對“公正性說”也不乏質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公正性說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因而其法益區分性較弱,將其作為受賄犯罪的法益,不能從本質上對受賄犯罪以及同樣侵害職務行為公正性的職務犯罪進行區分[注]Geerds. über den Unrechtsgehalt der Bestechungsdelikte und seine Konsequenzen für Rechtssprechung und Gesetzgebung:47// Geppert. Jura 1981:46; Graupe, Die Systematik und das Rechtsgut der Bestechungsdelikt:77// Henkel. JZ 1960:508//Schr?der.GA 1961:290.;其二,對于特殊形式的受賄犯罪,“公正性說”不能給出合理解釋:在沒有違反職務義務的情形下,即通常所說的“受財不枉法”情形,公正性說無法準確說明對其予以規制的合理性。正如德國學者所批評的,“德國刑法典第331條和第333條中并沒有規定違反義務的職務行為,因此將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作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并無意義”[注]Geppert. Jura, 1981:46.;按照“公正性說”,對于事后受財行為,只能得出無罪的結論,但這一結論無論從司法實踐以及形勢政策的角度考量,都不具有合理性[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 條規定,“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后給予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第三,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上來看,如果采“公正性說”,則受賄犯罪的規定與同樣侵犯職務行為公正性的濫用職權罪的規定不相協調[注]張明楷.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J].法學研究,2018,(1):150.。“公正性說”部分揭示了受賄犯罪的特征,即公職人員在收受賄賂之后往往會作出傾向于利益提供者一方的決策從而損害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但這種描述并不周延,無法包含受賄犯罪的全部情形。此外,“公正性說”基于將斡旋受賄以及利用影響力受賄納入受賄罪法益的涵括范圍的考量而舍棄了受賄罪“錢權交易”的本質特征,因而不能認為是恰當的受賄犯罪法益。
(三)“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反思
從法教義學的角度來看,“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至少有如下缺陷:其一,在斡旋受賄場合,該說將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具體化為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的不可收買性,一方面,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不可收買性的重要性程度要低于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不具有解釋的當然性,上述解釋則不當地擴大了職務行為概念的內涵,使之缺乏必要的邊界[注]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0.。其二,在利用影響力受賄場合,該說認為國民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也屬于受賄罪保護的法益。因此,對于信賴說的批評也就當然適用于對這一修正觀點。例如有學者指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應當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之類的客觀內容,而不應包括對不可收買性的信賴之類的主觀內容,將“信賴”這種內容模糊、主觀色彩濃厚的要素作為保護法益不具有合理性[注]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 條的解釋[J].法學研究,2017,(1):69-70.。此外,也有學者從具體的刑法體系協調性的角度對“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提出質疑:“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不能解釋為什么斡旋受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處罰范圍要較普通受賄為窄[注]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0.。。“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實際上只是回應反對者對于不可收買性說的質疑的權宜之策,以之作為受賄犯罪的法益,理論上并不具有優勢,實踐中則可能使受賄犯罪的法益判斷復雜化,因此,如果有更為合理的法益學說,“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并非首選。
(四)“公職不可謀私利說”反思
公職不可謀私利說基于受賄犯罪的不法本質在于“違反不得用公共職位謀取私利的禁止性義務”的認識,而將受賄犯罪的法益確定為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如果嚴格依照公職不可謀私利性說的語義,基于公用目的的受賄則無法被涵括在受賄罪法益的解釋范圍內。詳言之,當收受或者索取賄賂的公職人員并非基于占為己用的主觀意圖而是基于公用的目的收受他人財物,或者在收受財物之后用作公用的,則不能認為符合公職不可謀私利性的法益界定,進而不能認定為構成受賄罪。例如某國土局領導心系鄉村教育,一心想為教育落后鄉村捐建一所希望小學,無奈公務員工資不高,積蓄甚少,一直未能如愿。后有房地產商向其行賄,請托其在建設用地審批中提供便利,該領導心想:“有了這筆錢,我就可以捐建一所希望小學了”。遂收受房地產商的賄賂款并為請托事項提供便利。后該領導將所得賄賂款全部捐給希望工程并如愿為落后鄉村建起希望小學。依照“公職不可謀私利性說”的立場,本案中的受賄官員并非為私利而收受賄賂,因此沒有侵犯受賄犯罪的法益,也就不構成受賄罪。這樣的結論,無論從司法實踐角度抑或從刑事政策的角度都是不能接受的[注]基于公用目的的受賄仍然成立受賄罪。參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6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出于貪污、受賄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收受他人財物之后,將贓款贓物用于單位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的,不影響貪污罪、受賄罪的認定,但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
三、法益確定的考察要素與不可交換性說的提出
(一)法益確定的考察要素
綜觀受賄犯罪不同法益學說之間的相互辯駁,可以歸納出學者們在考察法益是否適格時主要關注三個方面,即法益的專屬性、涵攝性以及協調性。首先,法益應具有專屬性,即法益應當能夠揭示某一犯罪區別于其他犯罪的本質特征,如果某一法益揭示了某類犯罪的共同法益,則不能認為其具有專屬性。其次,法益應具有涵攝性,即所確定的法益應當對目標犯罪的所有不同犯罪形態具有解釋力,當所確定的法益不能涵括目標犯罪的所有犯罪形態時,則不能認為其是目標犯罪的適格法益。再次,法益應具有協調性,即所確定的法益以及據此得出的解釋結論應當與現有的法律體系以及教義學結論相協調,如果兩者之間存在抵牾或者明顯的不協調,則不能認為其是目標犯罪的適格法益。
1.法益的專屬性與受賄犯罪法益的選擇
法益專屬性的基本內涵是特定的犯罪應具有特定的法益,不能以類法益或者復法益的存在而否定法益的專屬性[注]孫國祥.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其實踐意義[J].法律科學,2018,(2):134.,申言之,所確定的法益應當能夠揭示目標犯罪區別于其他犯罪的本質特征,如果所確定的法益除了揭示目標犯罪的本質特征之外,仍能涵括其他犯罪類型,則不能認為其是目標犯罪的適格法益。刑法規定的每一種犯罪之所以各自擁有不同罪名,原因正在于其與其他犯罪行為具有本質的不同,而確定法益的過程,即是揭示目標犯罪本質特征的過程,也是界分目標犯罪與其他犯罪的過程。貫徹法益的專屬性,對于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具有重要意義。具體到法益專屬性的確定而言,應當結合法益的位階性進行判斷,下文將結合受賄犯罪的法益進行詳細闡述。
2.法益的涵攝性與受賄犯罪法益的選擇
確定法益的過程中,仍應考慮涵攝性要素,即所確定的法益應當對目標犯罪罪名之下的所有犯罪形態具有解釋力,易言之,目標犯罪罪名之下所有的犯罪形態都應當能夠涵括到所確定法益的解釋范圍之內,否則,則不能稱之為適格法益。事實上,所有關于法益的爭論,大多是不同學說之間基于法益涵攝性的相互批駁。具體到受賄犯罪而言,如上文所述,反對學說對于“不可收買性說”的批評集中在“不可收買性說”不能對斡旋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以及索賄給出合理解釋[注]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條的解釋[J].法學研究,2017,(1):71.。而意圖擺脫“不可收買性說”涵攝性缺陷的公正性說以及“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同樣面臨涵攝性不足的質疑。易言之,學者們對于受賄犯罪法益的攻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法益的涵攝性進行的。因此,涵攝性的檢視也是“不可交換性說”教義學檢視的重點。
3.法益的協調性與受賄犯罪法益的選擇
協調性要素是法益在滿足專屬性要素、涵攝性要素之后,仍需考察的方面。其判斷的內容是所確定的法益以及據此得出的解釋結論是否與現有的法律體系以及教義學結論相協調,易言之,所確定的法益應當經受住體系解釋的檢驗并且符合教義學的邏輯[注]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7.。舉例而言,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那么,侵犯相同法益的行為,在侵害程度大致相同時,其法定刑也應當大致相同,這是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得出的當然結論。如果認為受賄犯罪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那么,對比同樣侵犯職務行為公正性法益并且以實害犯面貌示人的濫用職權罪,以侵害職務行為公正性法益的危險犯面貌出現的受賄犯罪反而配置了更高的法定刑,這一體系解釋的悖論從反面說明公正性說作為受賄犯罪法益并不具有妥適性。張明楷教授在對于“不可收買性說”的修正中,認為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侵害的不再是單一法益,而是復合法益,但從處罰范圍上來看,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均規定了“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限制條件,使得其處罰范圍較普通受賄犯罪更窄,申言之,依照“修正的不可收買性說”,侵害復合法益的斡旋受賄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處罰范圍要窄于侵害單一法益的普通受賄罪,這在解釋論上顯然難以自圓其說。
(二)“不可交換性說”的基本內涵
“不可交換性說”的基本內涵是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應為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其中,職務行為既包含收受利益的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也包含相關的其他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職務行為既可以是已經實施、正在實施的職務行為也可以是將來實施的職務行為;交換的方式就現階段而言指以財物為對價的交換,同時保留了將其解釋為以服務或者其他無形物為對價的可能性;交換的時機可以是實施職務行為之前、實施職務行為之時或者實施職務行為之后;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交換不要求合意,一方存在交換意圖并且實施交換行為即可。
(三)“不可交換性說”的界分
“不可交換性說”脫胎于不可收買性說,又與“不可交易性說”具有相似之處,在此有必要對三者進行語義上的界分。“不可交換性說”是對“不可收買性說”的修正,克服了“收買”在語義上單向性的缺陷,兼顧行賄人角度的不可收買和受賄人角度的不可出賣,從而體現了受賄行為的交易性[注]陳偉,汪潔,受賄罪相關問題探析——以受賄罪的交易性本質為視角[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6):119.。此外,相較于“收買”,“交換”在語義上的內涵更為豐富,基于此,“不可交換性說”較“不可收買性說”具有更強的涵攝機能,對于不能涵括在“不可收買性說”語義范圍之內的犯罪形態(如事后受財型受賄)具有解釋力。不可交換性在語義上與不可交易性類似,兩者仍存在差別:交易本指物物交換,后指做買賣[注]夏征農,陳至立.大辭海(第3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1624.,就其語義而言,交易具有正式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當場性,作“做買賣”理解時,雙方至少對買賣行為應具有合意,因此,采“交易”的語詞表述,不利于將事前沒有約定的事后受財納入到解釋范圍內。相比較而言,交換意為雙方各拿出自己的給對方[注]夏征農,陳至立.大辭海(第3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1621.,不論何時給對方,不論是否有合意,只要雙方相互交付,即是交換。因此,相較于交易,交換的表述則更具有隨意性,其語義的涵攝范圍更廣。
綜上,“不可交換性說”雖與“不可交易性說”以及“不可收買性說”具有語義上的相似性,細究其意涵,“不可交換說”的涵攝范圍更廣,因此本文采“不可交換性說”的表述。
四、“不可交換性說”的教義學檢視
根據上文的論述,法益的確定應當考察其專屬性、涵攝性以及協調性,本文對于“不可交換性說”的教義學檢視也將從這三個方面展開。
(一)“不可交換性說”的專屬性檢視
通過上文對于受賄犯罪法益不同學說的展示與反思,可以發現,雖然不同法益學說嘗試以各種方式描述受賄犯罪的本質特征以使其與其他犯罪相區分,但是基于描述角度的不同,各種學說既表現出相互重疊的特性,也分別表現出了各異的涵攝性,進而展示出了不同的位階性。具體而言,除賄賂犯罪之外,濫用職權犯罪也可能侵犯職務行為的公正性,賄賂犯罪和貪污犯罪都侵犯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賄犯罪、貪污犯罪以及瀆職犯罪都可能影響國家職能的正常實現,而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以及公職不可謀私利性雖然在具體的表述上存在差異,但都揭示了受賄犯罪“錢權交易”的本質,而都只能作為受賄犯罪的專屬法益而存在。根據上述法益學說所涵攝的犯罪類型的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不同的位階:其中,位于第一位階的是國家職能的正常實現說,其所能涵括的犯罪類型最多;位于第二位階的是公正性說、廉潔性說,除賄賂犯罪外,它們分別能夠涵括其他另一類犯罪類型;位于第三位階的是“不可收買性說”、“不可交換性說”、“不可交易性說”以及“公職的不可謀私利說”(見表1)。

表1 受賄犯罪法益學說的位階分析
總體而言,上一位階的法益具有類法益的性質,基本可以涵攝下一位階的法益,而作為具體法益的第三位階的法益,則并不能應用于描述賄賂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類型,因而屬于賄賂犯罪的專屬法益。在確定某一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時,應當首先考慮專屬法益。就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而言,只有位于第三法益位階的受賄犯罪法益學說(不可收買性說、不可交易性說、不可交換性說、公職不可謀私利說)符合法益確定的專屬性要求,能夠作為受賄犯罪的適格法益。因此,就專屬性的考察而言,“不可交換性說”表現出妥當性。
(二)“不可交換性說”的涵攝性檢視
1.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
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的法益是不同受賄犯罪法益學說聚訟的焦點,直接決定了學者們對于受賄犯罪法益的基本態度。整體而言,學理上對于斡旋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法益之爭的焦點在于是否承認上述場合中職務行為與財物之間的對價關系,即“交易性”。否定“交易性”的觀點認為,《刑法》第388條對受賄犯罪保護法益的傳統理解形成了挑戰,將受賄罪的本質由“權錢交易”擴展至“影響力交易”,這直接導致受賄犯罪的法益不再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注]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條的解釋[J].法學研究,2017,(1):67-70.。斡旋受賄場合,處于斡旋地位的行為人并沒有利用自身的職權,充其量只能說是利用了自身職位的間接影響,因而并不涉及職務行為與財物之間的出賣與收買關系[注]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1.。肯定“交易性”的觀點則認為,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并沒有否定受賄犯罪的交易性本質,同時認為,其保護法益應當是復法益,即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一方面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其中,不可收買性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本身(斡旋受賄);二是國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利用影響力受賄)[注]張明楷.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J].法學研究,2018,(1):159-163.。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說”脫胎于“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說”,其立論的基礎也在于承認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職務行為與財物之間的“交易性”。因此,對于否定“交易性”的觀點,應當自覺回應:“交易性”否定說的基本邏輯往往是收受財物的人與實施職務行為的人并不同一,因此難以認定特定的職務行為與給予財物之間形成了對價關系,也就不能肯定職務行為與收受財物之間的“交易性”。在本文看來,僅從此種意義上理解受賄犯罪的“交易性”過于狹隘。“交易性”的基本形態是實施職務行為的公職人員親自“出賣”其職務行為并取得相應的對價,但利害關系人通過“出賣”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而獲得利益所表現出“間接交易性”同樣未脫離“交易性”范疇。將職務行為用以交換的行為人所持有的對價雖非其自身的職務行為,但基于其身份、地位或者特定關系,又可以影響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正是基于此,刑法才對此類行為予以規制。當然,刑法也將此類行為的主體明確限定為基于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公職人員(對應斡旋受賄)以及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者關系密切的人(對應利用影響力受賄)。
“交易性”否定說的觀點仍然認為,《刑法》第385 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成立受賄罪,并不以職務行為與財物之間形成對價關系為必要。此外,以“交易性”為基礎的法益學說無法說明為什么有關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斡旋受賄行為的立法規定要求成立相應犯罪必須滿足“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注]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1-137.。關于第一個質疑,在本文看來,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規收受的回扣、手續費實際上也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職權)的對價:雖然其可能不存在具體的、直接的職務行為,但是,相應的回扣和手續費是與相關國際工作人員的職權密切相關的。易言之,如果國家工作人員不具有相應的職權,相關人員也不會為其提供回扣和手續費,而之所以為其提供回扣和手續費,目的正是獲得其在職權行使(職務行為)時的便利。因此,《刑法》第385條第二款規定的受賄罪,仍然沒有否定職務行為(職權)與財物之間的對價關系。關于第二個質疑,本文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條件是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對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要件所作的必要限縮。以斡旋受賄為例,對斡旋受賄的行為人進行處罰的依據是其利用了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但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與職務行為相比,在保護的必要性程度上要低得多,對這一類行為進行規制,則有必要以“謀取不正當利益”條件進行限縮。
“不可收買性說”和“不可交換性說”同屬承認受賄犯罪“交易性”的法益學說,但是其在語義上存在差異:不可收買性說的“收買”對應“出賣”,通常語境下,“出賣”權力者必須擁有權力或者至少擁有對權力的處分權,而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場合,國家工作人員對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密切關系人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均不具有“出賣”的權力,因此,對于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不可收買性說”存在語義上的解釋困境。而“不可交換性說”的“交換”,對于上述情形則仍具有解釋力:國家工作人員以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對價交換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密切關系人以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對價交換財物,則存在語義上的合理性。
綜合上述,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場合,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與財物之間仍然體現著“交易性”的特性。相較于“不可收買性說”的“出賣”要件,“不可交換性說”的“交換”能夠準確地詮釋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的“交易性”特征,因而體現出更強的涵攝性。
2.事后受財型受賄
事后受財型受賄可以分為事前有約定的事后受財和事前沒有約定的事后受財,前者為典型的受賄罪,此處僅討論后者。“不可收買性說”中,“收買”語境下,實施職務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與財物受特定時空限制,“收買”對應“出賣”,要求行為人在收受財物時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或者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圖,否則不能認為其在“出賣”權力[注]陳興良.判例刑法學(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642-644.。易言之,收買關系應當在買賣當時已經存在約定,而嚴格依照“收買”語義,事后受財型受賄中,職務行為實施時并不存在“買賣”的約定。而不可交換性說的“交換”在時空上則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因而其表現出更強的涵攝性:即使是實施職務行為時并不存在約定,而只有事后的受財的行為,也可以將事后收受的財物理解為職務行為的對價,從而肯定兩者之間的交換關系。
3.感情投資型受賄
感情投資型受賄是指公職人員收受沒有具體請托事項的財物提供者的財物的行為。在傳統刑法理論中,感情投資型受賄因為不滿足受賄罪“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而不構成受賄罪。根據本文的立場,“不可交換性說”中用以交換的公職人員職務行為可以是已經實施的、正在實施的職務行為,或者將來實施的職務行為,感情投資型受賄即是以現在的財物為對價,交換公職人員將來的職務行為或者對于將來職務行為的期待,從公職人員的角度而言,即將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或者將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這一解釋路徑契合了司法解釋關于感情投資型受賄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從而明確了感情投資型受賄應受刑罰處罰。從比較法角度來看,德國刑法也規定了單純收受賄賂行為的處罰:《德國刑法典》第331條收受利益罪(Vorteilsannahme)第一款規定:“公務員、歐洲公務員或特別受雇從事公共服務的人員,為自己或者第三人而對于職務行使,要求、期約或者收受利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罰金”。易言之,無論是否實施公務行為,公職人員收受利益的行為均構成犯罪。同樣,《德國刑法典》第333條規定的“提供利益罪”(Vorteilsgew?hrung),對是否實施職務行為,也沒有要求[注]StGB§331,§333.。
4.公用型受賄
公用型受賄是指受賄的目的并非為了私利而是出于公用目的或者將所收受的財物用于公共用途。按照刑法理論,受賄的目的為何在所不問,只要公職人員實施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并且收受了作為對價的財物,行為即已符合受賄犯罪的犯罪構成,至于收受財物的目的以及收受財務之后的用途,只能作為量刑時酌定考量的因素。如上文所述,“公職不可謀私利說”對于公用型受賄不具有解釋力。基于本文“職務行為不可交換性說”的立場,只要將職務行為與作為對價的財物互換即已構成對法益的侵害,至于受賄時的目的為何以及收受財物之后的用途,“不可交換性說”再所不問。可見,對于公用型受賄,“不可交換性說”具有解釋力。
(三)“不可交換性說”的協調性檢視
“不可交換性說”無疑會遭受基于協調性的質疑:如果承認受賄罪的“交易性”本質,那么行賄行為與受賄行為就會構成共同正犯的關系,兩種行為的不法程度沒有明顯差別,并且行賄方在賄賂犯罪中屬于主動方。基于此,不可交換說立場下行賄罪的法定刑期限至少應當不低于受賄罪的法定刑期限,這與刑法的規定并不協調[注]勞東燕.受賄犯罪兩大法益學說之檢討[J].比較法研究,2019,(5):137.。在本文看來,上述質疑忽略了賄賂犯罪在刑法中的體系地位。賄賂犯罪在刑法典中被規定在“貪污賄賂罪”一章中,本章中規定的犯罪都具有明顯的身份性特征,或者要求行為人具有特殊身份(如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者要求行為對象具有特殊身份。因此身份在本章犯罪中對于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扮演著重要角色。具體到賄賂犯罪中,行賄者只占據形式上的主動,受賄者則掌握實質上的主導權。詳言之,雖然在賄賂犯罪(索賄罪除外)中,行賄者的行賄行為是發動賄賂犯罪的主動因素,但是,是否接受賄賂,是否為他人謀利,決定的主動權卻掌握在具有身份的公職人員手中。此外,在賄賂犯罪中受賄者的身份決定了賄賂犯罪的實質,例如,當受賄者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時,行賄者構成行賄罪;當受賄者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時,行賄者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因此在賄賂犯罪中,表面上行賄者占主動地位,實質上則是具有身份的受賄者起決定作用。因此,從法益侵害性的角度而言,受賄罪具有更高的不法性,對其配置更高的法定刑也是合乎教義學邏輯的[注]許恒達.貪污犯罪的刑法抗制[M].中國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6.。因此,對于不可交換性說立場下行賄罪和受賄罪不協調的批評不具有妥當性。
五、結語
法律不是嘲笑的對象,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隨便批判法律,不要隨意主張修改法律,應當從更好的角度解釋疑點,對抽象的或有疑問的表述應當作出善意的解釋或推定,將“不理想”的法律條文解釋為理想的法律規定[注]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M].3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3.,這便是教義學的使命。關于受賄犯罪的法律及其司法解釋規定了數量眾多的受賄犯罪情形,給教義學的探討設置了不少障礙,但無論受賄犯罪情形如何駁雜,對于受賄犯罪法益的探討都不能偏離受賄犯罪“交易性”的本質,否則無異于緣木求魚,水中撈月。在承認受賄罪“交易性”本質的法益學說中,本文所主張的“不可交換性說”符合專屬性、涵攝性以及協調性的要求,能夠經受教義學的檢視,是受賄犯罪的適格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