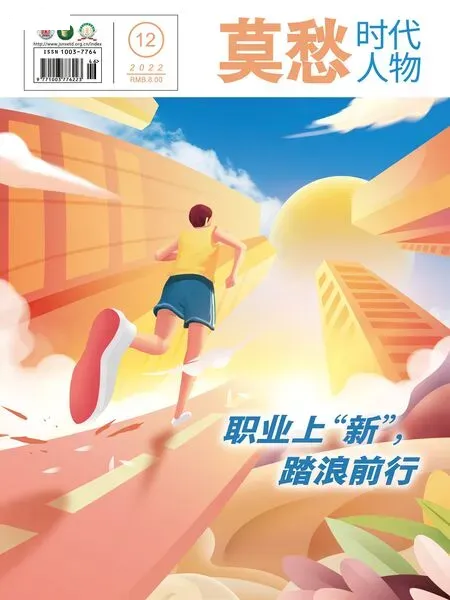葉培建,永不停步
文/春華

葉培建
半個世紀以來,從“中國資源二號”到“嫦娥一號”,從圓夢月球到逐夢火星,有一位老人為中國航天事業兢兢業業奉獻五十余年,一生矢志“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科學家”。他就是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技術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培建。在他的帶領下,中國的“奔月之夢”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圓夢之旅。他書寫了人類探月史上嶄新的一頁,讓中國航天人對星辰大海的向往不斷傳承。
與航天結下不解之緣
葉培建1945 年1 月出生于江蘇泰興胡莊鎮一個軍人家庭,父母都是新四軍戰士,沒滿周歲的他一直由外婆照顧。1951年,政府將葉培建送到一所軍隊子弟學校——南京衛崗小學。次年,抗美援朝的父親回到家后,葉培建跟隨父親“轉戰南北”,在南京、杭州、湖州都上過學。盡管如此,他僅用兩年時間就讀完初中所有課程,并因數學成績拔尖,被學校破格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學。
1962年,葉培建高中畢業。在填報志愿時,父親對他說:“國家正處于建設時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你應該立志報效祖國。”受父親教誨,葉培建高考志愿前四個填的全是有關國防與航空的,不料卻因成績太優秀,意外被浙江大學“扣留”。葉培建以為此生與航天無緣了,沒承想,他畢業后被分配到航天部衛星總裝廠任技術員。這令他喜出望外,第一時間打電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家人:“我又能搞航空航天了。”
1978 年,國門剛剛打開,葉培建考上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和502 所兩個專業的研究生,赴瑞士納沙太爾大學微技術研究所,攻讀博士研究生,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出國留學生。在瑞士留學期間,葉培建咬緊牙關迎難而上,爭分奪秒自學法語,并因學習刻苦出了名。瑞士一家報紙曾報道:他從不去酒吧,偶爾打打乒乓球,把周末的時間都用于看書和工作。記者問他:“為什么要這樣下功夫?”他說:“中國從那么多人中選派我出來學習,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我應該努力,為國家做些事情。”
1985 年,葉培建獲得納沙太爾大學的科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手寫中文計算機在線自動識別》,這在20世紀80年代,全中國也沒幾個人能懂。同年8 月,年逾四十的葉培建學成回國。從考大學、出國留學再回來工作,在葉培建漫長的奮斗生涯中,面臨多次選擇,但對他來說,做選擇不是難事,四個字貫穿始終——國家需要。
從“中國資源二號”到“嫦娥一號”
1992 年,空間技術研究成為葉培建研究的主戰場。四年后,他擔任“中國資源二號”衛星總設計師兼總指揮,開啟領導衛星研制工程新征途。“中國資源二號”衛星主要用于國土資源勘查、環境監測與保護、城市規劃、農作物估產、防災減災和空間科學實驗等領域,技術起點高、研制難度大,屬傳輸型對地觀測衛星。在當時是“最大最重,具有最高分辨率、最快傳輸速率、最高姿態精度、最大存儲量”的一顆衛星。
盡管壓力重大,但他卻對技術難關的挑戰備感興奮。“中國資源二號”衛星有效載荷很大,過去的試驗條件不能適應大部件要求。葉培建大膽而科學地提出,改進試驗條件的方案,從而保證了試驗質量和產品安全。他常說:“對質量問題要提倡‘捕風捉影,對技術上的表象要‘追根溯源’。”他提出衛星進入發射場前,要進行可靠性增長試驗,把問題徹底解決在地面。他還率先實踐了把電測與總體隊伍分開的做法,既合理分配資源,又為測試隊伍的專業化奠定了基礎。
2000 年9 月1 日,“中國資源二號”01 星從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升空。這是我國自行研制的首顆傳輸型遙感衛星,無論從社會經濟建設還是國防建設方面,都被寄予厚望。這顆衛星對于葉培建也有著特別的意義——這是他擔任總設計師后研制的第一顆衛星。“中國資源二號”的成功發射且穩定運行,標志著我國航天遙感技術日臻成熟。
葉培建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更重要的任務來了。2004 年,我國探月工程批準立項,年近60歲的葉培建出馬,擔任“嫦娥一號”衛星總設計師兼總指揮。“嫦娥一號”是我國探月工程的第一顆繞月人造衛星,面對一些國際航天強國的技術封鎖,葉培建只能帶領科研團隊“創新”。葉培建說:“過去衛星在地球附近飛,只有一個軌道,現在要讓衛星從地球飛到月球,完全是兩個概念。”三年內要設計出一個全新的航天器,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葉培建舉步維艱之際,妻子卻不幸去世。他化悲痛為力量,忘我地工作。葉培建將衛星系統總指揮和總設計師“一肩挑”,帶領平均年齡不到30 歲的研制團隊沒日沒夜為“嫦娥”奮戰。在近四年的時間里,“嫦娥一號”研制團隊夜以繼日,攻克了“軌道設計與控制,測控和數據傳輸,制導、導航與控制,熱控技術”等一系列技術難題,拿下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2007 年10 月24 日,“嫦娥一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之后,經歷八次變軌進入月球軌道,正式開展繞月探測任務。很多人不知道其中攻克了多少難題,尤其當衛星進入月球引力區時,在衛星軌道上要反復核算,真正做到萬無一失。作為中國首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成功繞月,是繼人造地球衛星、載人航天飛行之后,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又一座里程碑,標志著中國邁出深空探測的第一步。他帶領團隊鋪就出中國第一顆月球探測器的“奔月”之路。
用“航天夢”托舉“中國夢”
2013年,“嫦娥三號”探測器完成落月任務后,大家對“嫦娥四號”的規劃仍存在一定的分歧。當時很多人認為嫦娥四號落在月球正面更為可靠。葉培建力排眾議,在他看來,遙感、氣象、通信等應用型衛星應該力保成功,但包括“嫦娥”系列探測器在內的探索性衛星,應該給予更多機會,去做探索性的創新。在葉培建的堅持下,2019年1月3日,“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著陸在月球背面的馮·卡門撞擊坑。對于“嫦娥四號”任務的成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一位專家感嘆道:“我們再也不能說中國人只會跟著干了。”
2021年5月15日,76歲的葉培建又迎來人生一次大考。凌晨,北京飛行控制中心指揮大廳氣氛凝重,經過約十個月的飛行,“天問一號”進入著陸窗口,準備在火星著陸。作為我國首次發射的自主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要一次性完成“繞、落、巡”三大任務,其中“落”的難度最高、風險最大,每個環節必須確保精準無誤,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整個任務的失敗,這是讓葉培建感到壓力最大的一次任務。2021 年5 月15 日7 時18 分,“天問一號”探測器在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預選著陸區成功著陸。在電視直播畫面中,葉培建紅著眼睛鼓掌的鏡頭令人動容。但不為人所知的是,鼓完掌后,他發現自己站不起來了。幾十年如一日的超負荷付出,讓他落下了一身傷病。葉培建打趣地說:“從我當總師開始就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現象,只要我腰疼就成功了。‘中國資源二號’打過三發,我有兩發是躺在床上指揮的。”
為航天事業奮戰了五十余載的葉培建,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寫成了兩本書,第一本叫《走在路上》,第二本叫《永不停步》。他說,中國航天事業,一直走在路上,并且永不停步。為了傳好“接力棒”,他走進高校任教,定期給本科生傳道授業。如今,77 歲的葉培建更多是站在幕后,扶持年輕的航天工作者,為他們“撐腰、鎮場”,是無數年輕人心中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