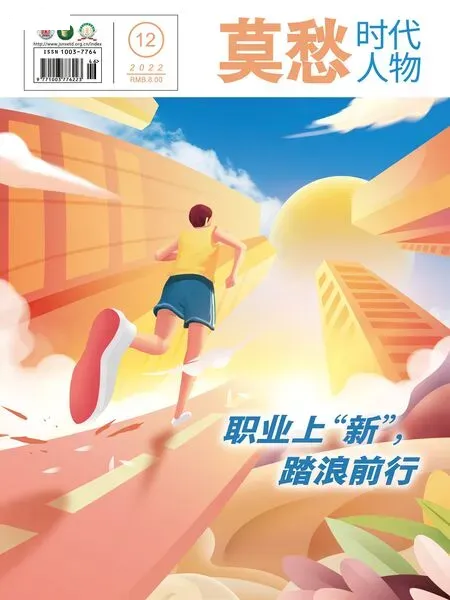瞿秋白在莫斯科
文/劉維榮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重視革命理論與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黨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早在《餓鄉紀程》中,瞿秋白就指出:“一切真理,從物質的經濟生活到心靈的精神,都密切依傍于實際。”
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1920年8月,俄文專修館尚未畢業,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報館和上海《時事新報》報館聘為駐蘇俄特約通訊員,赴莫斯科采訪。在登上赴蘇俄征程的101 天里,瞿秋白沿途調查采訪寫作,備嘗艱辛,終于在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斯科。
1
在莫斯科的兩年中,瞿秋白三次見到革命導師列寧,為中國讀者采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成為俄國革命后最早系統地向中國人介紹蘇俄實況的新聞界先驅。
1921 年6 月22 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遠難忘的日子,他和張太雷在克里姆林宮安德萊廳第一次見到了列寧,并在會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親耳聆聽到列寧的教誨。“列寧發言三四次,德語、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是將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節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的紀念集會,又一次見到了列寧,并聆聽了他的演講。“工人群眾的眼光,萬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寧身上。大家用心盡力聽著演說,一字不肯放過。”瞿秋白親眼觀察工人群眾對自己領袖的尊敬和愛戴之情,受到了莫大的教育和鼓舞。正如友人鄭振鐸所言:“那些充滿熱情和同情的報道,令讀者們對于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充滿無限向往之情,我相信那影響是很大的。”
瞿秋白旅蘇期間所寫的兩本散文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真實地記錄了蘇聯十月革命后的社會情況,同時也真摯地敘述了自己世界觀變化的過程。他把這兩部書稿寄回國內,由其好友鄭振鐸編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瞿秋白在蘇俄兩年,夜以繼日地寫出了60 多篇旅俄通訊,其中40多篇在《晨報》和《時事新報》的“莫斯科通訊”專欄發表,共約16萬字,另外還有約15篇在遞送途中被郵局遺失了。
1921 年3 月,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列寧出席大會并作了報告。他敏銳地看到了這次大會的重要意義,集中精力寫了長篇通訊《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全文約3萬字,在《晨報》連載27(天)次。
2
1921年秋,為了培養革命干部,列寧創辦了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并開辦了“中國班”,瞿秋白任翻譯和助教。中國班單獨編一班,該班學生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蕭勁光等。
1921年5月,瞿秋白由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黨組織,1922 年2 月,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不久,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又一次表述自己的志愿:“‘我將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類新文化的胚胎。……‘我’不是舊時代之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固然不錯,我自然只能當一很小很小無足重輕的小卒,然而始終是積極的奮斗者。”
在旅居蘇俄期間,瞿秋白還寫了《俄國文學史》,書中包括“民間文學”“古代文學”“俄國文學之黎明”“普希金”“托爾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等共19章,對俄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和作家、詩人的評價,均有獨到的見解。
瞿秋白最早翻譯了列寧的《列甫·托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和《L.N.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以及蘇俄杰出的文藝理論家普列哈諾夫的《易卜生的成功》《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法國的戲劇文學和法國的圖畫》《唯物史觀的藝術論》等文藝論文。他對蘇俄文化的傳播是多渠道、多層次的,又是非常投入的。這方面的工作是瞿秋白革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付出了他的畢生精力。
3
1923 年1 月23 日,瞿秋白隨中共領袖陳獨秀從蘇俄回到了闊別兩年之久的祖國。
為了更好地傳播列寧主義,瞿秋白翻譯了斯大林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列寧主義概述》部分,同年4 月22 日在《新青年》第1 號上發表。在此之前,瞿秋白嚴格遵循“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的原則,還撰寫了許多介紹列寧、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面的文章。
《新青年》季刊1923 年6 月15 日第一期,就有7篇是瞿秋白的譯著,具體包括重譯了《國際歌》,號召中國共產黨人要為“英特勒維納爾”的最終實現而努力奮斗,以及《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共產國際的黨綱、策略、《俄羅斯革命的五年》。瞿秋白專門撰寫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新青年》季刊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這期《新青年》上,還刊登了一首歌頌十月革命,歌頌中國工人階級英勇斗爭,號召人們起來革命,為實現“共產大同”的歌曲《赤潮曲》,詞作者“秋蕖”就是瞿秋白。歌詞中寫道:“赤潮澎湃,晚霞飛動,驚醒了五千余年的沉夢。遠東古國,四萬萬同胞,同聲歌頌神圣的勞動……”
1925 年4 月22 日,中共四大決定把《新青年》由季刊改為月刊,仍由瞿秋白主編。第1號就是紀念列寧逝世一周年的專號,瞿秋白發表了《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紀念文章。
1926年1月,列寧逝世兩周年,瞿秋白在《向導》第143 期上發表了《列寧主義與中國國民革命》的紀念文章。借列寧逝世三周年之際,在瞿秋白參與編輯的《向導》周報第184期上刊登了《列寧逝世紀念特刊》,說明中國革命運動如此蓬勃發展,正是中國共產黨靈活運用列寧主義的成效。
為了紀念列寧逝世四周年,瞿秋白負責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在第15期封面扉頁上發表了悼念列寧的短文《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號召中國人民要推翻國民黨這個新式的青天白日的軍閥統治。
“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饑寒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正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第五章中所寫,瞿秋白長久地熱烈而堅決地信仰著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