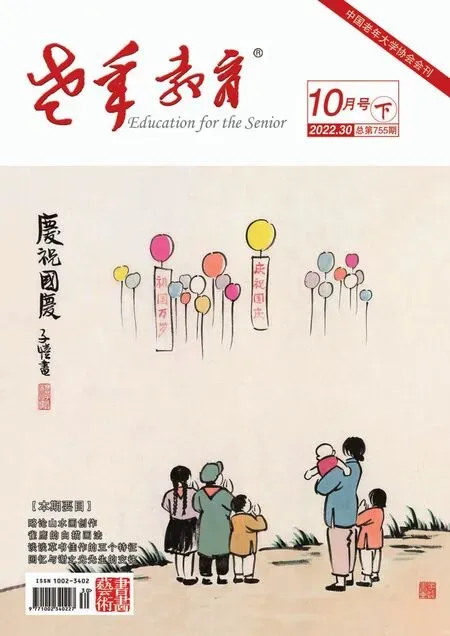詩畫相映共頌偉大勝利
——李可染《鐘山風雨》賞讀
□尚玉新
1949年4月20日,解放戰爭進入尾聲,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21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當夜,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1000余里的戰線上分三路強渡長江,發起著名的渡江戰役。解放軍以木帆船為主要渡江工具,一舉突破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解放南京、武漢、江蘇和安徽兩省全境、浙江大部,以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整個戰役的勝利,為解放華東全境和向華南、西南地區進軍創造了重要條件。23日晚,東路由陳毅率領的第三野戰軍占領南京。毛主席聽到這個消息后歡欣鼓舞,于是寫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1964年,李可染先生根據毛主席的這首詩(1963年12月正式發表)創作了《鐘山風雨》,并將全詩題于畫面:“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大篇幅的落款,使詩詞內容的豪情和畫面景象的雄偉相輝相映,將戰場的震撼場面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此圖在創作上以傳統水墨為主,結合西方油畫技巧來營造硝煙彌漫的渡江場景。圖中,解放軍的渡船呈斜向排列,朝著遠處硝煙中的南京城門駛去,渡船上的紅色軍旗在勁風中飄揚,充滿力量,體現出解放軍作戰驍勇、不畏艱險的英勇氣概,以及上下一心為解放全中國而英勇奮戰的精神面貌。遠處被硝煙籠罩的南京城門顯得弱小不堪,暗示出在解放軍強大火力的攻勢下,南京的解放已近在咫尺。
整幅作品以線面結合,大量的線條融于運用豐富、層次分明的團塊性筆墨之中,顯得濃重渾厚、深邃茂密,整體單純而內涵豐富,完美地體現出戰爭的宏大場面與緊張氣氛,帶給觀者以直面戰爭的現場感。一排排戰船,猶如一支支利劍刺向被硝煙籠罩著的黑暗世界。水墨皴染的手法和留白的處理既將炮火連天的激烈戰爭場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又好似這黑暗中透出的光明,象征著革命勝利前的曙光。斜向右上的留白將畫面分割成占比懸殊的兩部分,寓意著敵我雙方在氣勢和戰斗力上的懸殊;畫面的落款與戰船一道,形成畫面線條存在的壓倒性優勢,猶如天兵壓陣般沖向敵營,預示著勝利的必然到來。
《鐘山風雨》既然是以渡江戰役作為描繪主題,則必然離不開戰船,其自然也成了這幅畫的主角。畫家對畫面的構圖可謂獨具匠心,戰船既如左上至右下斜向排列的多組平行線對著城門“萬箭齊發”,又如一條“S”形巨龍直奔南京城蜿蜒而去。近處戰船以寫實而出,與江水融為一體;中遠景戰船則與硝煙相融,虛實相生,增添了畫面的空間感和戰場的縱深感;船上人物雖以概括性筆觸點出,但臨危不懼的大無畏精神依然可被感知。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以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及詩人的多重視角,描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的雄偉場面,贊頌了南京解放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表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徹底打垮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的信心和決心,全詩格調雄偉,氣勢磅礴,雄壯有力,充滿革命豪情。《鐘山風雨》則以繪畫的形式描繪出渡江戰役的震撼場面,以直觀的形象將觀眾帶入那段宏大的歷史場景中。繪畫雖然通過瞬間場景來表現歷史事件,但畫面形象所帶來的生命力和熱烈氣氛依然能夠引發我們結合自身的知識展開想象,去豐富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而完成繪畫本身的價值所在。

《鐘山風雨》李可染 92.2cm×57.3cm 1964年作 江蘇省美術館藏
李可染的山水畫注重意象的凝聚,減弱了意象與形式的獨立性,同時將傳統、西法、自然三者結合,尤其是光線的引入,形成了畫面的朦朧、流光之感。《鐘山風雨》在詩與畫的結合上相得益彰,把中國畫的傳統筆墨與西方繪畫的光影相融相生,以獨特的藝術形式將戰爭氣氛描繪到極致,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無堅不摧、勢如破竹的氣勢完美呈現在觀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