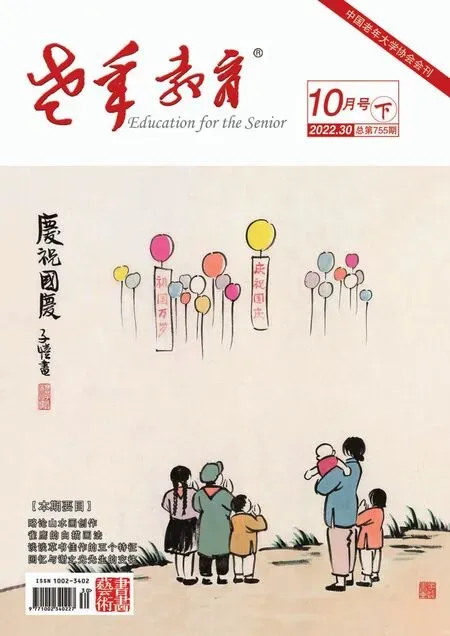干支、年歲、題款與古代書畫的辨別
□王永林
由兩個不同的機緣,我讀到了兩件署款為清初蕭云從的繪畫:一件是一冊來自公立博物院的借展作品,一件是一卷來自香港拍賣行由日本回流的“重要”拍品。這兩件作品的可研究之處,在于古代繪畫流傳中關于創作者非常重要的辨別依據上。其中“干支、年歲”是作者創作時間點的準確記錄,是相互匹配的,而長篇“題款”則往往關乎作者的創作緣由、環境、氛圍及當時的生活狀態、心境等,除題畫詩句(自作詩或他人詩)偶有重復,其他題句文字大都是不會重復的。因此,干支、年歲、題款是對古書畫進行辨別時,除繪畫本身筆墨的個性特征、造境的時代風格這些關鍵點外,同樣非常重要的辨別依據,有時甚至能起到判其“生死(真偽)”的作用。
來自公立博物院藏的山水畫冊頁,于末頁款題曰:“癸卯夏五,客采江,蔚宗同硯時五子在魯,篤學繪事,因作稿本,月余遂成冊,山煙水漳,佳氳沸升,為近況第一樂事,幸勿以塵飯土羹視之也。七十翁云從識。”第一眼的感覺是書法與蕭云從有距離,且印章位置甚為局促,頗似后加款印,再讀到其中的“癸卯”干支與“七十翁”年歲時,就更生疑竇。因為“癸卯”這一年的蕭云從并非“七十翁”。蕭云從出生于1596年,卒于1673年,癸卯應為1663年,蕭氏時年應為實67歲、虛68歲(書畫家多以虛歲署款),故干支與年歲是完全不符的。也許有人會說,如是作偽,作偽的人為何不查干支和年歲呢。這就牽涉到古人作偽的局限性,同時古人作偽還往往有一種道德上的負罪感,有時會故意賣一破綻,以為自欺,不似今人作偽那么無所不用其極。
再看從日本回流到香港拍場的近六米長的山水長卷。圖畫山重水復,頗為繁密,然細看用筆明顯與蕭云從的皴筆存在距離,用筆、皴法、構圖雖有蕭氏作品的影子,但很板刻,沒有其用筆的力度,山石結構也太實。再看題款,書法也顯得太嫩,沒有73歲蕭云從的那種老到,細讀題句卻讓我生出似曾相識的感覺,其款曰:“戊申(1668 年)秋七月,臥居靜齋,憶河陽李古年近八十,多喜作長圖大障,至為高宗所眷愛,爰題其卷曰:李唐可比唐李思訓。余草野中人,無緣獻納,近雖衰老,猶不肯多讓古人,于是極力經營,勉為此卷,自覺落筆矜慎,谷幽深,云煙澹逸,意興所到,饒稱俊逸,留此以俟知我。鐘山老人蕭云從時年七十有三。”這與清宮舊藏《石渠寶笈續編》著錄之蕭云從《谷幽深卷》題句幾近相同:“丙午(1666年)菊月,臥居靜齋,憶河陽李古年近八十,多喜作長圖大障,至為高宗所眷愛,爰題其卷曰:李唐可比唐李思訓。余草野中人,無緣獻納,近雖衰老,猶不肯多讓古人,于是極力經營,勉為此卷,自覺落筆矜慎,谷幽深,峰巒明秀,亦生平所僅有者,藏之以俟知我。區湖蕭云從畫并記。”兩卷“創作”時間相距兩年,“戊申”卷除畫、字都有問題外,我們也不能想象蕭云從在創作“丙午”卷兩年后,再度創作時會完全照抄自己以前的題款,而僅僅在首尾更改幾字,這完全不符合蕭云從這樣一位文人畫家的創作風格與題款習慣。

“癸卯”冊題款

“戊申”卷題款
此卷后由《四庫全書》總裁官、侍郎曹文埴進獻給清乾隆皇帝。乾隆在其“題蕭云從山水長卷(《谷幽深卷》)”詩注中,曾特別寫明:“蕭云從,蕪湖人,國初時工畫山水。昨四庫館進其所著《離騷圖》,檢石渠所藏,向無云從跡,侍郎曹文埴因進所藏山水長卷,筆墨高簡潔凈,頗合古法。”對于蕭云從自識題字則評曰:“蕭云從自識云:河陽李古年近八十,多喜作長圖大障,至為高宗所眷愛,爰題其卷曰:李唐可比唐李思訓。余草野中人,無緣獻納,雖衰老猶不肯多讓古人,于是極力經營,勉為此卷,藏之以俟知我。其言頗見誠懇,今百余年后,卷入石渠,競符其愿,豈非翰墨有緣耶?”乾隆壬寅(1782年)題蕭云從此卷墨寶時,已是蕭氏逝世一百余年后,真可謂一段百年翰墨之奇緣也。由上所述,這兩件署款蕭云從的作品,雖“癸卯”冊為公立館藏,“戊申”卷也有日本多次早期著錄出版,但從學術的角度來講,我還是持存疑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