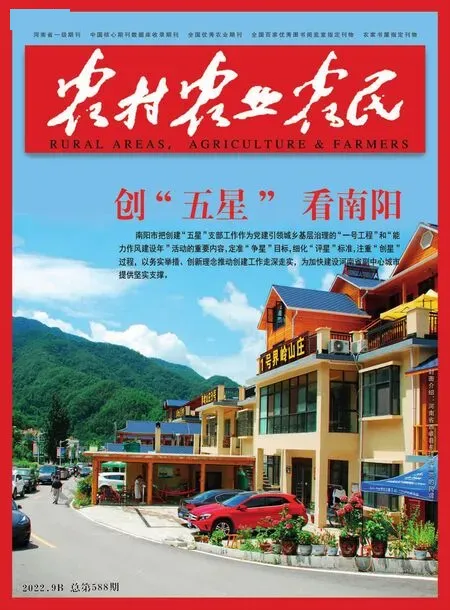村干部“微腐敗”形成機理及治理對策
旦雅寧
(云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
一、問題的提出
腐敗是自古以來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也是現代國家治理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課題。孟德斯鳩曾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監管一直被認為是腐敗滋生的根本條件。村干部這一群體雖屬最基層的干部,級別較低,但其相對權力比較集中,村內各種公共事務都由村干部管理,處于權力集中且監管不足的狀態,易滋生腐敗。尤其是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鄉村扶貧、鄉村產業、土地流轉等事務下放到鄉村,主要村干部逐漸掌握各項資源,成為村級各種公共事務的“把關人”。然而,一些村干部卻違背用權為民的初心,在權力面前迷失自我,逐漸背離黨的宗旨,置黨的事業、人民利益于不顧,通過編造資料、虛假冒領、套取截留等形式騙取國家補助和村集體資產。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反腐敗工作,將反腐倡廉作為戰略任務來抓,以持之以恒的毅力進行倡廉教育,以零容忍態度開展反腐斗爭。但當前村干部基數大,“微腐敗”案件數量大、形式隱蔽、傳染性強、查處難度大,腐敗和反腐敗的較量還在激烈進行,減少存量、遏制增量的任務依然嚴峻。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村干部“微腐敗”治理是一場持久戰、攻堅戰、保衛戰,堅持一體化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刮骨療毒的勇氣反腐,全面清除啃食群眾利益的“蛀蟲”,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鄉村場域中村干部“微腐敗”行為的內在機理,結合實際分析當前村干部“微腐敗”治理困境,并從思想、法治、監督等維度提出村干部“微腐敗”的治理對策,以期為完善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提供理論參考,為健全村級監督體制機制、改善基層政治生態、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實踐指導。
二、文獻述評
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對“微腐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年內。2014年實施精準扶貧政策后,基層“微腐敗”研究進入高峰期。學者們認為“微腐敗”是由小微權力引發的腐敗行為,具有腐敗金額相對較小、腐敗干部級別較低、腐敗發生范圍較廣等特點。學者們指出基層“微腐敗”的原因不僅在于基層政治領域“圈子文化”、特權思想、資源配置的序差格局,還在于鄉村雙重監督失靈、制度約束乏力、薪酬激勵異化等因素。為有效治理“微腐敗”行為,學者們提出既要保持高壓態勢反腐,強化問責追責、監督巡查、制度確權,又要加強自治、德治和法治的融合,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完善腐敗預警研判機制,著眼于對黨員干部和工作人員廉潔從政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建立重點案件線索建檔和查詢制度;從事前、事中、事后分別構建腐敗治理的預防體系、控制體系、懲治體系;通過治理結構重構和完善技術嵌入基層小微腐敗的治理體系,發揮“互聯網+監督”在基層“微腐敗”治理中的效能;完善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建設,規范村干部權力運行,有效防止權力過度集中。
已有研究成果為豐富“微腐敗”治理理論、健全我國反腐法律制度、提高“微腐敗”治理效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多關注基層“微腐敗”行為,對村干部“微腐敗”這一特定主體的腐敗行為關注較少,與我國鄉村村干部“微腐敗”治理的現實需要不相符,因此,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村干部“微腐敗”的內在邏輯及治理對策,為治理村干部“微腐敗”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
三、村干部“微腐敗”的形成機理
(一)內部動機:思想蛻化變質
作為基層干部,村干部既是我國鄉村建設的“領頭雁”,也是村民代表和村民自治的“主心骨”,履行管理鄉村公共事務的職責。這一職位雖任務繁重,卻無上光榮,肩負為村民辦實事、為村民謀幸福的重大使命和責任。但一些村干部對這一職位認識不清,意志不堅定,其心理逐漸發生變化,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宗旨意識淡薄,特權意識膨脹,貪占心理嚴重。在這些錯誤觀念的刺激下,部分村干部將公共權力看作個人權力,利用職權謀取個人私利。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探究《中國紀檢監察》雜志公布的腐敗分子的懺悔錄,發現大多數的腐敗分子都是因為內心私欲膨脹,理想信念動搖,致使一步步墜入腐敗深淵。在懺悔錄中,落馬官員反思最多的就是自己內心私欲、貪心、不甘的感覺膨脹,忘記了自己執政為民的初心。可見,腐敗并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腐敗行動的根源在于思想腐敗,放縱內心貪腐之欲瘋長,最終導致腐敗行為滋長蔓延。
(二)外在條件:基層監督不足
基層監督不足是誘發村干部“微腐敗”行為的重要因素,監督防線筑得不牢,進而導致腐敗行為猖獗。從外部監督來看,鄉鎮政府和村委會之間是工作指導關系,部分鄉鎮政府對村干部作風問題不夠重視,對村“兩委”失職失責行為排查不到位、問責積極性不高、監督執紀不嚴。從村級內部監督來看,村級內部監督機構運行亦面臨困境。村務監督委員會具體運作方面制度供給不足,保障機制欠缺、職能范圍模糊、監督程序不規范等現象突出,導致部分村務監督委員會只能發揮簽字認可、列席會議、村務協商等職能,變成協助村“兩委”辦理日常事務的工作機構,甚至被村里“一把手”操控。另外,部分地區鄉村治理依然依賴傳統模式,重人情、輕法治,民主監督基礎薄弱,村民不敢監督、不愿監督、不會監督。部分鄉村宗法觀念、特權思想、官本位風氣濃厚,少數村干部團體甚至在村內形成“政治寡頭”。部分村民出于害怕威脅和報復的心理,不敢舉報或監督村干部腐敗行為。綜上,基層監督機制多頭監督、各自為戰、能力較弱,監督時隱時現,無法形成村干部“微腐敗”治理長效機制,導致村干部“微腐敗”問題反彈回潮、固態萌發,陷入“整治—反彈—再整治—再反彈”的惡性循環之中。
四、村干部“微腐敗”治理困境
(一)防腐拒變的思想堤壩不牢固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部分村干部思想意識的松懈和不健康的心理因素是腐敗行為產生的心理誘因。作為農村各項工作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村干部應堅守政治立場,堅持公正廉明的治理理念和工作作風。尤其是在鄉村熟人社會中,鄉村公共事務牽涉廣大村民的利益,更需要村干部從鄉村公共利益和大局出發,經受住現實的考驗,不向公共資產伸手。但仍有一些村干部政治素養和黨性修養不足,政治信念不夠堅定,將村民委托的公共權力當作自己的權力,家長制作風嚴重,在村內重大事項上大搞“一言堂”,肆意利用手中權力為個人謀私,最終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要筑牢防腐、反腐、拒腐的思想堤壩,加強村干部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引導村干部樹立廉政辦事、依法行政、為民服務的工作理念,不斷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養和理論素養,堅定信念之光,補牢精神之鈣,筑牢信仰之基。
(二)鄉村社會的法治底色不夠亮
由于文化知識水平有限,大多數村民法律意識較為淡薄,不了解“微腐敗”行為邊界,也不清楚腐敗的危害。一些村民將村干部腐敗行為默許為“合法合規”的行為,對村干部貪占行為習以為常,并且認同其腐敗無傷大雅。但從長遠來看,村干部腐敗行為腐蝕了黨的執政根基,嚴重破壞了我國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建設的成效。另外,村干部的法律知識素養也有待提高。學者王悅對云南省14292個村(社區)黨組織書記文化程度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專科以上學歷占28.74%,高中、中專占33.64%,初中以下占37.89%。當前村干部隊伍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著年齡結構不當、文化素質結構不合理、法律知識掌握不夠全面等問題。一些村干部處理村級事務更多依靠傳統經驗,缺乏新時代領導干部應當具備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導致一些村干部在征地拆遷、土地糾紛、惠農項目等工作中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處置,違反法律法規現象時有發生。
(三)村級民主監督制度機制“棚架化”
所謂“棚架”現象,主要指對決策、制度、法令的執行只停留在表面,或者在執行中走樣變形,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村級民主監督制度機制“棚架化”表現為程序形式化、手段軟化、成果簡單化等,監督機制運作空轉。依據憲法規定,我國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作為村民擁有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但在一些鄉村中,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召開次數很少,村民極少能通過村民大會參與村級事務,村民對村務信息了解甚少,村級民主參與逐漸成為“紙上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監督也為村干部“一言堂”“拍腦袋決策”等行為所代替。另外,一些鄉村村務監督委員會形同虛設,甚至淪為村“兩委”的附庸。在法律意義上,村務監督委員會具有監督村“兩委”的法定職責,村務監督委員會和村“兩委”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但實際運行中,一些村務監督委員會只能發揮村級重大決策參與的功能,變成鄉村公共事務的參與者,村務監督變成例行“舉手表態”和簽字蓋章;而村“兩委”從被監督的身份變成對村務監督委員會參與的村務工作實施領導監督,導致村務監督委員會處于被動監督的困境。
(四)“不敢腐”的制度藩籬未扎緊
從我國現有反腐敗法律來看,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但有關小微權力腐敗的制度規范還有待完善。第一,當前我國村干部“微腐敗”治理的規則、程序、適用范圍有待補充。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對政務處分做出了原則性規定,但是具體的使用規則、程序等均未作出規定。《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暫行規定》雖規定懲處條例,但也只是作為政務處分規定一種過渡狀態,法律效力不強。與前兩者類似,《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村干部的職責和義務,也未提到村干部腐敗問題。第二,村干部“微腐敗”懲處規定仍需不斷更新。由于村干部“微腐敗”行為大多為“小微小腐”,懲處多為黨紀處分,懲處相對較輕,而且因一些村干部不是黨員,更易逃脫黨紀處分,違法成本較低,間接導致村干部“微腐敗”行為屢禁不止。此外,我國尚未建立一部專門的反腐敗法規,對腐敗干部的懲處主要依據是黨紀、監察法等,反腐敗法律體系不完善,制度漏洞尚未補齊,有待建立更加系統化、完備化、成熟化的反腐敗法律體系。
五、村干部“微腐敗”的治理對策
(一)夯實清正廉潔的思想之基
一些村干部之所以濫用公共權力,除外在環境影響之外,本質上是根植于內心的貪欲作祟,思想變質引發行動腐化。因此,治理村干部“微腐敗”治理必須加強思想反腐,堅定村干部為群眾服務的理想信念,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堤壩,強化防腐拒變的精神支柱。首先,要加強對村干部的黨性教育和廉政教育,通過理論培訓、警示教育、業務培訓等活動,將黨的使命和宗旨植入每一位村干部內心,培養一支講政治、有能力、敢擔當、信念強的新時代鄉村好干部隊伍。堅定村干部內心的共產主義信念,提高村干部政治站位,增強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義利觀,以政治自覺和思想自覺引導行動自覺。其次,要增強村干部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將基層監督視為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主動接受監督,這既是一種胸懷,也是一種自信”。村干部應主動接受監督,時刻敬畏人民、敬畏權力、敬畏法紀。最后,村干部要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提高自身道德修養和文化知識水平,堅決不搞特權,增強自身責任感、光榮感和使命感,多為人民做實事、辦好事。
(二)塑造鄉村“崇法善治”的法治之魂
不斷提高村民和村干部的法治素養,有助于塑造鄉村知法、守法、用法的文明新風尚,鞏固村干部“微腐敗”治理的法治防線。首先,縣級和鄉鎮政府應定期組織開展下鄉普法活動,普及反腐法律法規,讓村民了解哪些行為屬于“微腐敗”行為、如何監督舉報“微腐敗”行為,讓村民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厚植法治文化土壤,凝聚村民法治反腐的強大共識。其次,要持續深入推進“一村一法律顧問”工作,為村民提供免費法律顧問服務,逐漸培養村民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行為,增強村民對法治建設的信心,逐漸消除鄉村人情社會沒有好處不辦事的壞風氣,打通法治社會建設的“最后一公里”。最后,法治意識是現代鄉村帶頭人的必備素養,必須增強村干部法律素養,加強村干部法律知識培訓,引導村干部自覺守法用法,將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到鄉村工作各領域全過程。
(三)織密村干部“微腐敗”的監督之網
立足當前基層監督實際,必須解決群眾監督力量薄弱、同級監督乏力、外部監督難以到位等問題,織密監督之網,匯聚監督合力,實現全過程、全方位、全領域的監督。首先,完善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中“問政”和“質詢”環節,經常舉行線上或線下問政活動,拓寬村民民主監督渠道,改變以往“干部講群眾聽”的單向交流模式,形成村干部和群眾面對面交流、協商、質詢的融洽氛圍。其次,切實發揮村務監督委員會的鄉村“紀委”功能,保障村務監督委員會規范化運作。在法律上規定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權職,對村務監督委員會的監督程序、隸屬關系、工作內容、機構設置等內容作出詳細規定,保持村務監督委員會獨立行使監督權,保障監督公正有力。再次,建立協商、聯動監督、線索移送等制度,加強村務監督委員會與其他監督主體(紀檢監察等)之間的有效銜接和協同合作,增強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權威性。最后,加大縣級巡查組對村級組織的巡察力度,推動構建“縣—鄉—村”聯動巡查格局,充分發揮政治巡查的利劍和震懾作用。此外,還要強化村務監督人才隊伍建設。在人員選拔和培養上,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原則,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選舉,避免村務監督委員會與村“兩委”人員交叉任職現象,同時加強監督人員的專業技能、職業道德、法律知識的培訓,提升村務監督委員會的監督能力。
(四)筑牢鄉村反腐的制度之本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從我國反腐進程來看,當前村干部“微腐敗”治理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而且從各國腐敗治理經驗來看,世界上很多清廉指數排名靠前的國家,無一例外都制定了嚴格的反腐敗法律法規,如新加坡的《防治貪污賄賂法》《沒收貪污賄賂利益法》等。因此,我國村干部“微腐敗”治理要有長遠眼光,堅持依法治理,借鑒古今中外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的有益做法,健全反腐敗法律法規,提高村干部腐敗成本,扎緊防治腐敗的制度籠子,讓反腐敗法律制度剛性運行。一是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整合現有的反腐敗法律規定,健全反腐敗單行法律和配套法規,不斷更新反腐敗的法規范圍和懲罰措施,將腐敗程度分為幾個等級,根據官員腐敗等級作出明確的處罰規定,包括刑事處罰、行政處罰和經濟處罰。二是完善行政問責制度和辦法,明確規定村干部的問責主體、程序、權責標準等,確保權責匹配,推動行政問責法制化、制度化和標準化,切實加大對村干部的監督問責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