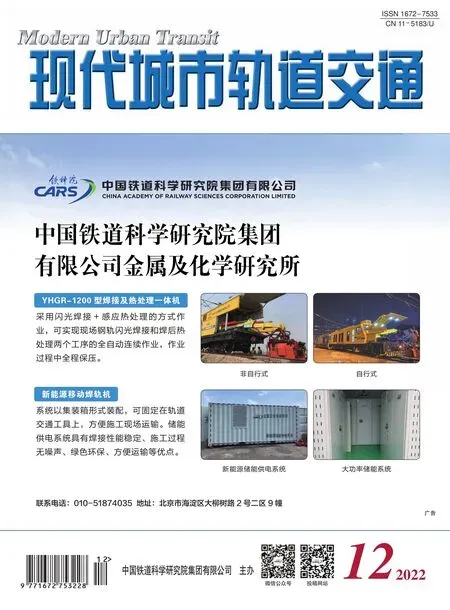大斷面暗挖隧道下穿地鐵既有線結構監測分析
陳 聰,胡曉龍,周興林
(廣東省重工建筑設計院有限公司,廣東廣州 510700)
1 引言
近年來,我國地鐵行業發展迅猛。在一線城市,由于地鐵建設規模龐大,一定范圍的城市地下空間原地鐵線網較密集,在新建地鐵期間往往存在區間隧道穿越既有運營線隧道的情況。為減少新建地鐵隧道下穿對既有隧道結構的影響,國內外眾多學者基于工程實踐開展研究[1-9],并積累大量的成功經驗。然而,由于地鐵區間隧道穿越地段地質條件的復雜多樣性及既有隧道結構本身使用功能上的特殊性,當新建隧道下穿既有線時仍需要結合穿越地段的工程地質條件以及既有隧道結構的使用特征、服役狀況以及周圍工程環境而開展專門的研究[10-12]。本文結合廣州地鐵18號線番禺廣場ü南村萬博站區間下穿既有7號線的工程實例,對大斷面暗挖下穿運營線路既有隧道結構監測數據進行分析,以便為類似地層條件下大斷面暗挖下穿既有線施工和地層沉降控制提供借鑒。
2 工程概況
廣州地鐵18號線番禺廣場ü南村萬博區間(以下簡稱番ü南區間或區間”)暗挖段起訖里程YDK43+455.000~YDK43+763.100,長度308.1 m,其中左線下穿既有7號線盾構區間,右線下穿7號線明挖段。18號線左線下穿段斷面高度13.7 m,跨度15.6 m,覆土厚度26.2 m,與7號線的垂直凈距為5.1 m。右線下穿段斷面高度11.6 m,跨度12 m,覆土厚度27.1 m,與7號線的垂直凈距為4.5 m,18號線與7號線位置關系見圖1、圖2。

圖118 號線與7號線平面位置關系圖

圖218 號線下穿7號線三維示意圖
番ü南區間礦山法隧道覆土主要地層有:人工填土層(1-1)、砂質黏性土(5Z-2)、全風化混合花崗巖(6Z)、強風化混合花崗巖(7Z)。左線開挖面地層主要為強風化混合花崗巖(7Z),開挖面下方局部存在微風化混合花崗巖(9Z)。右線開挖面中上部主要為全風化混合花崗巖(6Z),下部主要為中風化混合花崗巖 (8Z)。
3 工程設計
18號線番ü南區間礦山法隧道根據限界要求及場地圍巖等級共分為A/B/C/D,4類形式,均為大斷面暗挖隧道,其中左線D斷面跨度15.6 m,高度13.75 m,面 積 184 m2,初 支 厚 度350 mm,二襯厚度700 mm,采用雙層φ159大管棚+雙側壁導坑法施工,并輔以二重管無收縮雙液WSS注漿加固,斷面設計見圖3。

圖3 左線暗挖D斷面設計圖(單位:mm)
4 監測方案
為準確監測18號線大斷面暗挖下穿期間既有運營7號線隧道結構的變形,本工程對暗挖施工影響范圍內的7號線DK11+885~DK12+170里程隧道結構三維變形進行全站儀自動化監測,7號線左、右線采用雙站聯測,共布設27個監測斷面,正下穿段為10~18斷面。考慮到本工程地質條件復雜、工程風險大,額外增設靜力水準自動化沉降監測,監測布點見圖4。同時,為研究18號線暗挖施工對既有隧道橢圓度的影響,本工程采取隧道三維激光掃描監測手段。
5 隧道結構監測分析
5.1 隧道沉降分析

圖47 號線隧道自動化監測布點圖(單位:m)
18號 線 暗 挖 下 穿 時 間 段 為2020年7月21日—2020年11月7日,圖5、圖6分別為7號線左線隧道10~14監測斷面道床點累計沉降曲線及靜力水準點累計沉降曲線圖。由圖可知,整個暗挖下穿期間各道床點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沉;下穿時段的曲線斜率最大,下沉速率顯著大于下穿前及二襯施工階段。主要原因為大斷面暗挖施工期間土方開挖卸荷對上部7號線擾動嚴重,導致7號線隧道結構顯著下沉。隨著土方開挖的結束,初支的逐步閉合,進入二襯施工階段,釋放的圍巖應力一部分由初支承擔,沉降速率減緩。故暗挖施工階段及時跟進初支尤為重要,可有效減緩圍巖變形,進而控制既有線隧道變形。

圖5 左線10~14斷面道床點累計沉降曲線

圖6 左線10~14斷面靜力水準點累計沉降曲線
7號線左線13~15斷面道床點沉降速率曲線圖如圖7所示。2020年10月7日至10月21日期間,7號線左線下沉速率均超過1 mm/天,該時段在整個暗挖下穿期間7號線沉降速率最大。由于該時段7號線正下方左、右線隧道同步開挖活動對7號線隧道下部土體擾動最為嚴重,7號線隧道結構沉降變形速率明顯增大;其中,左線進行上導洞上臺階開挖,右線進行左右導洞上臺階開挖。10月21日,18號線左線全部貫通初支閉合后,一個工作面開挖停止后,7號線受擾動程度明顯減小,沉降速率也日趨減小。因此,下穿既有線施工過程中應盡可能避免2條隧道同步開挖的情況,相鄰導洞或并行隧道應嚴格控制施工步距,以減小開挖過程對上方土體的擾動。

圖7 左線13~15斷面道床點沉降速率曲線
7號線右線8~22斷面道床點累計沉降曲線如圖8所示。18號線開挖卸荷導致7號線右線形成以15斷面為中心的沉降槽,由于15斷面位于18號線左、右線中心上方位置,受左右線開挖施工擾動疊加效應影響最為顯著。其中,Y15-1累計沉降值最大達到-87.39 mm。隨著監測斷面逐漸遠離15斷面,擾動效應逐漸減小,隧道結構的沉降變形也逐漸減小。可見在隧道兩平行相鄰隧道的中心線位置上方既有建(構)筑物、管線、地表的沉降應作為施工控制及監測關注的重點。
5.2 隧道橢圓度分析
在施工擾動等偏壓荷載作用下,隧道結構會發生一定的橢變,橢圓度過大時通常都會伴有管片掉塊、裂縫、滲漏水等現象。因此,地鐵隧道的橢圓度檢測對運營維護具有重要意義[13-16]。本工程采用移動式三維激光移動小車對7號線施工影響段進行掃描。受18號線開挖施工影響,7號線既有隧道結構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橢變。經過統計,橢圓度值大于6的環數占比36.95%,其中最大橢圓度達到18.57‰,位于右線第1 160環位置,該位置對應沉降槽中心位置15斷面;同時,該斷面Y15-1監測點為全站儀自動化監測累計沉降最大點,橢圓度與沉降最大值位置一致。

圖87 號線右線8~22斷面道床點累計沉降曲線
由圖9的7號線右線1 160環沉降與橢圓度對比情況可知,10月17日至12月15日期間,隨著18號線暗挖施工的進行,7號線既有隧道結構沉降逐步增大,由-63.58 mm發展至-86.42 mm,增加了35.92%;在此期間,橢圓度亦隨之增加,由14.58逐步增加至18.57‰,增加了27.36%。可見暗挖施工擾動在導致既有線沉降的同時會加劇隧道的橢變,且沉降變形越大,橢變越嚴重。

圖97 號線右線1 160環沉降與橢圓度對比圖
根據如圖10所示的7號線右線第1 160環斷面變形位置及變形量情況,發現第1 160環橢變主要表現管片結構豎向扁平,橫向突出,豎向直徑小于橫向直徑,呈橫鴨蛋形狀[15],主要原因為7號線下方18號線暗挖隧道土體開挖引起隧道豎直方向的偏壓,管片結構往中間擠壓導致橢變,嚴重的橢變有可能影響隧道的運營限界。因此,在大斷面暗挖下穿既有線工程中,除應關注隧道結構沉降變形外,隧道橢圓度也應是監測的重點。

圖10 右線1 160環斷面變形量圖(單位:m)
6 結論
(1)大斷面暗挖下穿期間,既有線隧道結構均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沉降。下穿期沉降速率最大,隨著初支的逐步閉合,沉降速率減緩。故暗挖施工及時跟進初支尤為重要,可有效減緩圍巖變形,從而減小對既有線的擾動。
(2)整個下穿期間,左右隧道同步開挖對既有線隧道下部土體擾動最為嚴重,沉降速率最大。因此,暗挖過程中相鄰導洞或并行隧道應嚴格控制施工步距,以減小對上方土體的開挖擾動,施工過程應盡可能避免既有線下2條隧道的同步開挖。
(3)暗挖下穿段,開挖卸荷導致既有線左、右線均形成以15斷面為中心的沉降槽,受左、右線開挖施工擾動疊加效應影響最為顯著。因此,施工控制及監測應重點關注在隧道兩平行相鄰隧道的中心線位置上方既有建(構)筑物、管線、地表的沉降。
(4)暗挖施工擾動會導致上方既有線隧道結構產生一定程度的橢變,隧道沉降變形越大,橢變越嚴重,管片結構橢變主要表現為豎向扁平、橫向突出,呈橫鴨蛋形狀。
7 展望
本工程暗挖下穿既有7號線過程中,既有線累計沉降值一直是各參建單位關注的重點,最終沉降值直接影響既有線運營安全及后期隧道永久修復方案的制定。本次監測僅對已產生的隧道變形進行監測,未對最終沉降值進行數據預測。后期進行類似重大風險工程時,可結合有限元分析軟件進行物理場分析,通過與已有實測數據進行對比,反演出該工程項目巖土層參數,通過反演出的巖土體參數對計算模型進行修正,從而實現對工程完工后最終沉降值相對精準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