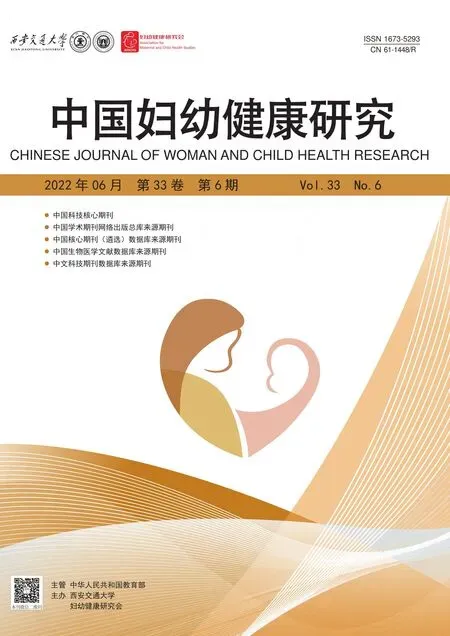川崎病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王琛玥,焦富勇,馮建英
(陜西省川崎病診療中心 陜西省人民醫院兒童病院 西安交通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兒科,陜西 西安 710068)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又被稱為皮膚黏膜淋巴結綜合征,是由日本醫生川崎富作(Dr.Tomisaku Kawasaki)于1967年首次報道,主要的臨床表現為超過5天的持續性發熱、黏膜改變、皮疹、頸部淋巴結非化膿性腫大、雙側球結膜充血、手足硬性水腫及指趾末端脫皮等[1]。KD主要發生在5歲以下兒童,且具有較明顯的性別及地域差異,男性多于女性,亞裔兒童發病率高于歐洲和北美國家[1]。日本針對全國川崎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2015—2016年5歲以下兒童川崎病的發病率為(309.0~330.2)/10萬[2];韓國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5歲以下兒童川崎病的發病率為194.7/10萬[3]。我國尚未發現較新的、全國范圍內的發病率數據,北京市調查結果顯示2000—2004年5歲以下兒童川崎病的發病率為(40.9~55.1)/10萬,上海市2008—2012年5歲以下兒童川崎病的發病率為(30.3~71.9)/10萬[4]。KD主要的病理改變是非特異性血管炎,累及全身中小血管,尤以冠狀動脈為主。KD目前的標準治療方案為丙種球蛋白聯合阿司匹林,雖然可以降低冠狀動脈瘤的發生率,但仍存在冠狀動脈損傷(coronary arteries abnormalities,CAAs)[5]。
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發現,KD發病與外源性感染、遺傳易感性及免疫反應顯著相關。流行病學和臨床報告表明,KD可由鏈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支原體、衣原體、麻疹病毒、博卡病毒、鼻病毒、輪狀病毒、腺病毒、細小病毒B19、真菌等誘發[6]。KD的易感性與遺傳因素密切相關。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在基因遺傳、環境因素相互影響疾病中的作用已被廣泛探索[7]。Waddington于1942年首先提出表觀遺傳學的概念,它是研究基因型如何產生表型的過程,是在不改變基因序列的前提下,通過DNA和組蛋白化學修飾、RNA干擾、染色質重塑等多種機制影響和調節基因的功能及相關特性,決定基因的表達方式,并可以通過細胞分裂和增殖周期進行遺傳[8]。目前國內外針對表觀遺傳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表達變化的調控機制方面。有學者表明,表觀遺傳調控及功能障礙在生理疾病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其在風濕免疫疾病、腫瘤、心血管病等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中作用顯著[9-12]。近年來,有學者對參與KD發病機制的基因表觀遺傳調控進行了相關研究,表觀遺傳修飾可以通過幾種方式發生,包括胞嘧啶的共價修飾(如DNA甲基轉移酶的甲基化)、組蛋白的轉錄后修飾(如乙酰化、磷酸化、甲基化、瓜氨酸化、泛素化、核糖化和亞基化)及基于RNA的轉錄機制的調節[13]。本文重點闡述KD相關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而為KD的發病機制、早期識別、生物標志物、新型治療等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1 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表觀遺傳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早發現的、目前最典型的表觀遺傳學修飾,其在維持細胞生理結構功能、遺傳因子和相關疾病發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KD中研究最廣泛的表觀遺傳學修飾。DNA甲基化是由一組DNA甲基轉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s)和其他輔助蛋白來調控,是在DNMTs的作用下,以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methionine,SAM)作為甲基供體,與胞嘧啶的C5位結合形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lCytosine,5mC)的化學修飾過程[13]。這種修飾反應主要發生在胞嘧啶-鳥嘌呤二核苷酸(Cytidine-phosphatte-Guanonine oligodeoxynucleotides,CpG)位點上。管家基因的啟動子、部分外顯子及內含子富含CpG的區域,被稱為CpG島。在全基因組中,CpG島通常位于基因的啟動子區域[14]。甲基與基因組的CpG島的共價結合可以在不改變基因序列基礎上調節基因的表達,從而影響蛋白質的表達。DNMTs家族系包括DNMT1、DNMT3A、DNMT3B、DNMT3L、DNMT3L-AS1,DNMT1不僅能維持DNA甲基化水平,而且對T淋巴細胞分化的表達起重要作用,DNMT3A和DNMT3B主要功能為起始甲基化[15],其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在免疫性疾病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人類基因組中,甲基化的基因通常與轉錄活躍的基因相關,啟動子區域中CpG島的超甲基化可通過募集轉錄阻遏物或掩蓋轉錄激活因子的結合而導致長期穩定的基因抑制[16]。在全基因組或單個基因水平方面,DNA甲基化的動態變化對于正常發育和疾病中的細胞分化作用至關重要。
Huang等[17]對KD的基因組DNA甲基化和基因表達進行了分析,發現KD患者的DNMT1和DNMT3A的表達水平明顯低于正常對照組,短暫的DNA甲基化過程發生在KD的急性階段。Li等[18]對KD患者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給藥前后DNA甲基化的變化進行了研究,證明用IVIg治療主要通過減少甲基化CpG標記物來改變DNA甲基化,抑制免疫炎癥反應。Chen等[19]發現KD患者與正常對照組二者的CpG區域甲基化具有明顯差異,不同的甲基化區域包含了參與炎癥反應、先天免疫和趨化因子信號途徑的基因。在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s)、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TLRs)、NOD樣受體(NOD-likereceptors,NLRs)、IgG的Fc組分低親和性IIa受體(Fc fragment of IgG,low affinity IIa receptor,FCGR2A)等基因中可以觀察到KD相關的表觀遺傳改變,為KD的病理生理學提供了新的依據。
TLRs不僅能激活人體天然免疫系統而且能調節獲得性免疫反應,與免疫性疾病及炎性疾病密切相關。TLRs廣泛識別細菌(脂多糖)和病毒(dsDNA/RNA、ssDNA/RNA)上所存在的特征模式分子,通過激活蛋白激酶(如IRAK1/4、TBK和IKKi等)介導炎癥反應和細胞因子的生物合成。除KD急性期的TLR3和TLR7外,KD患者TLRs的mRNA表達都有所升高。然而,與正常對照組相比,KD患者急性期TLR1、2、4、6、8、9上的甲基化模式分子表達水平較低。在IVIg治療后,此差異更顯著[20]。已有研究證明,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TLR2和TLR4可以調節KD小鼠模型中的IL-2、IL-6、IL-10、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干擾素-β(interferon-beta,INF-β)的表達,這一觀察結果提供了KD是由細菌感染觸發的相關證據[21]。
在KD急性期,巨噬細胞從M1到M2的活化已有所研究。近年來,使用基因芯片陣列對急性KD患者的轉錄組進行分析,除了與M2巨噬細胞相關的標記物外,TLR2和IL2RA(M1巨噬細胞)的表達有所升高(例如MS4A4A、MS4A6A、TLR1、TLR8、TLR5、CD36、CCR2和ARG1)。這些基因的啟動子區域處于低甲基化狀態。對KD患者進行的IVIg治療通過豐富低甲基化狀態,進一步增強了這些基因的表達模式。中性粒細胞激活異常也與KD有關。在KD患者中觀察到具有異常甲基化模式的中性粒細胞激活標記CD177表達增強。與IVIg敏感KD患者組的CD177水平相比,IVIg耐藥KD患者組的CD177水平相對較高[22]。
免疫細胞中的Fc受體[免疫受體酪氨酸基激活基序(immunoreceptor tyrosine-based activation motif,ITAM)相關受體家族]可與抗體或抗原抗體復合物結合,幫助調理吞噬、脫粒和細胞因子生物合成[23]。近年來,研究發現Fc受體的表達水平及其功能的改變與風濕免疫疾病發生有關[24]。全基因組關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已證實FCGR2A基因是KD的易感性基因。FCGR2A主要編碼在激活的免疫細胞中廣泛表達的免疫球蛋白IgG(Fc區域受體II-a)受體。研究表明,該基因的甲基化水平會影響IgG2與其受體的結合。一項最新的GWAS研究發現,與對照組相比,KD患者的FCGR2A基因具有15.54%低甲基化模式的表觀遺傳調控。與IVIg敏感的KD患者相比,IVIg耐藥患者的低甲基化水平也顯著較高[25]。
2 microRNA
microRNAs(miRNAs)是內源性,單鏈非編碼小RNAs(長約18~25個核苷酸),在控制mRNA翻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非編碼的RNA被轉錄但不轉化為蛋白質,而是作為一種表觀遺傳機制來調控基因表達。它們可以調節轉錄后的基因表達,具有抑制靶mRNA轉錄、翻譯或者能夠剪切靶mRNA并促進其降解的功能[26]。多數miRNA具有高度保守性、時序性和組織特異性。miRNA的表達受表觀遺傳機制控制,其本身也控制著表觀遺傳機制,組成一個“表觀遺傳學-miRNA調控回路”,其調控環節的異常與多種疾病相關[27]。
miRNA具有獨特的表達模式,因此被用作疾病診斷的新型非侵入性生物標志物[28]。有報道稱miRNAs可在外周血中被釋放,這些miRNA與某些特定的病理生理狀態相關。因此,外周血清miRNA被廣泛用作各種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性生物標記物。據報道,異常的miRNAs表達與免疫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炎癥和腫瘤密切相關,在KD的發病機制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KD的急性期,miR-143、miR-199b-5p、miR-618、miR-223和miR-145的表達明顯較高[29]。另一項研究表明,在KD患者中,血清miR-200c和miR-371-5p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這些miRNAs可能在KD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可作為KD的潛在生物標志物[30]。已有學者研究了血清miRNA,如miR-1246、miR-4436b-5p、miR-197-3p和miR-671-5p在KD中作為生物標記物的作用[31]。Zhang等[32]對102例KD患者進行研究,血清中miR-200c和miR-371-5p在KD急性期顯著升高;在IVIg耐藥的KD患者中,其水平也較高;研究還表明,經過治療后,其水平較前下降。在一項研究中顯示,血漿miR-328、miR-575、miR-134和miR-671-5p已被證明是診斷KD和通過影響炎癥基因表達來預測IVIg治療結果的潛在生物標志物。Wang等[33]研究顯示在KD中,hsa-let-7b-5p和hsa-miR-223-3p略有下調,而miR-200c、miR-197-3p和miR-671-5p水平有所上調。Li等[34]研究表明,與健康對照組相比,KD患者的血漿中的18個miRNA表達具有差異;miR-125a-5p在KD患者血漿中顯著增加,其通過調節靶基因MKK7誘導血管內皮細胞凋亡,在KD的發病機制中發揮作用。
3 長鏈非編碼RNA
長鏈非編碼RNAs(lncRNAs)是長度大于200個核苷酸的非編碼RNA分子,通過調節基因轉錄參與細胞內多種過程的調控。在人類基因組中已經發現了超過27 000個lncRNAs,有新研究證明它們的功能與人類疾病的發展具有密切相關性[35]。Ko等[36]研究了37例KD患者lncRNA表達的變化,結果顯示,XLOC_006277的轉錄在IVIg敏感的KD患者中,急性期表現過高,IVIg治療后下降;在之后發展為CAAs的KD患者中也發現了更高水平的XLOC_006277轉錄。
研究發現lncRNA可以通過增加促炎細胞因子及其他炎癥靶基因的轉錄或增強炎癥信號來加強炎癥反應。THRIL(TNF-和hnRNPL相關的免疫調節性lncRNA)是TLR2激活后誘導的許多lncRNA之一。CXCL10是目前已被發現的由THRIL調節的基因之一,在KD患者急性期水平上調,已被證實為KD的生物標志物[37]。在一項17例KD患者的研究中發現,在KD急性期,當TNF-α水平升高時,linc1992/thirl表達較低,故linc1992/thril被認為可能是KD免疫激活的一種新的生物標志物。
lncRNAs在炎癥反應時被誘導表達,并在炎癥反應過程中調節基因轉錄。目前有關KD與lncRNAs的研究較少,但研究已經表明KD與lncRNAs表達的變化密切相關。在深入了解lncRNAs在KD中的生物學功能和作用方面,仍需更多的研究,以發現更多的生物標志物及探索新的治療方案,
綜上所述,KD作為兒童較為常見的免疫炎癥性疾病,常伴冠狀動脈損害,甚至發生冠狀動脈瘤破裂、心肌梗死及猝死等嚴重并發癥,其影響患兒正常生長發育,并給患兒家庭帶來較沉重的心理和經濟負擔。故減少KD發生、控制其發展尤為重要。KD受遺傳及環境雙重控制,外界環境的變化密切影響著KD的發生發展,故需在表觀遺傳學方面對本病做進一步研究。
目前關于KD中表觀遺傳學的研究及認知處于初步階段,本文闡述了幾種關于KD診斷和疾病預測的新的生物標志物,其中大多數研究是基于有限患者數量的單中心研究,還需更大的樣本量來進行驗證。表觀遺傳學作為基因調控的開關,對表觀遺傳學調控機制進行相關的研究,可以為KD的發病機制、早期識別、生物標志物、新型治療等方面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