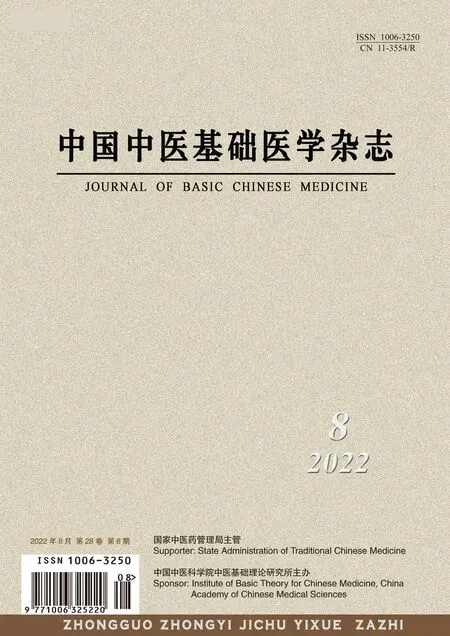基于肝、脾、腎三臟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的臨證思路?
黃念文,王成李,陳小均,張偉濤,王伊光△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泌尿外科,北京 100078)
壓力性尿失禁(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SUI)是指當用力、咳嗽或打噴嚏時有尿液不自主的漏出[1]。我國成年女性SUI患病率高達18.9%[2],現代醫學認為壓力性尿失禁與括約肌張力減弱、尿道過度活動等相關,但具體的發病機制仍不明確[3],目前臨床對于SUI主要采用藥物等保守治療及手術治療,手術治療效果一般優于藥物治療,但是術后出血、排尿功能受阻、感染等風險限制了手術治療的推廣[4,5]。SUI不僅可以導致患者心理障礙,也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經濟負擔。
壓力性尿失禁(SUI)屬于中醫學“遺溺”“小便不禁”“膀胱咳”等范疇[6],多數學者從脾氣下陷、腎氣不固、肺氣虧虛等方面進行辨證治療。王伊光教授在經典方金匱腎氣丸和柴胡疏肝散合方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臨床醫學理論,以健脾益氣、補腎固攝、疏肝解郁三位一體,以經驗方補腎健脾疏肝湯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在臨床上應用多年,取得了一定的療效。
1 治病求因
根據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的臨床表現和癥狀特點,其屬于中醫學“遺溺、小便不禁、膀胱咳”等范疇。《靈樞·九針》曰:“膀胱不約為遺溺,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認為遺溺乃膀胱失約,開闔失常而引起。隋·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記載:“小便不禁者,腎氣虛,下焦受冷也。腎主水,其氣下通于陰。腎虛下焦冷,不能溫制其水液,故小便不禁也”[7],提出了腎氣虧虛、腎陽虛損,進而導致小便不禁。宋·陳自明在《婦人大全良方》亦對本病進行了描述:“又婦人產蓐,產理不順,致傷膀胱,遺尿無時”[8],指出婦人遺尿可由妊娠致傷膀胱引起的。清代醫家尤怡在《金匱翼·小便不禁》指出:“肺脾氣虛,不能約束水道而病不禁者……上虛不能制下者也”[9],肺脾虧虛亦可導致小便不禁。
中醫對于遺溺的認識歷史悠久,《素問·經脈別論篇》中記載:“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合于四時五臟陰陽”,認為小便的生成是依賴膀胱的氣化作用來完成的,體內的津液由脾胃攝入的水谷精微組成,通過肺的宣降和肝的疏泄把水液輸送至全身,下輸于腎,腎將水液分開,清者回于體內,濁者為尿液下注于膀胱,進而排出體外。尿液的生成與排泄與膀胱關系最為密切,同時與腎、脾、肺、肝、心亦有關系。所以,凡能引起體內水液代謝異常的因素可為遺溺發病的因素。病因亦隨著不同時代的醫家對本病的認識不同而各有側重,但萬變不離其宗,總體以臟腑為病、經脈生疾、婦人產傷、誤傷經穴等為主。
2 病機理論
基于歷代先賢著作,長期臨床實踐以及現代醫學觀點,王伊光將本病的相關病機歸納為腎氣不足、脾氣虧虛、肝氣郁結。
2.1 腎氣不足
《素問·上古天真論篇》云:“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腎為先天之本,但腎氣隨年齡的增長進而衰竭,符合現代醫學提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多發于中老年女性患者的觀點[10]。《素問·宣明五氣論篇》曰:“膀胱不約為遺溺,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壓力性尿失禁的病位在于膀胱,而“足少陰腎經屬腎絡膀胱”。腎與膀胱相表里,膀胱為六腑,瀉而不藏,排尿屬于瀉,貯藏尿液則依靠腎氣的藏而不瀉。膀胱的開闔功能有賴于腎氣的推動和固攝,兩者各司其職,膀胱開闔有度,一旦腎氣受損、膀胱開闔失常,則可見小便不禁。故腎氣不足,膀胱失約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發生的機理之一。
2.2 脾氣虧虛
《灸法秘傳》曰:“遺溺者,由于中氣虛衰,不能攝固所致。[11]”脾居于中焦,主升清及運化水液,若脾氣虧虛,清氣不升,氣機升降失調,水液不能正常輸布,機體水液代謝障礙,水濕內聚,流于膀胱,膀胱開闔失約遂見小便頻數或自遺。脾亦為運化腐熟水谷的場所,氣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根本,筋脈皆賴于水谷精微的濡養。清·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遺尿》言:“脾虛則不能為氣化之主,故溺不禁也。[12]”若脾氣虧虛,水谷運化乏源,機體氣血不足,則肌肉失于濡養,甚至萎弱不用,故而膀胱失約,小便不禁。現代臨床醫學認識到,女性壓力性尿失禁可能與膀胱括約肌張力減弱等相關[13],故脾氣虧虛、運化失常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發病的機理之一。
2.3 肝氣郁結
足厥陰肝經過陰器故而遺溺的發生與肝經生理狀態是否正常具有緊密聯系,正如《靈樞·經脈》所曰:“肝所生病為遺溺。蓋因二經循陰器,系廷孔,病則榮衛不至,氣血勞劣,莫能約束水道之竅,故遺失不禁”,肝經生病可發為遺溺。現代臨床醫學研究表明,由于壓力尿失禁具有病因復雜、病情漫長且治愈率低等特點[14],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患者的日常活動及社交生活,從而導致患者常伴有焦慮、抑郁、恐懼、緊張、悲觀等情緒改變[15]。患者長期情緒低落致肝氣郁結,肝主疏泄,調暢全身氣機,氣能運化津液,推動水液運行,三焦通利;若肝氣郁結導致肝失疏泄,推動無力,水液輸布排泄障礙遂見小便不禁。肝主疏泄亦主藏血,產婦由于分娩次數多,產后津血耗損的程度更大,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高發人群[16],故肝氣郁結、肝失疏泄亦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發病的機理之一。
腎為先天之本,腎的氣化功能正常固攝有權,膀胱開闔正常,則小便正常。若腎氣不足,如先天稟賦不足、后天失養、年老體弱、妊娠、外傷等引起腎氣虛損,固攝無權,遂見小便不禁。脾主肌肉,若脾氣虧虛,肌肉失于濡養,膀胱功能失調亦可見小便不禁。此外,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患者除下尿路癥狀以外,大多還伴有不同程度情緒上的改變,致使肝氣郁結,所以王伊光認為腎氣不足、脾氣虧虛及肝氣郁結皆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的基本病機。
3 臨證思路
3.1 明晰辨證思路
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王伊光注意到多數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患者多為經陰道分娩者,陰道分娩可能導致微循環缺血以及骨盆底肌肉、恥骨上韌帶和神經組織的過度伸展,進而導致SUI的發生[17]。《胎產新書》云;“產后氣血虛脫,溝瀆決裂,潴蓄不固,水泉不止,故數而不禁耳。[18]”肝主藏血,產時失血過多,氣隨血耗損傷肝臟。肝腎同源,朱丹溪在《格致余論》中記載:“司疏泄者,肝也,主閉藏者,腎也。[19]”女性壓力性尿失禁多見于中老年女性,因隨著年齡增長,腎氣逐漸虧損。腎為主水之臟,膀胱為蓄水之腑,兩者又互為表里。腎氣充足、固攝有權,膀胱氣化得宜,開闔有度,小便正常。腎為先天之根,脾為后天之本,腎病及脾,中醫認為脾主肌肉,為氣血生化之源,筋脈皆賴于氣血的濡養,而現代臨床醫學認識到壓力性尿失禁的小便失禁、小便頻數等臨床癥狀,可能與膀胱括約肌張力減弱等相關[13]。
3.2 法隨證立
臨床上本病患者常伴有腰膝酸軟、小便頻數、體倦乏力等腎氣不足的表現,亦可有小腹墜脹、大便溏泄等脾氣下陷癥狀,同時大多數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焦慮、抑郁、恐懼、緊張、悲觀等情緒改變。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是一種慢性虛損性疾病且反復發作,由于病程較長,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導致患者情緒低落。情志與臟腑功能息息相關,《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中云:“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中醫對于情志的調節多從肝入手[20]。故而疏肝解郁法在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過程占有重要地位,恢復肝的疏泄功能,其一可促進水液代謝,從而改善SUI患者的排尿異常的癥狀;其二可改善患者焦慮、悲觀、抑郁等不健康心理癥狀,提高患者對預后的信心。王伊光認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的病機特點為本虛標實,虛為脾腎兩虛,實則肝氣郁結,故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時不單只補腎或者健脾,而是要補腎、健脾、疏肝三管齊下,方可事半功倍,取得良效。此外,本病屬于慢性病程,治療該疾病需要一定的療程,可輔以盆底肌康復訓練[21],不可操之過急,緩緩而圖之,循序而漸進,方可從量變到質變。
3.3 方從法出
在組方用藥中,王伊光在經典方劑金匱腎氣丸和柴胡疏肝散的基礎上,加健脾之藥加減而構建成經驗方補腎健脾疏肝湯,其藥物組成為黃芪、柴胡、熟地黃、白術、牛膝、川楝子、香附、枳殼、澤瀉、杜仲、桑螵蛸、白芍、桔梗、烏藥、升麻、炙甘草。方中重用黃芪,有健脾補中、升陽舉陷、益衛固表之力,熟地黃填精益髓,滋補肝腎,張元素[22]認為熟地通腎,腎通則氣達膀胱,膀胱得以司其職;柴胡有和表解里、疏肝解郁、升陽舉陷之功,三藥合用共奏補腎健脾疏肝之功,為君藥;白術健脾益氣、燥濕利水,配合君藥黃芪可增強健脾益氣之功;桑螵蛸滋肝補腎、固精止遺,配合君藥熟地黃補腎固澀之力增;升麻性升陽舉陷,加強君藥柴胡升陽舉陷之力,三藥共為臣藥。澤瀉利水滲濕泄熱,白芍柔肝斂陰養血,川楝子、香附、枳殼疏肝行氣,更佐柴胡疏肝之力,烏藥性溫入腎膀胱經,其性溫可反佐柴胡之苦寒;杜仲滋補肝腎,更佐熟地黃補腎之功,七藥共為佐藥;桔梗是為氣分之藥,可協助藥物上入肺經,牛膝引藥下行達于肝腎,炙甘草性平味甘,有調和諸藥之功,三藥共為使藥。
3.4 因證施治,隨證加減
補腎健脾疏肝湯乃王伊光多年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臨床經驗總結出來的經驗方。一是標本同治。女性壓力性尿失禁基本病機屬于本虛標實,本虛即脾腎兩虛,標實則為肝氣郁結。方中運用黃芪、白術、熟地黃、桑螵蛸健脾補腎的同時,亦用柴胡、川楝子疏肝解郁。故在治療脾腎兩虛的同時,亦需治療肝氣郁結,乃為標本同治;二是注重疏肝解郁。方中柴胡、白芍、桔梗、枳殼及香附皆為柴胡疏肝散的組成,具有疏肝行氣解郁之功效;三是攻補兼施。補方之中誠不可專一于補,必于一瀉,若一味補之澀之則有閉門留寇之憂,故補中得有瀉,方中熟地黃、桑螵蛸補腎固攝之功,澤瀉利水滲濕泄熱之功,一補一瀉相得益彰;四是上下同治。方中桔梗為氣分之藥,助藥上入肺經,肺主上通調水道,與牛膝腎經之藥一上一下,肺腎兼顧,固有因咳而遺溺者,得上下同治,其效更佳;五是寒溫并用。方中烏藥性溫可反佐柴胡之苦寒,以暖腎水,助膀胱氣化,固攝有權,所謂調和亦在于此;六是脾腎緩補。補法則分為緩補和峻補,本病屬于慢性病程亦緩而圖之,循序而漸進,因勢而利導,攻伐而有度。故可用補腎健脾疏肝湯作為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的基礎方,臨證應用時,根據患者癥狀不同,靈活化裁,隨證加減。如睡眠多夢、不安者,可加入遠志、茯神、酸棗仁以獲養心安神之功效;若口干咽燥、干咳者,可加入沙參、麥冬、天門冬以達滋陰潤燥之目的;若食欲不振、呃逆者,可加入焦山楂、焦神曲、麥芽以得消食導滯之意;若帶下黃臭、尿道灼熱者可加入知母、白花蛇舌草、黃柏以獲清熱利濕之功效。
4 典型病案
患者吳某,女,40歲,待業,順產有1子1女,月經正常,2019年8月16日初診:主訴尿失禁3年余,加重半年。自訴3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時欲小便癥狀,未給予重視隨后逐漸加重,外出20 min左右必如廁,不敢咳嗽言笑,否則必便溺。曾在當地醫院診斷為“盆底肌松弛癥”“壓力性尿失禁”,建議入院手術治療,但患者拒絕,其中間斷服用中西藥(具體未詳)效果不佳,延醫至今。否認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慢性病史,否認手術史。刻下癥見小便不禁,運動或者咳嗽時癥狀加重,精神焦慮,失眠煩躁,腰膝酸軟,大便溏泄,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弱。中醫診斷遺溺,證屬脾腎兩虛、肝氣郁結,西醫診斷壓力性尿失禁,治療以健脾補腎、疏肝解郁為治療原則,方以經驗方補腎健脾疏肝湯。方藥組成:黃芪30 g,熟地黃20 g,白術20 g,柴胡15 g,川楝子9 g,香附10 g,枳殼12 g,澤瀉10 g,牛膝10 g,杜仲15 g,桑螵蛸15 g,白芍15 g,桔梗10 g,烏藥6 g,升麻15 g,炙甘草1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飯前溫服,同時輔助盆底肌康復訓練治療。
2019年8月30日復診:患者述其乏力緩解,漏尿癥狀較前減輕,偶有失眠。前方既效守方再進。處方:加遠志10 g,茯神10 g,酸棗仁15 g,繼續服用2周,同樣聯合盆底肌康復訓練治療,患者于2019年9月14日再次復診時腰膝酸軟、體倦乏力、大便溏泄及尿失禁的癥狀明顯減輕,同時囑咐患者繼續盆底肌康復訓練療法,放松心情,保持生活愉悅感。
按語:患者主訴尿失禁,運動或者咳嗽時加重,屬于中醫學“遺溺”范疇,證屬脾腎兩虛、肝氣郁結。患者為中年產后女性,產時失血過多,氣隨血耗,導致中氣不足,升舉無力,不能自主控制尿液,故見小便不禁,大便溏泄,體倦乏力。病程日久及脾氣虧虛皆可損傷腎氣,致腎氣不足,腰失濡養,故可見腰膝酸軟。病情漫長,患者情緒低落,導致肝失疏泄,肝氣郁結。
5 結語
王伊光認為,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患者病位雖屬于膀胱,但與脾、腎、肝關系密切。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王伊光將本病的病機歸納為脾腎兩虛,肝氣郁結。法隨證立,方從法出,經驗方補腎健脾疏肝湯就是在經典方金匱腎氣丸和柴胡疏肝散合方的基礎之上針對這一病機而創立的,以補腎固攝、健脾益氣、疏肝解郁治法三位一體,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多年,取得較好的療效,為中醫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提供新的思路,值得進一步觀察與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