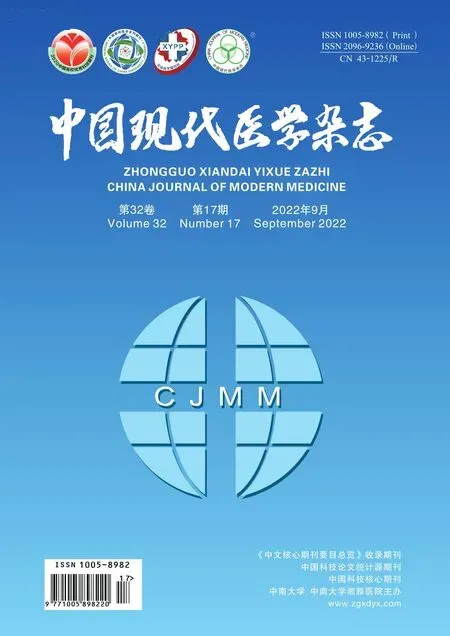鐵死亡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王新羽,張霖柯,符艾青,朱家璇,朱洪
(1.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湖南長沙 410013;2.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國家老年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湖南長沙 410008)
鐵死亡的概念最早在2012年提出[1],這是一種區別于細胞凋亡、壞死和自噬的細胞死亡方式。目前,關于鐵死亡與腫瘤、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缺血再灌注損傷的研究收獲頗豐,但鐵死亡與心血管疾病發病機制相關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本文綜述近年來鐵死亡與心血管疾病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為心血管疾病的診療提供新思路。
1 鐵死亡的概念及其調控機制
鐵死亡最主要的特點是完整的細胞膜脂質過氧化,從而導致致死量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沉積,這一過程是鐵依賴性的,且可被鐵螯合劑抑制[1]。鐵死亡細胞的主要變化有:線粒體外膜的破裂和皺縮、線粒體嵴的減少和消失及線粒體深染,而細胞核未發生明顯的改變[2]。
鐵死亡過程受多種因子調控,如Erastin、p53 等可正性調控鐵死亡,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 GPX4)、核因子紅細胞系2相關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等則為負性調控因子[3]。其中一種主要調控機制為基于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消耗的GPX4失活,導致GPX4 不能催化谷胱甘肽還原酶反應代謝脂質氧化物,進而二價鐵氧化脂質產生ROS,導致細胞的鐵死亡[4]。
2 鐵死亡與心血管疾病
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發現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存在鐵代謝紊亂、脂質過氧化物集聚和ROS 超載等鐵死亡特征,且鐵死亡相關調控因子如Toll 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 4, TLR4)上調[5]:提示調控鐵死亡可以影響心血管疾病進程。本文著重論述鐵死亡在各種常見心血管疾病或相關病理過程,如動脈粥樣硬化、動脈瘤、動脈夾層、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肌病、心臟瓣膜病及其他心血管疾病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及機制。
2.1 鐵死亡與動脈粥樣硬化
動脈粥樣硬化是多種心腦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和病理學基礎。而脂質代謝障礙是其病理變化中的關鍵一環,內皮損傷、氧化應激、炎癥等在其病理發展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異常升高的鐵蛋白水平促進氧化應激,內皮細胞內鐵濃度升高導致還原劑谷胱甘肽的消耗及低密度脂蛋白的形成,進一步促進氧化應激及細胞內脂質過氧化物的積累。此外,鐵超載通過ROS 和環氧合酶通路導致內皮細胞中線粒體損傷,影響巨噬細胞的炎癥表型[6],促進早期動脈粥樣硬化形成。研究[7-8]表明,鐵還通過影響體外和體內的脂質過氧化物(lipid peroxide, LPO)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的發展。過氧化的多不飽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UFA-OOH)是LPO 的主要來源,可能引發內皮ROS 增加、一氧化氮減少、巨噬細胞慢性炎癥和泡沫細胞的形成,并最終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的形成[9]。鐵催化的自由基反應可引起內皮細胞、平滑肌細胞或巨噬細胞中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的氧化,這可能是動脈粥樣硬化性病變形成的危險因素[10]。
BAI 等[11]發現鐵死亡抑制劑鐵抑素-1(Ferrostatin-1, Fer-1)可以緩解載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高脂肪飲食引起的動脈粥樣硬化病變和脂質過氧化。體外研究[11]表明,Fer-1 可以改善LDL 引起的鐵質疏松癥和內皮功能障礙,從而延緩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因此,抑制鐵死亡可能是治療動脈粥樣硬化相關疾病的新策略。此外,YANG 等[12]通過復制人冠狀動脈內皮細胞(human coronary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 HCAEC)的動脈粥樣硬化模型發現戊酰基二磷酸合酶亞基2(prenyl diphosphate synthase subunit 2, PDSS2)過表達激活Nrf2 來抑制HCAECs 的鐵死亡,因此PDSS2 可能在動脈粥樣硬化中起到心臟保護的作用。還有體內實驗[13]證實,內皮祖細胞分泌的細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 secreted by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PC-EVs)轉移microRNA-199a-3p 以抑制特異性蛋白1(specificity protein 1, SP1),從而抑制內皮細胞的鐵死亡并延緩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也有實驗數據[14]表明,丹參酮IIA(Tanshinone IIA, TSA)通過激活HCAECs 中的Nrf2 來抑制鐵死亡。
綜上所述,鐵死亡參與動脈粥樣硬化形成的諸多環節,通過不同路徑抑制血管內皮細胞的鐵死亡可以延緩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
2.2 鐵死亡與動脈瘤及動脈夾層
動脈粥樣硬化是動脈瘤及動脈夾層形成的病因之一,鐵死亡同樣可能參與動脈瘤及動脈夾層形成的過程。實驗發現與吸煙相關的主動脈瘤及主動脈夾層,可能是由于相關煙草提取物(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引起血管平滑肌細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s)鐵死亡引起的,且這一過程可被Fer-1 抑制[15]。這提示鐵死亡可能與主動脈瘤及主動脈夾層患者VSMCs 的功能障礙相關[16]。
2.3 鐵死亡與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是因冠狀動脈狹窄,粥樣硬化性斑塊破裂形成血栓,冠狀動脈完全閉塞,或冠狀動脈痙攣引起心肌持續性缺血缺氧導致心肌壞死。及時的血運重建恢復心肌灌注可逆轉這種損害。心肌梗死后造成的微血管損傷及心肌的再灌注均可造成心肌內出血(intramyocardial hemorrhage, IMH)[17]。臨床通過及時恢復梗死區心肌血液灌注以緩解病情、改善預后,而恢復供血時發生的缺血-再灌注損傷也會進一步損害心肌。心肌細胞壞死是心肌梗死中最不可逆的損害。心肌細胞依賴線粒體有氧呼吸產生三磷酸腺苷作為能量來源。有研究18]也表明線粒體功能障礙是心肌細胞死亡的重要原因。動物實驗證明Liproxstatin-1(LIP-1)作為鐵死亡的特異性抑制劑能夠保持線粒體結構的完整性從而減少心肌壞死[17,19]。
雖然目前心肌梗死后缺血再灌注損傷機制尚不明確,但已有研究[20]證實鐵死亡在心肌梗死后缺血再灌注損傷的再灌注階段起重要作用。ZHAO 等[21]研究發現鐵死亡通過內質網應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ROS 產生、GPX-4 失活和自噬依賴性鐵質途徑調節缺血再灌注損傷。臨床研究[22]表明,心肌梗死患者經皮再灌注治療后梗死區鐵水平升高。同時有研究[22-23]證明,IMH 及心肌鐵殘留是ST 段抬高心肌梗死后左室重構不良的獨立預測因素。
因此,通過鐵螯合劑或其他途徑阻斷鐵死亡以減少缺血再灌注損傷,可對心肌梗死的預后產生積極影響,可防止心力衰竭的發生發展。CHAN 等[24]研究表明,原發性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在再灌注前給予去鐵胺可以迅速改善氧化應激,但不能限制梗死區域大小。PARASKEVAIDIS 等[25]的研究發現靜脈注射去鐵胺可保護心肌免受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手術期間的再灌注損傷和減少脂質過氧化。
GAO 等[26]發現轉鐵蛋白和谷氨酰胺可作為鐵死亡的誘導劑,抑制細胞表面轉鐵蛋白受體及細胞內谷氨酰胺分解代謝途徑可有效減輕小鼠心肌的缺血再灌注損傷。BABA 等[27]研究發現,在小鼠心肌細胞缺血再灌注中發生的鐵死亡可以被雷帕霉素(mTOR)抑制,但其機制尚不清楚,可能與ROS 減少有關。FANG 等[28]的實驗也發現抑制鐵死亡可延緩心肌梗死缺血再灌注模型小鼠的心室重塑,在短期和長期內均可保護心肌細胞,防止心力衰竭發生,這一過程可能與維持線粒體功能有關。
因此,諸多研究均表明心肌梗死后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與鐵死亡的過程有一定的相關性,可通過抑制鐵死亡減輕心肌的缺血再灌注損傷,緩解心肌梗死的進展。
2.4 鐵死亡與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即心臟結構或功能疾病導致的心功能受損,使心排血量無法滿足機體需要,主要表現為體、肺循環充血及組織灌注量不足。引起心力衰竭的常見病因包括高血壓、心肌梗死、心肌病、糖尿病、退行性心瓣膜病、風濕性心臟病等,依據生理功能可將心力衰竭分為舒張性和收縮性兩種。近年來,心力衰竭的病因學、病理生理學、診斷、治療等多方面已取得很大進展,但心力衰竭和鐵死亡關系的研究尚存在諸多未知。
鐵死亡與心力衰竭過程中心室重構有關。在主動脈束帶(aortic banding,AB)誘導心力衰竭的大鼠模型中,大鼠心肌細胞數量減少、有左心室擴大和心臟收縮功能障礙,同時也可觀察到脂質過氧化提示物4-羥基壬烯醛(4-hydroxy-trans-2-nonenal, 4-HNE)表達上調、不穩定鐵池(labile iron pool, LIP)增加,以及鐵死亡關鍵分子GPX4 和鐵死亡重鏈蛋白1(ferritin heavy chain 1,FTH1)表達下調,心肌細胞內存在線粒體收縮、線粒體膜密度增加等鐵死亡相關線粒體特征性結構改變,表明在心力衰竭的過程中可能伴隨著鐵死亡的發生[5,30]。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生物信息學分析也為相關機制的發現提供支持。基于生物信息學分析及大鼠模型實驗,CHEN 等[5]發現,在心力衰竭發生過程中敲低TLR4 或NADPH 氧化酶-4(NADPH oxidase-4, NOX4)均可導致GPX4、FTH1 表達升高,細胞內不穩定鐵減少,脂質過氧化程度降低,左心室重構有所抑制,心室功能改善;同時驗證了TLR4是NOX4 的上游分子,證明了TLR4-NOX4 通路是心力衰竭過程中鐵死亡的相關通路之一。ZHENG等[31]構建circRNA-miRNA-mRNA 調控網絡,即circSnx12 的下游靶點為miR-224-5p,而miR-224-5p可直接調控FTH1 轉錄。FTH1 是鐵蛋白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心力衰竭模型小鼠的心肌細胞中表達降低,導致大量亞鐵離子釋放進入細胞質,可能通過Fenton 反應提高活性氧水平,進而攻擊心肌細胞線粒體細胞膜,導致其功能障礙甚至細胞死亡。ZHENG 等[32]基于生物信息學分析,構建與心力衰竭相關的兩個lncRNA 介導的ceRNA 網絡,并預測網絡中GAS5/miR-18b-5p/PLIN2、GAS5/miR-185-5p/LPCAT3 和GAS5/miR-29b-3p/STAT3 通路可能與鐵死亡有關,但3 個通路與鐵死亡是否直接相關仍需進一步驗證。在慢性心力衰竭的進程中,混合譜系激酶3(mixed lineage kinase 3, MLK3)可以控制JNK/p53 通路介導的氧化應激導致鐵死亡,最終造成心肌纖維化[33],但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
一些已知藥物的作用途徑也可能與抑制鐵死亡的相關過程有關。LIU 等[30]在誘導心力衰竭的細胞和模型小鼠中應用葛根素后發現,鐵超載和脂質過氧化物積累均減少,認為葛根素的抗心力衰竭作用可能通過抗鐵死亡作用實現。他汀類藥物亦可通過抑制鐵死亡發揮心肌保護作用[34]。針對糖尿病小鼠射血分數保留的心力衰竭模型,KITAKATA 等[35]發現伊麥格雷明可恢復心臟代謝應激小鼠受損的未折疊蛋白反應及GPX4 的表達,抑制鐵死亡和射血分數保留的心力衰竭發生。
由此可見,細胞及動物實驗證明了鐵死亡通過減少細胞數量及心肌細胞纖維化等方式參與了心力衰竭的發生、發展,針對鐵死亡的調控可能為心力衰竭的干預和治療提供潛在可能。
2.5 鐵死亡與心肌病
心肌病是由多種病因引起的心肌病變導致心肌出現的心肌機械和/或心肌電活動障礙的一組異質性疾病,可分為遺傳性心肌病、獲得性心肌病和混合性心肌病。但以下所論述的心肌病并不包括由冠心病、心臟瓣膜病等其他心血管疾病所繼發的心肌病理改變。
鐵超載可導致早期的限制型心肌病和晚期擴張型心肌病[36]。鐵蛋白H(Ferritin H, Fth)缺乏小鼠的心肌細胞鐵死亡調節因子Slc7a11 降低,高鐵飲食時可出現鐵代謝紊亂,導致肥厚型心肌病[37]。ZHANG等[38]則發現鐵死亡抑制劑xCT 可保護心肌細胞,xCT基因敲除的小鼠可發生鐵死亡導致的心肌肥大從而引起肥厚型心肌病。鐵死亡抑制劑Fer-1 可減輕上述兩個過程導致的心肌細胞肥大。此外,鐵死亡可能參與了藥物導致心肌病的過程。化療藥物多柔比星(Doxorubicin, DOX)可誘發心肌病,該過程與鐵死亡相關。TADOKORO 等[39]在DOX 誘導的心肌病小鼠及DOX 體外培養的心肌細胞中均發現了GPX4 的下調,并表明線粒體中DOX-Fe2+復合物誘導的脂質過氧化導致了線粒體依賴的鐵死亡,提出DOX 心臟毒性的主要原因是導致了線粒體依賴的鐵死亡。E3 泛素連接酶MITOL/MARCH5 對線粒體的正常功能維持起重要作用,研究表明[40]MITOL/MARCH5 可通過調節GSH 的穩態,降低心肌細胞對DOX 的易感性,抑制DOX 相關的心肌病發生。通過投射電子顯微鏡,LIU等[41]證實了DOX 相關性心肌病中鐵死亡的發生,并發現酰基輔酶A 硫酯酶1(Acot1)是該過程中抑制鐵死亡發生的關鍵基因。FANG 等[28]還通過DNA 測序發現心肌細胞鐵代謝的調控與Nrf2/Hmox1 通路相關,并證明線粒體靶向抗氧化劑MitoTEMPO 可顯著抑制DOX 相關心肌病的發生。ZHANG 等[42]則發現地塞米松通過調節高遷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發揮DOX 誘導心肌病大鼠鐵死亡的保護作用。另外,DOX 處理可導致甲基轉移酶METTL14 表達下調,通過METTL14/KCNQ1OT1/miR-7-5p 軸調控DOX 相關心肌病中的鐵死亡[40]。
以上實驗都從不同的方面表明,心肌細胞鐵死亡參與了限制型心肌病、擴張型心肌病、藥物性心肌病等病理過程。通過合理抑制心肌細胞的鐵死亡可以有效延緩心肌病的進程,側面證明了鐵死亡與心肌病的因果關系。
2.6 鐵死亡與心臟瓣膜病
心臟瓣膜是位于心房-心室、心室-大動脈之間的薄片狀結構,表面為內皮細胞,內層為致密的結締組織。盡管心臟瓣膜相關疾病進程中仍缺乏鐵死亡的直接完整證據,但小葉內出血和鐵代謝紊亂、活性氧的產生及鐵死亡相關通路的證據皆提示了鈣化相關的瓣膜退行性病變中可能有鐵死亡的存在。
在主動脈瓣退行性病變中觀察到了小葉內出血(intraleaflet haemorrhage, ILH),且ILH 被認為是導致主動脈瓣退行性狹窄中瓣膜鈣化的獨立危險因素[43]。ILH 和組織間的鐵沉積可以導致瓣膜組織的炎癥反應和細胞的成骨分化,對瓣膜鈣沉積起到促進作用[44]。研究證明來自血紅素的鐵可以通過Fenton 和habe-weiss 反應催化ROS 的生成,從而誘導DNA、蛋白質和脂類的氧化損傷[44]。ROS 的產生和積累在瓣膜鈣化和狹窄進程中起到關鍵作用[45]。
新近研究發現心臟瓣膜鈣化的過程中,鐵死亡過程可能由Nrf2/HO-1 軸調控。Nrf2 參與了多個氧化反應的調節。正常情況下Nrf2 與Keap1 分子結合,通過泛素化途徑降解。氧化還原狀態下Nrf2 穩定性升高,進入細胞核,進而調控相關基因的轉錄[46]。在主動脈瓣鈣化過程中,不穩定狀態的血紅素通過Nrf2 誘導瓣膜間質細胞中HO-1 的轉錄,分解不穩定的血紅素,降低瓣膜細胞的氧化應激水平,從而對瓣膜組織起到保護作用[47]。盡管該通路具體機制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但該結果提示了可能有效干預瓣膜鈣化進程的潛在靶點。此外,在二尖瓣及其他瓣膜疾病,如瓣膜炎癥、心內膜炎、黏液樣退行性二尖瓣病變中也觀察到了小葉內出血的情況[48]。但小葉內出血與心臟瓣膜不同病理變化之間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7 鐵死亡與其他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心肌病、肺動脈高壓等心血管病的發生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鐵死亡有關。高糖水平在糖尿病心肌病的發病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長期高血糖可以誘導心肌細胞ROS 蓄積,凋亡水平的升高和炎癥細胞的趨化,是糖尿病心肌病的主要病理機制[49]。發生在肺血管內皮細胞(pulmonary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 PAEC)的鐵死亡已在野百合堿(Monocrotaline,MCT)誘導的肺動脈高壓大鼠模型中得到證實,鐵死亡的PAEC 通過HMGB1/TLR4 通路介導肺動脈重塑,并激活炎癥小體NLRP3 刺激炎癥因子表達,參與MCT 誘導的肺動脈高壓的進展[50]。
3 小結和展望
鐵死亡是一種特殊的細胞程序性死亡方式,在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心血管疾病的發展過程存在著鐵代謝紊亂、脂質過氧化物集聚、ROS 積累等鐵死亡特征,調控鐵死亡可以影響心血管疾病進程,干預鐵死亡過程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治療的新策略。然而鐵死亡對心血管疾病發展的影響程度仍不明確,具體機制仍不清楚,且在不同的心血管疾病中鐵死亡的作用及機制可能存在差異,這些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