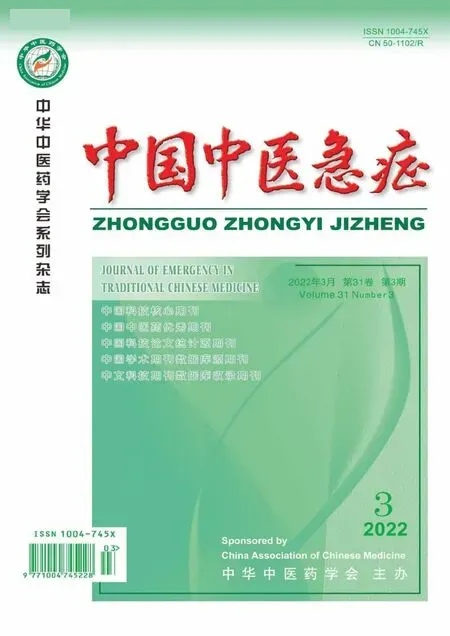從“肺為嬌臟”論膿毒癥肺損傷*
陳 波 林 海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福建 福州 350003)
“肺為嬌臟,最易受邪”,肺葉嬌嫩,百病易傷,而肺氣一傷,百病蜂起。肺在機體氧輸送及器官功能調節中具有重要意義,在膿毒癥中更是核心臟器及窗口臟器。從解剖生理基礎到病理反應特點,從治療時機強度到治療相關再損傷,均體現膿毒癥之“嗜肺性”。“焉有膿毒癥不傷肺”,膿毒癥患者易出現以肺損傷為基礎的多器官功能損害,治療過程中應貫徹以肺保護為核心的全身多器官功能保護,重視肺的前哨作用,從中西醫角度出發,認識膿毒癥肺損傷,有利于更好地治療膿毒癥,以改善膿毒癥患者預后。
1 膿毒癥肺損傷之解剖生理基礎
吳敦序曰“肺葉嬌嫩,通過口鼻直接與外界相通,且外合皮毛,易受邪侵,不耐寒熱,故有‘嬌臟’之稱”[1]。解剖上肺處高位、空虛多腔,上連氣道,開竅于鼻,外通大氣,可直接感受外邪而為病。“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2]。肺臟清潔空虛,依賴呼吸吐納維持機體功能,而邪氣于外,通過呼吸入肺,可直接造成外邪傷肺。肺具有全身最大面積的上皮細胞,巨大的肺泡面積直接與外界相通,各種病原體及致病因素可經呼吸道引起肺損傷。
生理上“肺朝百脈、主治節”,各臟腑通過血脈與肺相連,所以肺在病理上不僅易于感受外邪,他臟邪氣也易傳之于肺。因此有學者提出“五臟的非均衡性”理論[3]。肺具有豐富的血液循環,大量的血管內皮細胞,感染可經血行播散、微循環異常引起肺損傷,除原發于肺部的膿毒癥,其他來源的膿毒癥所產生的炎癥風暴[4]、失調性免疫反應[5]可經血液循環進入肺循環引起肺血管內皮損傷,血管通透性增大,引起滲出性改變。另外肺循環與體循環密切聯系,尤其是心臟,肺循環作為右心的后負荷并承接左心的前負荷,心功能的變化極易導致肺循環的改變,造成肺的氣血交換異常,引起肺損傷。
同時“肺主衛氣,外合皮毛”,肺具有保衛肌表、抗御外邪之作用,邪氣外犯皮毛,可內應于肺,肺失宣肅而為病。肺主司衛氣的生成,并宣發衛氣以溫養皮毛、滋養腠理、開闔汗孔。所以“肺主皮毛而在上,是為嬌臟,形寒飲冷則傷肺”[6]。肺臟為人體之藩籬,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在機體受邪侵擾時最先發病。《大眾醫藥·衛生門》曰“肺居五臟最高之部位,因其高,故曰蓋。因其主氣,為一身之綱領。恰如花開向榮,色澤流霞,輕清之體,華然光采,故曰華蓋”。肺具有良好的屏障功能和代償能力,可作為機體異常反應的代償器官。肺循環是一個低壓力、低阻力、低容量的循環結構,儲備能力強,有利于承接右心壓力及左心容量,在機體應激、容量狀態、血管張力改變時起到良好的調節作用,而在出現失代償時肺循環首當其沖,最早出現變化,亦體現“肺為華蓋,保護他臟”之生理特性。
因肺空虛多腔,外通大氣,易受邪侵,且肺朝百脈、主治節,主司衛氣,職司華蓋。肺具有最大面積的內皮細胞與豐富的血管上皮細胞,并與體循環、心臟產生密切聯系,在膿毒癥中作為機體的第一道門戶,為感受外邪而引起肺損傷奠定了基礎。
2 膿毒癥肺損傷之病理特點
膿毒癥屬于溫病范疇[7]。“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一方面外感溫病早期病位在肺,而肺葉嬌嫩,風寒暑濕痰燥火多種外邪均可能損傷肺部,提示膿毒癥患者常表現為肺損傷,且多種致病因素均可能導致肺損傷。流行病學調查亦顯示肺部感染占膿毒癥首位[8]。《臨證指南醫案·肺痹》亦云“肺為嬌臟,不耐邪侵,凡六淫之氣,一有所著,即能致病”。《難經·七十五難》中言“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肺臟病理特點為正氣易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肺之正氣虧虛則易受多種病因及病理變化的影響。《黃帝內經》曰“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在病因上,肺可因感染、炎癥、休克、液體治療、體位、鎮痛鎮靜、心臟、手術、創傷等多種原因造成損害,表現為肺之疾病易感性。同時膿毒癥肺損傷常表現為ARDS,呼吸窘迫及過強的自主呼吸可導致肺容積傷、壓力傷及生物傷。膿毒癥患者早期易出現急性胃腸損傷,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胃腸功能障礙所導致的營養不良及腸道菌群移位,均可能加重膿毒癥之肺損傷。反之,治療膿毒癥肺損傷,可通過通腑驅邪達到宣通肺氣之效。
宋代張杲在《醫說·喘嗽》中最早提出“肺為嬌臟”,其指出“古人言肺病難愈而喜卒死者,肺為嬌臟,怕寒而惡熱,故邪氣易傷而難治”。病理上他臟邪氣易傳之于肺。全身臟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聯系密切,他臟受邪易于損傷肺臟。基于心肺交互,心肺在氧輸送中密切配合以維持人體生理功能。而在膿毒癥早期,心臟代償性增強,右心動力的增加,可持續對肺循環進行沖刷,引起肺毛細血管內皮損傷及滲漏。反之,膿毒癥可抑制心肌,心肌收縮力的下降導致肺循環瘀血,特別是左右心功能不匹配時,左心無法承接右心高輸出量狀態,使肺循環容量及壓力增加,加重肺部滲出性改變。
肺臟生理特點決定其疾病發生時易受邪侵擾,病理上肺葉嬌嫩,正氣虧虛,邪氣易傷。同時五臟六腑密切聯系,肺為華蓋,而最易受邪。膿毒癥作為致命性的器官功能衰竭,其多種病因均可能引起肺損傷,特別是循環系統的改變,導致膿毒癥傷心而傷肺。
3 膿毒癥肺損傷之治療與再損傷
程鐘齡在《醫學心悟·咳嗽》中言“且肺為嬌臟,攻擊之劑,既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故臨床肺病治療當取“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為法則,用藥以輕、清、宣、散為貴,肺非喜潤惡燥[9],過寒過熱過潤過燥之劑皆所不宜。
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言“肺為嬌臟,且屬金,最畏火刑”“冷熱皆足以傷之也”。肺葉嬌嫩,攻擊之劑不任受,過之則傷。強調肺葉嬌嫩,不耐侵擾,治療稍有偏頗便可致病。在膿毒癥治療中,強調治療時間性及精準性,早期準確及時的液體治療改善膿毒癥患者預后,而大量液體復蘇極易導致血管內皮糖萼受損,加之盲目的液體復蘇可能引起肺循環壓力增加,誘發肺損傷。而在膿毒癥肺損傷治療中,良好的鎮痛鎮靜有利于實施肺保護,減少自主呼吸驅動及呼吸機相關性肺損傷,反之,呼吸機使用不當及過度鎮痛鎮靜均可導致肺損傷及呼吸功能障礙。
“肺為臟腑之華蓋,呼之則虛,吸之則滿。只受得本然之正氣,受不得外來之客氣。客氣干之,則嗆而咳矣。亦只受得臟腑之清氣,受不得臟腑之病氣。病氣干之,亦嗆而咳矣”[2]。肺臟潔凈空虛,不耐邪侵,肺具有完整的解剖屏障與良好的免疫功能,而膿毒癥患者出現低氧血癥時常需建立人工氣道,這便為病原體的入侵引起肺損傷提供了天然腔道。
肺抵抗力弱,不耐邪侵,各種病邪及外來干預均可損傷肺的功能而發生疾病。“肺為嬌臟,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爍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津液;太泄,則汗出而陽虛;太澀,則氣閉而郁結”[10]。藥物太寒、太熱、太潤、太燥、太泄、太澀皆可能損傷肺,故治療應明辨陰陽寒熱虛實,以平為期。在膿毒癥治療中,液體、組織灌注、機械通氣、體位治療均可能引起肺繼發性損傷。在治療監測中,肺水(包括重癥肺部超聲評估肺水含量、分布及有創血流動力學評估血管外肺水)是觀察膿毒癥的窗口,重癥患者持續體位制動,導致肺滲出呈重力依賴性改變,動態評估肺水的同時應重視體位治療。同時膿毒癥疾病微循環異質性、高/低灌注、高血管活性藥、高CVP、過高的非攜帶氧液體、血管屏障破壞的液體過負荷等因素均可能影響肺的微循環而引起肺損傷。因此,在膿毒癥治療中應密切關注“肺為嬌臟”之前哨作用,并準確評估患者的血流動力學及器官功能狀態,做到有的放矢,避免治療相關再損傷。
“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膿毒癥治療應貫徹目標與目的、連續與動態、治療與再損傷等治療理念,在治療過程中應精準目標,及時有效的液體復蘇,準確評估容量狀態及容量反應性,及時足量合理地使用抗生素,正確使用血管活性藥物,避免單一血管活性藥物的過度使用,有利于實現治療最大化,減少治療相關再損傷。同時在中醫“整體觀念”及“辨證論治”指導下進行治療,樹立“即病防傳”理念,重視膿毒癥治療過程中肺保護的核心作用。
4 驗案舉隅
患者,男性,55歲,2020年11月7日初診,因“畏冷、發熱3 d”就診于急診科。患者3 d前出現畏冷、發熱(體溫未監測),自行服用“感冒藥”未見明顯緩解,后發熱持續,伴氣促,于筆者所在醫院急診,測體溫39 ℃,血壓89/54 mmHg(1 mmHg≈0.133 kPa),心率121次/min,呼吸 29次/min,氧飽和度 85%,查血常規WBC16×109/L,GR#89%,CRP>200 mg/L;降鈣素原>100 μg/L;血氣分析 pH 7.317、PCO226.6 mmHg、PO243 mmHg、HCO3-13.6 mmol/L;乳酸8.38 mmol/L。腹部CT示肝區存在混雜密度占位(肝膿腫可能),急診遂予穿刺引流、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抗感染、液體復蘇,考慮病情危重收入ICU。入ICU癥見:高熱,呼吸急促,腹脹,少神,撬舌見舌暗紅、苔黃膩,脈弦數。入院中醫診斷:肝癰病(陽明熱盛證);西醫診斷:1)肝膿腫、感染性休克;2)ARDS。治療予液體復蘇,去甲腎上腺素升壓,美羅培南聯合左氧氟沙星抗感染,瑞芬太尼鎮痛,丙泊酚鎮靜,維持水/電解質平衡、營養支持等治療。中醫治以通腑瀉肺、清熱解毒,予宣白承氣湯合仙方活命飲加減:生石膏30 g,生大黃9 g(后下),金銀花12 g,梔子9 g,杏仁6 g,瓜蔞皮9 g,白芷6 g,防風9 g,天花粉9 g,貝母12 g,蘆根12 g,赤芍9 g,當歸9 g,桃仁9 g。每日1劑,早晚2次,濃煎100 mL。綜合治療3 d后,患者熱退,氣促較前緩解,血壓較前改善,動態評估患者容量狀態維持液體負平衡,監測肺水含量,并逐漸下調鎮痛鎮靜藥物劑量,盡可能保留自主呼吸,但患者表現為氣短,倦怠,舌淡暗、苔薄黃,脈細沉,表現為邪去正傷,肺氣受損、宗氣虧虛之象,治以補肺氣、益宗氣,予補中益氣湯加減:黃芪60 g,人參9 g(另煎),川芎9 g,桔梗9 g,仙鶴草12 g,柴胡9 g,白術12 g,陳皮6 g,當歸6 g,紫菀9 g。每日1劑,早晚2次,濃煎100 mL,配合早期康復,呼吸鍛煉,患者呼吸循環穩定,神志清楚,脫機拔管轉至消化科進一步治療。
按:本例患者急性起病,畏冷、高熱,迅速進展為氣喘、腹脹、少神。肺為嬌臟,溫邪上受,首易犯肺,患者病情初起便可見氣喘、氣促,綜合舌脈,以陽明熱盛、火毒凝結為主,陽明溫病,胃腸肝膽熱邪壅滯,腹部脹滿,腑氣不通,致肺失宣肅,喘促不寧,治以通腑瀉肺、清熱解毒。方用宣白承氣湯合仙方活命飲加減,方中生石膏清泄肺熱,生大黃通腑瀉熱,金銀花、梔子清熱解毒療瘡共為君藥。臣以杏仁宣肺止咳,瓜蔞皮潤肺化痰。赤芍、當歸、桃仁行氣活血,白芷、防風通滯散結,貝母、蘆根、花粉清熱化痰散結,均為佐藥。肺與大腸相表里,病理上陽明經證易出現肺臟病變,經宣白承氣湯通腑瀉肺,仙方活命飲清熱解毒,陽明熱邪得解,嬌肺之氣機得以宣通。西醫上采取肺保護通氣,動態評估液體量及肺水含量,重視膿毒癥患者之肺保護,終使患者病情得到階段緩解。但患者仍有氣短、倦怠等,結合患者早期陽明腑實、邪熱壅盛,采用苦寒攻邪之劑易傷肺氣,同時西醫抗生素、鎮痛鎮靜藥物均可損傷人體正氣,故后期治以補肺氣、益宗氣,采用補中益氣湯加減,方中重用黃芪、人參補肺氣、益宗氣為君藥,臣以柴胡、桔梗舉陷升提,川芎、當歸行氣活血,仙鶴草益氣補虛,紫菀宣肺化痰,佐以白術、陳皮健脾益氣,開宗氣生成之源,最終患者肺氣得益、宗氣得復,病情得以最終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