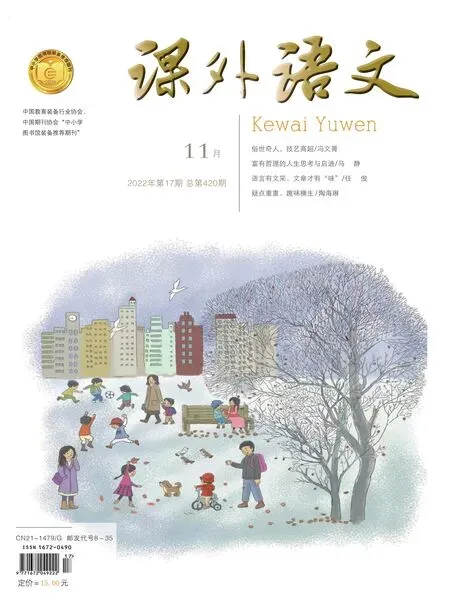一曲哀詞摧肺肝
——蘇軾悼亡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賞析
⊙王明玫(甘肅省景泰縣第六中學)


★悼亡詩是我國古代詩歌常見題材,最早可追溯到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魏晉時期著名詩人潘安創作的《悼亡詩三首》將悼亡詩推到了新的境界。也就是從那時起,悼亡詩逐漸成為悼念亡妻、亡妾的專屬。時至宋代,以詞為盛的文學氛圍使得“悼亡詩”逐漸發展成“悼亡詞”。借助于騰挪跌宕的章法結構以及悲涼哀婉的意境組合,宋代悼亡詞完美抒發了創作者對離世故人的無限懷想之情,《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一、蘇軾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蘇軾是我國北宋時期集大成的文學創作者。他在詩、詞、繪畫、音樂等領域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一生對政治抱有極高的熱情,但不幸的是,雖然他滿腔熱血、滿腹經綸,仕途卻并不順利,常年被貶謫在外。蘇軾以一種豁達寬廣的心態去面對政治道路上的種種得失,并將他的性情、襟懷、人生態度等都融于其藝術作品之中。“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就是其胸襟最好的體現。人們提到蘇軾,總是想到“大江東去”式的豪邁,但其實他也不乏纏綿凄惻之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就為我們展示了其情感細膩的一面,表達了他對亡妻肝腸寸斷、痛徹心扉的相思之情。
本詞創作于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此時蘇軾亡妻王弗已逝世十年。蘇軾與妻子一朝永別后,他十載縈心,積思成夢,心中的悲痛與思念與日俱增,最終創作出有“千古第一悼亡詞”之稱的絕世佳作。與王弗相遇、相知、相戀時,蘇軾年十九,王弗只有十六歲,但她知書達理并且聰明賢惠,對上恭敬,對下慈愛,二人情深恩愛。對蘇軾來說,王弗不僅是生活上的伴侶,更是精神上的知己。可惜造化弄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僅二十七歲的王弗便早早離世,只留給蘇軾一個七歲的孩子。次年蘇軾遵照父訓,將王弗遷葬回其故鄉眉山。在王弗逝世的這十年中,蘇軾的仕途也頗為不順,在朝中深受排擠的他,先是通判杭州,后又至密州。在任密州知州時,蘇軾上書羅列呂惠卿強制推行新法所導致的擾民之罪,但因呂惠卿位高權重,朝廷不僅未阻止新政推行,反倒將王安國、鄭俠等一批反對新政的官員加以懲處。身處密州且深感自危的蘇軾不禁回憶起過去十年“飄然未可期”的種種苦楚,迸發出對亡妻的無比思念之情。他是多么渴望向王弗訴說過去十年的種種不幸,并得到妻子的安慰與疏導。但現實就是如此殘酷,兼為知己和諍友的妻子如今卻在千里之外的“孤墳”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出來的。
二、超乎尋常的感情境界:生者與死者的感情交流
詞共分為上下兩闋,上闋用于表達對亡妻的思念,下闋記錄了蘇軾夢中的場景,用來襯托其對亡妻的哀傷之情。“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開頭便直抒胸臆,感人至深。對于相愛的夫妻來說,一日不見便已如隔三秋。可以想象,在十年的離別時光中作者內心是如何煎熬。“茫茫”二字,形象地傳達了一股苦寂凄清之感,而前面的“兩”字則將本詞升華,使本詞不再是作者對亡妻的單向訴說,而是成了夫妻二人的雙向交流:九泉之下的王弗同樣也在日夜思念著漂泊在外的丈夫。“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其中的“千里”與“十年”相對應,從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表達了作者對妻子的思念。細細品讀,可以發現兩人之間的距離又何止千里,分明是生死之別,作者的痛心與苦楚躍然紙上:夫妻二人是多么渴望有一天可以互訴衷腸,可現實卻是一人在人間,一人在千里之外的孤墳下。蘇軾渴望將心中的苦悶吐露出來,卻發現“無處話凄涼”,孤寂與思念之情更甚。本句也暗示了作者在政治上的悲觀處境,蘊含著自己在這十年間抱負不得實現的失意之感。“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將詞作的情感推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在蘇軾亡妻故去的十年間,蘇軾遭受了親人離去、宦海沉浮等諸多的打擊和摧殘。雖然當時年僅四十歲,但曾經意氣風發的蘇軾已經不在,只留下容顏蒼老、形體衰敗、塵土滿面、兩鬢斑白。即便沖破陰陽界限,夫妻重新相見,恐怕妻子也早已認不出他,還有什么比這更讓人悲傷的嗎?
下闋是蘇軾對正月二十日夜所夢之景的描寫。“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這既是蘇軾夢中所見,也是昔日的真實場景。“小軒窗”與上闋的“孤墳”形成鮮明對比。次句“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是在上句情境下對二人后續動作的描寫。在夢中夫妻二人終于打破時間、空間、生死陰陽的屏障,但相見后二人卻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十年的相思之情最終化為了淚水與對望。久別的夫妻二人重逢后沒有親昵與寒暄,所有的情感均濃縮在淚水之中,營造出“此處無聲勝有聲”的意境,給人以極大沖擊,可謂是整首詞的點睛之處。“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是本詞的最后一句,寫的是夢醒之后的情境。蘇軾不僅僅在繼續隔空懷念早已去世的妻子,而且遙想到千里之外明月夜下的王弗也因時刻想念丈夫而肝腸寸斷。縱觀全詞,夫妻之間的情感交流從未停止。
我們常說,時間是最好的解藥。隨著時間的消逝,對亡故愛人的情感會漸漸淡化趨于平復,可蘇軾對王弗的感情卻不是這樣,縱使已過十年之久,縱使妻子埋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眉山,蘇軾依然持續地感受著她的存在,不肯跨過這道坎,斷了這道念。明明夫妻之間早已陰陽永隔,他偏偏堅信只是千里相隔,會有相逢之日。王弗早已化作一粒塵埃,蘇軾依然在心中掛念、憐惜著妻子。在某種意義上,在這對情深意篤的夫妻中死者反倒是幸運的。死者早已入土為安,生者卻在心中時刻掛念。蘇軾心中妻子鮮活的形象與千里孤墳的現實兩相對比,體現出極強的情感張力,更使人絕望的是,即便真的有朝一日夫妻之間得以再次相見,看到如今失魂落魄、微霜滿鬢的丈夫,王弗怕是早已無法認出。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將蘇軾推向悲劇旋渦之中而無法自拔,也使得這首悼亡詞有了不同于之前所有悼亡詞的超乎尋常的感情境界。它不是蘇軾用筆墨寫成的,而是其真摯濃烈的情思、沉郁心底的傷痛歷經十年凝結而成的。
本詞之中對亡妻的情感之所以能感人肺腑,就在于蘇軾不僅僅是在觸景生情地追憶故人,而是以“懷人”的方式在與妻子不停地展開情感交流。雖然妻子的肉體早已不在,可她依然活在蘇軾的精神世界之中。
三、超越時代的思想境界:對女性人格的尊重
在強調“以夫為綱”的封建社會里,蘇軾并沒有把愛妻王弗視作自己的附庸品,而是把她看作自己精神上的知音。這使得本詞有了超越時代的思想境界,體現了對女性獨立人格的尊重。蘇軾之前的悼亡詩與悼亡詞中,妻子、戀人等更多的是以操勞家務的生活陪伴者形象出現,如潘岳在《悼亡詩》中寫道:“豈曰無重纊(音況),誰與同歲寒”“展轉眄枕席,長簟竟床空”,又如元稹《譴悲懷》寫妻子“顧我無衣搜藎篋,泥地沽酒拔金釵”。這些作品雖寫出了丈夫對妻子的真摯情感,但妻子未能從根本上擺脫陪伴者這一角色。
《江城子》一詞中,妻子王弗是可以與他互訴衷腸的靈魂知己,伴隨著愛妻的去世,蘇軾也就“無處話凄涼”了。在下半闋的夢境幻象之中,蘇軾以欣賞者的視角,看到妻子正在軒窗下梳妝,此時妻子是生活中、詞作中真正的主角,是全詞中的靈魂人物。
借助王弗歸葬于眉山時蘇軾所作的《亡妻王氏墓志銘》中的描寫,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蘇軾與妻子之間的關系。從“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可以看出王弗的智慧與體貼,從“軾有所為于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可以看出妻子謹慎的性格和對蘇軾事業上的關心,在蘇軾與客人交談公務的時候,王弗會“立屏間聽之”,并且會與丈夫交流自己的看法,告訴丈夫何人宜交往,何人應該敬而遠之。這種夫妻關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背景下極難想象。在這些片段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兩人之間平等相知的親密感情。蘇軾對妻子王弗不僅有愛戀之情,對其才華和人品更是傾慕。可是命運卻是如此捉弄人,身為精神知己的妻子卻早早離世。蘇軾自己的仕途之路也屢受打擊,他是多么希望相親相知的妻子能在今天傾聽自己的心聲,給予自己安慰、開導,然而現實卻是自己獨自一人身處“火冷燈稀”的“寂寞山城”密州,妻子則在千里之外的孤墳之中,憶起過往恩愛情深,經十載而積思成夢,遂在夢醒之后創作了這一流芳千古的悼亡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