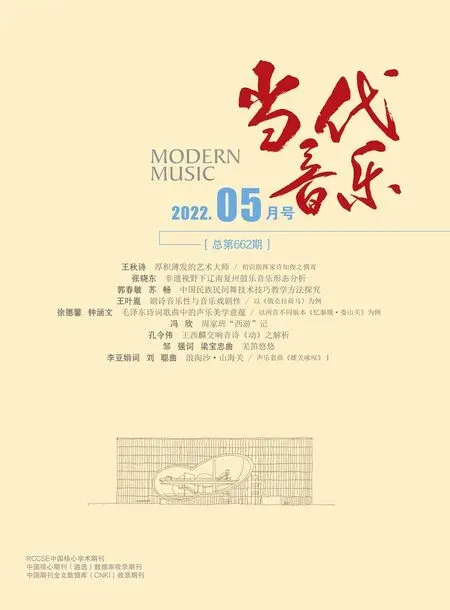論央視春晚舞蹈的創作流變與價值追尋
吳嘉敏
一、時代演進下的創作流變
四十載光陰見證了藝術形式的發展與革新。春晚,承載著一代人的青春記憶,而央視春晚舞蹈節目的更迭則從側面展示了中國舞蹈創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轉變與革新。題材的多元變更、形式的跨界融合、主題的深刻表達……無不體現著中國舞蹈人在藝術之路上的苦心探索。
(一)視點之變:從以“節日”為依據到著眼“現實”百態
春節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除去其可追溯至上古的驅邪攘災、除舊納新的功能之外,春節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則是團圓和睦、熱鬧紅火的喜慶氣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央視春晚舞蹈類節目主要以“節日”作為出發點進行創作,作品的內在邏輯盡可能符合春節這一特殊語境。從1983年首屆央視春晚,趙青、徐川表演的舞蹈作品《節日》開始,民俗節慶、婚慶儀式等活動成為央視春晚舞蹈創作挖掘可舞性的主要起點,如1986年春晚,表現一對新婚夫婦與抬轎夫鬧趣的《雙回門》;1992年春晚,取材于山西晉南地區特有娶親風俗的《踩鼓點》;2005年春晚,將春節熱鬧氣氛“舞蹈化”的《年年有余》等均將作品本身力圖展現的節日氛圍與春節這一傳統節日的特定需求相結合,在熱鬧紅火中慶賀新年。
20世紀90年代后,央視春晚舞蹈創作開始出現以“現實”為起點,探尋舞蹈多元呈現的趨勢。1993年,舞蹈《山妞與模特》刻畫了一位夢想登上大舞臺的山妞與模特同臺的故事,首次將“小人物”的夢想與期盼搬上春晚大舞臺,體現了國家平臺對于普通大眾的深切關懷。2007年由東北師范大學創作表演的舞蹈《進城》運用“虛擬化”的手法,描寫了一群農民工在進城路上的所思所想,他們融入城市的快節奏生活,與各行各業的人共同堅守平凡。2021年登上央視春晚舞臺的舞蹈《朱鹮》更是傳遞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主題,盡顯現實意義。從“節日”到“現實”的視點轉換體現了春晚舞蹈創作逐漸由再現“熱鬧”的表象,走向了彰顯深刻的“關懷”。
(二)手段之變:從“以舞為輔”到“以舞為主”的跨界融合
20世紀80年代初,“春晚”這一形式剛剛進入大眾視野,其節目構成則體現出各藝術門類的相對獨立性:相聲、詩朗誦、音樂等藝術形式各司其職。拋去舞美等因素的合理融入,“跨界”的嘗試大多局限于歌與舞的融合——歌舞。而央視春晚歌舞形式的最早呈現可以追溯至1983年首屆央視春晚。《草原民歌》以“獨舞+獨唱”的形式描繪草原遼闊之景,舞者與歌者在表演中不斷互動,既彌補了獨唱形式由于人數少而難以駕馭整個舞臺的弱點,同時也為舞蹈提供了合理的展開緣由。盡管20世紀80年代初,央視春晚歌舞節目的整體呈現還略顯稚嫩,未融入過多的燈光舞美因素,且“舞”的緣由大多局限于“歌”的可視化再現。然而在隨后多年的創作實踐中,央視春晚歌舞的主要特征逐漸形成—— “以歌為主,以舞為輔”。“伴舞”作為聽覺藝術的可視化呈現,一方面有利于歌曲本身的意境傳遞,另一方面也憑借人數之多而為歌曲提供舞臺張力[1]。而時至今日,盡管歌舞仍然是構成春晚節目的主流形式之一,但相比往日,站在舞蹈藝術的發展視角看,卻出現了復歸舞蹈本體,“以舞為主”的跨界融合趨勢。
“跨界”首先體現在舞蹈與相近藝術形式的相互融合,同以人體為媒介的藝術形式在融合中出新。1990年登上央視春晚的兒童舞蹈《京劇迪斯科》將京劇與舞蹈相融合,可謂率先突破了央視春晚舞蹈類節目以“歌舞”占據主流的局面。2010年,《對弈》將武術與中國古典舞相結合,演員人數配比上男女各占一半,動作風格融剛勁與舒展于一體。除此之外,科技的發展不斷豐富著央視春晚舞蹈的生命力,2009年,多媒體舞蹈《城市變奏曲》憑借立體化呈現、3D效果展示以及高空可移動的舞臺突破傳統舞蹈創作的時空局限,將城市數百年來日新月異的發展濃縮于舞臺之上。與以往央視春晚舞蹈的單一化類型呈現形成鮮明對比,上述節目在類型介紹時一改往日“歌舞”“歌伴舞”的概稱,運用了“武舞”“多媒體舞蹈”等說法,均體現出堅守舞蹈本體的跨界融合趨勢。
(三)中外之變:從立足本土文化到拓寬國際視野
20世紀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的契機下,文藝界開展了一場破冰之旅,舞蹈界刮起一股致敬傳統之風。而春晚舞蹈同樣隨著這股潮流深深扎根于傳統與民族之間,開啟了一段尋古溯雅之路。1985年一段《長袖舞》以變幻莫測的“圓與線”敘說了延續千年的神仙幻想。20世紀90年代,風土人情歌舞成為央視春晚舞蹈創作的主流之一,地域性民族文化獨占鰲頭,由山西省歌舞劇院創作表演的舞蹈作品成曾多次出現在央視春晚舞臺上,《看秧歌》《瞧這些婆姨們》《踩鼓點》都成為地域性文化的經典代表。而無論是“尋古溯雅”或是“扎根鄉土”都反映出春晚舞蹈人對于本土文化的重視。“春節”這一傳統民俗跨越千年歷史,將族群的集體記憶延續至今,成為連接古人與今人的紐帶,而“春晚”作為當代人歡度春節的主流形式又極大豐富著傳統民俗的內涵。站在古今歷史的交匯點,央視春晚舞蹈在創作中立足本土文化乃“題中應有之意”。
包容與博大是中華文明的國之氣度,反對國強必霸、大國必戰的邏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是中華文化歷經千年沉淀秉持的價值取向。回首千年之前的盛唐,中西雜糅共振的交響樂章至今回蕩在耳邊。時空流轉又一次迎來了歷史交匯的高點,開放的心態促使“傳統”向世界張開臂膀,擁抱多元的文化形態。千禧年后,央視春晚舞蹈呈現出拓寬國際視野的趨勢。2004年,愛爾蘭舞之魂舞蹈團所表演的《踢踏風暴》憑借快速有力、豐富多變的下肢動作,以及熱情似火的異國風情將踢踏舞帶入了中國大眾的視野;2009年一部《大河之舞》更是促使踢踏舞邁向國內各大綜藝,風靡一時。時至今日,國際元素與傳統文化相融,使得央視春晚舞蹈展現出全新樣貌。2021年央視春晚,歌舞《節日》融東西方文化精華于一爐,集中國傳統紅綢舞、埃及藤杖舞、俄羅斯民間舞于一身,展現出新時期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而舞蹈也在跨文化的對話與共享中煥發新生。
二、立足傳統的價值追尋
央視春晚作為每年除夕之夜家家戶戶必看的綜合性文藝晚會,自20世紀80年代誕生以來已逐漸與放鞭炮、拜年一同成為當代人慶賀新年的重要“儀式”之一。儀式感與娛樂性是“春節”與“晚會”二者帶來的特殊限定,因此央視春晚的節目呈現既要體現出老少皆宜、寓教于樂的功能屬性,同時也應承擔著宣揚主流思想、家國情懷的重要任務。[2][3]多年以來,央視春晚舞蹈創作在價值取向上堅持立足傳統文化,以此為基礎實現時代的多元演繹,在深扎傳統中喚醒大眾對于祖先文化的集體記憶,在特定文化語境中傳揚真善美。
(一)探索傳統符號的深層意義
皮爾斯的符號理論研究基于人類認知方式將符號分類為像似符號(icon)、指示符號(index)和規約符號(convention),而人類對于“符號”的理解則由表意感知走向經驗理解再到抽象理解[3]。舞蹈作品中豐富的符號文本傳達出了特定語境下的文化內涵,央視春晚舞蹈著眼于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深挖表象背后的深層文化價值,而觀眾則通過對符號的認知從而體會舞蹈作品的深刻意蘊。
在舞蹈發展的萌芽階段,原始人借助對外物模仿而獲得“交感”效應以實現某些功利目的,而其后的發展歷程中,舞巾舞象、舞龍舞獅等形式都極大豐富著舞蹈文本符號的多元呈現。“規約符號”被視作具有社會規約性的最復雜的符號,在特定的社會語境當彰顯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央視春晚舞蹈在歷年創作中順應中國文化背景下傳統符號的指示性,同時賦予傳統文化符號以時代呈現。例如松、竹、梅不僅是自然物象,同時也憑借其在寒冬里的獨特呈現而成為“中國風骨”的象征。2006年春晚,《歲寒三友——松、竹、梅》以中國古典舞、民族民間舞、芭蕾舞為主要手段,構造了松、竹、梅的像似符號,而伴隨作品形神與意象的升華,觀眾的感知過程由經驗理解走向抽象理解。松、竹、梅內在的精神意蘊被觀眾感知,高潔與傲岸,堅韌與傲骨借以符號實現傳達。除此之外《猴嘻》《聞雞起舞》等作品,在特定年份結合傳統生肖文化以及動物本身屬性傳遞出深刻意義。
(二)開掘歷史沉淀的當代表達
歷史與傳統是文化發展之根,如何堅守傳統并賦予其時代活力則考驗著今人智慧。春晚舞蹈是中國舞蹈發展的一面鏡子,觀其30余載的發展與流變,“賦歷史沉淀以時代新生”是央視春晚舞蹈一貫的堅守與追求。
堅守傳統又更新傳統,體現在央視春晚舞蹈的多元形態發展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地域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歌舞是央視春晚舞蹈的主流之一,“喜慶熱鬧造紅火、活潑生動接地氣”成為了這一類型舞蹈作品的重要特征。如前所述,“節日”為春晚舞蹈創作提供了可舞性依據,在“地域風俗”形態的舞蹈節目當中,作品本身的邏輯思考與春節這一特殊背景達成契合。而2000年以后,盡管民族性的彰顯仍是央視春晚舞蹈創作的內在核心追求,但以“靜”為突破點、抽取傳統文化的核心之意這一創作趨向卻逐漸代替過往,成為了春晚舞蹈創作的風向標。以近年央視春晚舞蹈作品為例,2020年的央視春晚舞蹈《漁光曲》聚焦海派風尚,將江南女子的溫婉之美呈現于舞臺之上;2021年登上央視春晚舞臺的《朱鹮》提取朱鹮的典型體態,將“天人和諧、與自然共生”的理念與女性靜謐之美相融[4];同是2021年,《茉莉》又以水墨畫般的質感將東方自然和諧之美呈現于觀眾眼前。上述作品均一反往日對于熱鬧氣氛的強調,轉而憑借“鬧中取靜”的獨特呈現而獲得大眾一致好評,而央視春晚舞蹈創作也借助“著眼文化內核”的形態突破了“再現熱鬧”的窠臼,打破雷同的單一呈現。
(三)延續美好祈愿的功能訴求
春節在中國已有四千余年的歷史,源于上古的原始信仰與祭祀基因至今保留在春節當中。時代的新鮮血液豐富著傳統節日的內涵,并賦予傳統節日以更加多元的整體呈現。然而借節慶之名表達對生活的美好祈愿卻貫穿在春節數千年的發展中。從除舊布新、祈年豐收到祈求學業有成、身體健康。“愿望”的個體表達各不相同,而“祈愿”的功能訴求卻一直是春節的重要標簽[5]。
春節聯歡晚會作為新時代科技力量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不僅借助全新媒介手段實現傳統民俗的時代新生,同時也實現其祈愿訴求的多元表達。20世紀80年代,國家層面的主旋律宣揚,改革開放后大眾對于未來的美好展望成為央視春晚舞蹈的主要“祈愿”,《長袖舞》在致敬古雅當中傳遞對于美好現實的無限遐想、《版納三色》《孔雀》在民族語境中利用傳統文化符號傳遞深刻的生命思考。20世紀90年代以后,家國情懷轉向人文關照,小人物的“愿望”登上了國家主流平臺,當《雙回門》《踩鼓點》《看秧歌》所代表的“俗文化”登上春晚舞臺之時,平凡人不平凡的憧憬成為春晚舞蹈的主旋律之一。21世紀以來,央視春晚舞蹈創作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中華傳統精神的寫意性表達、國家主旋律與主流價值觀的傳揚以及源于平凡百姓生活的“正能量”傳遞共同構成了春晚舞蹈的“大雜燴”。與此同時,央視春晚舞蹈也蘊含著更為豐富的祈愿訴求。2021年登上央視春晚舞臺的歌舞《節日》,描繪了一幅新時期多元文化和諧共生的美好藍圖,正如《節日》所展望的情景一般,新時期的中華文化正以開放包容的心態與異國文化共振時代樂章,而春節這一傳統民俗正凝聚著跨越膚色與國籍的人類共同愿景向前發展。
結 語
自誕生之日起,舞蹈與儀式就有著天然密切的聯系,春節聯歡晚會這一形式是傳統文化與科技交融的產物。舞蹈作為歷年央視春晚節目的重要構成,有著其他藝術形式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在這歡度新年之夜,舞蹈借助全新媒介手段,突破過往即時性的傳播局限,打破時間與空間的束縛走進千家萬戶,并由此實現傳統儀式的跨時代發展。三十八載探索,央視春晚舞蹈在多元文化的滋養下實現了藝術性與功能性的雙重躍升,同時借助主流平臺的傳播力實現了“出圈”。鑒于“央視”與“春晚”二者限定帶來的特殊性,春晚舞蹈創作必須將傳揚主流價值觀與探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作為內在擔當。未來,央視春晚舞蹈創作必將面臨更為復雜的文化環境。而如何在堅守傳統文化內核之上實現舞蹈形式的多元探索、如何在承擔社會責任之上提升舞蹈作品的藝術性等問題仍值得思考。
注釋:
[1]胡 偉.央視春晚舞蹈三十年(1983—2013)演藝形態分析[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01):105—108.
[2]王 琳,田 園.2021年央視春晚:國家美學的符號表達與價值建構[J].當代電視,2021(04):4—7.
[3]衛艷蕾,林 毅.春晚舞蹈中的文化自信與身份認同[J].舞蹈,2021(03):84—86.
[4]唐白晶.文化符號在舞蹈創作中的運用——以“茶馬古道”題材大型舞作為例[J].民族藝術研究,2020(03):94—102.
[5]馮雙白,林 毅.藝術創新的巨大力量——從2021年總臺春晚舞蹈節目的藝術突破說起[J].舞蹈,2021(02):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