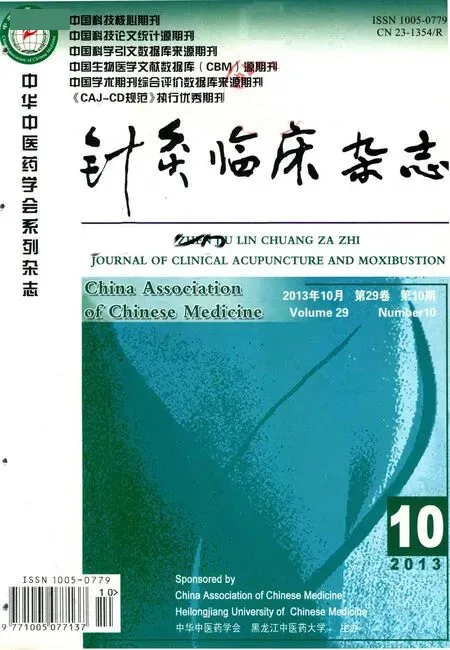調神通絡針法結合頭舌針治療混合性失語體會
潘婕,張連城
(1.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300073;2.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天津300073)
調神通絡針法針對中風病的基本病機,即肝風、痰濁、瘀血等病理因素導致“腦絡瘀阻,神明不調”而提出的治療法則和針刺方法。臨床上治療中風病及各種兼證、后遺癥,均取得了較滿意的療效[1]。在腦血管病變引起的失語中,最常見的是運動性失語,又稱Broca失語,由優勢側半球額下回后部病變引起;其次是感覺性失語又稱Wernicke失語,由優勢側半球顳上回后部的病變引起;兩者結合稱為混合性失語,是最嚴重的一種失語類型。對于本病西醫和傳統的中藥治療效果不明顯,針灸治療本病有一定的療效,筆者隨導師在醫院實習期間見過多例失語病人,運用調神通絡針法配合舌針治療均取得了較好的療效,治愈率高。現介紹如下。
1 針刺治療與操作
1.1 調神通絡針法
頭針選穴:頂中線(百會向前至前頂)、頂斜1線(百會前斜下45°,長1.5 寸)、頂旁線(距頂中線 2.25寸,承靈穴與正營穴連線)、頂斜2線(承靈前外斜下45°,長 1.5 寸)[1]。體針選穴:風池(雙側)患側外關、曲池、臂臑、涌泉、足三里、四強[1]。操作:頭針進針方向自上而下(或外斜下)自后向前(或向外斜前)沿皮刺,頂斜1線、頂斜2線進針方向和頂中線夾角呈60°。采用提插手法,進針時幅度小,行針時提插幅度要大,進針深度均為1.5寸。每穴行針時間30 s,可兩針同時操作。頭皮針應邊行針邊囑患者盡量活動相應部位[1],病灶側及對側頭針可交替使用。體針采用平補平瀉。
1.2 頭針
選穴:頂顳前斜線(MS6)下 2/5(雙側)、顳前線(MS10)(雙側)、頂顳后斜線(MS7)下 2/5(雙側)、顳后線(MS11)(雙側)、額中線(MS1)。操作:患者取坐位,穴位常規消毒后,取0.25 mm×40 mm華佗牌不銹鋼毫針。在針刺頂顳前斜線、頂顳后斜線、顳前線、顳后線時,進針點均為曲鬢、懸厘,針尖向上或斜上,沿著四線方向進針,進針后沿皮刺,進針約1.5寸。針刺額中線時,自下端進針,針尖方向向上,進針1.5寸。采用提插手法,平補平瀉,行針時可兩針同時操作,頭針行針時可鼓勵患者講話,以達到動守神的目的。病灶側及對側頭穴上、下午交替使用。
1.3 舌三針
選穴:第一針為上廉泉,在頜下正中一寸舌骨與下頜緣之間的凹陷中;第二針、第三針分別在上廉泉旁開0.8寸[2]。操作:針刺采用單手快速進針,針尖向舌根方向刺入,呈45°~60°,斜刺入25~30 mm,在得氣的基礎上,行提插捻轉手法20 s,使患者舌根有酸麻脹痛感則可[2]。
1.4 配穴
選穴:若為瘀血導致可以配合金津、玉液。金津、玉液位于口腔內舌系帶兩側靜脈上,左為金津、右為玉液。操作:金津、玉液點刺出血,令患者張口,用消毒棉球將舌體翻卷,暴露部位,向舌根方向快速刺入,以出現酸、麻、脹等感覺,并向喉部放散為佳。獲得針感后,立即起針。如出血量大則用棉球壓迫止血。
2 典型病例
患者,張某,男性,71歲,主訴“雙側肢體無力7天,語蹇1小時”。患者于2012年6月21日無明顯誘因出現雙下肢無力,行走緩慢,摔倒兩次,無頭暈、頭痛,無肢體抽搐,言語流利,進食正常。當時未引起足夠重視,未就診。2012年6月28日患者再次摔倒,頭部未觸地,但于就診8小時前出現言語不利,不能交流,遂就診于我院腦病針灸重癥病房。急查心電圖:基本正常。急查血糖:7.8 mmol/L。查頭CT示:左額頂顳枕梗塞;左基底節梗塞灶及軟化灶;腦萎縮。診斷“急性腦梗死”。入院時患者精神萎靡,呼吸平穩,語言蹇澀,面色無華,右側肢體癱瘓,進食、水不嗆,寐可,二便正常,舌質暗,苔白,脈弦滑。中醫辨證為風痰阻絡,用“調神通絡針法”可以疏通經絡、調理神明。10次為一個療程,經過3個療程后,患者理解能力好轉,能夠簡單理解別人的言語,反應較前敏捷,四肢活動靈活,右側肢體較之前好轉,能夠自行行走,但步態蹣跚。出院后患者于門診繼續針灸治療一個月,隨訪半年患者言語功能大為改善,能完全理解別人的意思,能做簡單應答,行走自如。
3 討論
中風失語癥,又稱“瘖痱”、“風喑”等。多由肝腎不足,陰虛陽亢,風火痰瘀,上擾清竅,導致舌竅失靈,則瘖不能言,或舌強語蹇。故臨床應用“調神通絡針法”結合舌針治療失語,“調神通絡針法”疏通經絡、調理神明。舌針在舌體局部,以活血通絡為治療大法,加金津、玉液點刺放血,使氣血通暢,腦神清明,舌竅開通,則舌體靈活,語言流利。
調神通絡針法結合頭舌針治療失語,從祖國醫學角度思考,“腦為髓海,為元神之府”,主管人的思維、意識、言語等精神活動。頭為諸陽之會,手足陽經循行均與腦相連,另外手足陰經的循行也直接、間接與腦相連。故針刺頭部和體部的穴位,能夠激發經氣,開竅啟閉,促進經氣運行,氣行則神行,神行則腦明。舌三針為靳瑞教授所創,其中1針為上廉泉,為任脈脈氣所發,該穴的深部正當舌體根部,與舌體的運動緊密相關。舌II針和舌III針分別為左右旁廉泉[2],針刺加強了舌體根部刺激,促使語言功能恢復。從現代醫學分析,中風后患者腦組織會出現缺血缺氧,血液粘度高。頭皮針治療的主要依據是大腦不同的功能區在頭皮的投影。針刺頭皮部位相應區域能有效地擴張腦血管、改善微循環、降低血液粘度、疏通腦絡氣血、改善血液流變學,促進患肢及神經功能缺損的恢復[3],配合體針改善患肢功能。舌三針深部有多條神經分布,其中包括舌下神經和下頜舌骨肌神經等,刺激舌體根部的神經能夠反射性地增強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性。反復刺激能夠增加神經纖維的激活數量,形成反射,從而調節語言中樞受損變性的細胞,使患者言語功能得以恢復[2-4]。
另外《針灸大成》指出:“舌強難語:廉泉、金津、玉液。”金津、玉液穴屬經外奇穴,是臟腑氣血交聚相連的樞紐。點刺可以疏通經絡、活血化瘀。故對瘀血所致中風失語效果較好。從解剖學角度考慮,穴位區有神經和血管分布,點刺出血可以刺激神經,改善局部血液循環,促進舌肌運動能力。共奏通經活絡、調暢氣血功能。
故臨床運用調神通絡針法配合頭舌針治療混合性失語癥簡便實用,大大提高了臨床療效,能給患者及其家人減輕痛苦和負擔,適宜在中風失語的治療中推廣應用。
[1]郭家奎,王立存.“調神通絡針法”針灸治療中風病[J].天津中醫學院學報,2000,19(2):21 -22
[2]李湘力,蔡敬宙,江剛輝.舌三針治療中風失語癥30例[J].針灸臨床雜志,2009,25(7):6 -8
[3]王占奎,郭家奎,趙淑華,等.“調神通絡”針法對腦梗死患者臨床療效及血流變影響的研究[J].針灸臨床雜志,2011,27(12):1-2
[4]李湘力,蔡敬宙,江剛輝.舌三針治療中風失語癥30例[J].針灸臨床雜志,2009,25(7):6 -8
[5]江剛輝,李湘力.靳氏舌三針治療中風運動性失語癥療效觀察[J].上海針灸雜志,2008,27(7):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