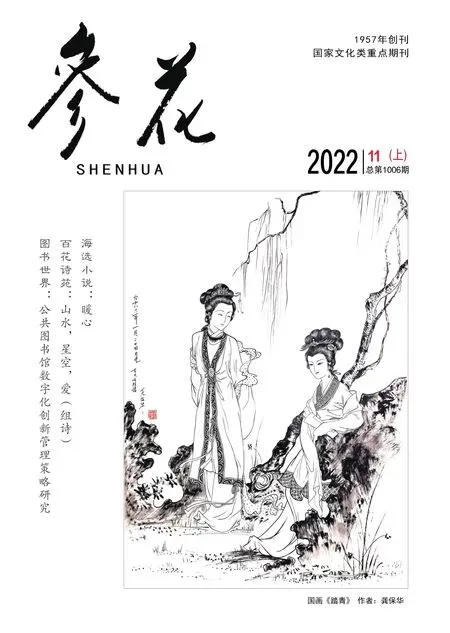植根民族沃土,助力文化傳承
——評李世相《蒙古族風格鋼琴組曲集》
◎石翠花
一、引言
以鋼琴為媒傳承民族音樂,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鋼琴創作的新趨勢,著名作曲家李世相教授立足于蒙古族音樂文化,改編、創作了一部具有蒙古族風格的鋼琴作品——《蒙古族風格鋼琴組曲集》(以下統稱為《組曲集》)。李世相在創作風格上追求純樸與真實感受的表達,民族風格與時代脈搏的相互融合。因此在作品中,他把蒙古族音樂風格作為音樂創作中的母語,并一直努力使之發揚光大。[1]《組曲集》于2001年9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凝聚了作者幾十年來研究蒙古族音樂、研究民族音樂鋼琴創作的心血,同時也展現了作者無論在表現蒙古族文化意蘊,還是在挖掘蒙古族音樂獨特的表達思維方面做出的積極而有成效的探索。《組曲集》的出版發行不論是社會價值還是學術價值都較高,創作中諸多創新與填補空白之處,成為研究民族音樂創作的范例。
二、作品簡介
《蒙古族風格鋼琴組曲集》由10個組曲,共47首小曲構成。10首組曲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直接引用完整的民歌主題曲調改編;另一類是將民間曲調擴展或汲取蒙古族音樂材料獨立創作的樂曲。每首樂曲融會了作者多年創作實踐的經驗,凝聚了作曲家深厚的蒙古族文化底蘊,堪稱曲曲經典。《組曲集》是我國迄今為止較全面、較準確地表現蒙古族音樂風格的鋼琴組曲集。
三、《蒙古族風格鋼琴組曲集》的創作特點
(一)貼切的標題從多角度展現了蒙古族風俗文化
《組曲集》作為傳承蒙古族文化的一部作品集,每首組曲及小曲都冠以濃郁的民族意蘊和地方色彩的標題,貼切的標題多角度地展現了蒙古族民俗文化;豐富的題材拉近了作品與聽眾之間的距離。
組曲二《少年那達慕掠影》中五首樂曲《摔跤手出場了》《飛向目標的箭》《小騎士的風采》《月光下的敖包》《篝火旁的安代》及組曲四《草原風俗場景三則》中三首樂曲《敖包祭祀》《婚禮歌舞》《薩滿之舞》,這些樂曲從標題的確定到題材的選取都蘊含著蒙古族祭祀文化、歌舞文化及草原風情。
“那達慕”是蒙語的音譯,意為“娛樂”或“游戲”,是蒙古族的重要節日。那達慕大會首先要進行大規模的敖包祭祀,敖包祭祀后進行一些蒙古族傳統文體娛樂活動,主要表演男兒的騎馬、射箭、摔跤三大競技運動,[2]通過樂曲《少年那達慕掠影》中“摔跤手出場了”“飛向目標的箭”“小騎士的風采” 的標題,我們能親切地感受到那達慕競技場上蒙古族男兒展示的摔跤、射箭、騎馬三技藝。
蒙古族舞蹈——安代,其最初的祭祀文化因子逐步消失,伴隨著祭祀的歌舞文化被遺留下來,并逐步脫離了母體形式演化為近代蒙古族風俗歌舞形式,“篝火旁的安代”選用了安代的題材,將安代旋律的主題動機進行發展,再現了傍晚人們圍在篝火旁載歌載舞的場景。[3]
蒙古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信仰、審美標準,標題中“那達慕”“薩滿”“敖包”“安代”等,這些名詞不僅僅是一個文字的符號,而是能引起人們詩意聯想的具有民族文化意蘊的代碼,對蒙古族文化起到了傳播的作用。
(二)獨特的民族音樂素材凸顯了蒙古族神韻
蒙古族音樂資源博大精深,以鋼琴為媒來表現蒙古族音樂的作品不少,但將代表蒙古族音樂文化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長調、說唱、安代、馬頭琴用鋼琴這一載體呈現出來,《組曲集》尚屬首例。在感慨這部作品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創作時的諸多創新之處,讓這部作品成為研究民族音樂創作的典范。
1.蒙古族民歌主題的選取,成為民族鋼琴曲創作的重要素材
蒙古族長調是具有蒙古族專業性、代表性的民歌體裁,只存在于蒙古族、用蒙古語演唱,其旋律起伏跌宕、音域寬廣、曲調悠長、高亢、嘹亮,大量使用“諾古拉”“烏日特艾”,節奏自由,腔多字少,獨特的甩腔演唱技巧構成了長調民歌獨特的藝術風格。[4]蒙古族長調具有“曲調性強,節奏性弱”的特點,組曲十《烏力格爾敘事》中《祭奠》的整曲運用了結構自由、內涵豐富的散拍子,靠內在延續不斷的長氣息把握整首樂曲的發展,展現了蒙古族長調旋律的特點——形散而神不散。[5]組曲九《隔不斷的情——思鄉》中的《木色列》,主題來自科爾沁蒙古族長調民歌《木色列》。長調旋律“貌似隨意,實則嚴謹”的結構富有邏輯性,結構內聚力體現在其拖腔的設計中。作曲家充分挖掘鋼琴的表達方式,運用和弦的快速琶音及延長音記號恰當地表現了長調的拖腔技術,保持了原民歌的長調風格;“低密高疏”的旋律形態是作曲家改編長調歌曲時又一表達方式,時值相對少而寬松的拖腔均在旋律的較高音區,而較低音區的音符組合相對密集;[6]“頭重尾輕”的語調化節奏與蒙古族詩歌的韻律相吻合,蒙古語詞匯中,單音節詞匯運用比較普遍,頭部發音較重,所以改編后的鋼琴曲較多地出現與之相適應的節奏形態,如后附點、切分節奏,[7]《隔不斷的情——思鄉》中僅僅旋律部分就有12處運用了后附點、切分的節奏;如《憂愁的諾恩吉雅》,大量的“波音”運用,模仿了蒙古族長調“諾古拉”的演唱方式。
這些長調歌曲的典型特征被作曲家運用到鋼琴曲的創作中,使得聲樂化的演唱形式變為器樂化的陳述方式,充分體現出作曲家對蒙古族長調音樂的通曉,成為民族鋼琴曲創作的重要素材。
2.創意性地將蒙古族說書調搬到鋼琴上來演奏,豐富了鋼琴語匯
蒙古族的說唱藝術具有節奏明快、語言豐富、有說有唱、腔調兼有的特點,在馬頭琴或四胡的伴奏下,配以合轍押韻的詩句,和著優美的曲調,成為蒙古族古老的民族文化藝術珍品。[8]作曲家在創作中,創造性地將蒙古族特有的說書調搬到了鋼琴上來演奏,用鋼琴模仿說書時,節奏形態便自然與語言韻律結合起來,用相對短促的節奏律動,解決語言陳述連貫性的需要。[9]例如,“祖訓”的第二樂段用三連音的節奏,模仿了蒙古族的語言韻律,來表現蒙古族的祝詞調,使蒙古族風格更具直觀性、趣味性。主題來自蒙古族民歌《丁克爾扎布》而改編的樂曲“悲壯”,全曲由兩種音樂材料組成,一種音樂材料是具有長調特點舒展悠長的旋律、疏密相間的節奏、尾音延長的拖腔、快速短小的裝飾音,另一種音樂材料:與蒙古語祝詞相似,模仿了蒙古語言發音的音調,主要強調的是語言節奏韻律上的美感。兩種音樂材料交替進行、形成互補,完成了一部具有濃郁蒙古族風格的鋼琴作品。[10]再如“開篇”6小節引子之后,正曲用十六分音符時值組合構成的旋律,表達著蒙古族的語言形態,生動地刻畫了類似傳統“烏力格爾”中的“開場白”;左手運用小連線奏法模仿四胡的伴奏,形象地再現了烏力格爾藝人在四胡的伴奏下進行著說唱表演。
作曲家成功地將蒙古族說書調運用鋼琴來演奏,將蒙古族語言的韻律運用到鋼琴曲的創作中,豐富了鋼琴語匯。
3.用鋼琴表現蒙古族器樂演奏,豐富了鋼琴的音色變化
蒙古族四胡、三弦、雅托克、馬頭琴是最能體現蒙古民族氣質的樂器,作曲家抓住蒙古族樂器的特點,將其音色及奏法運用鋼琴這一載體模仿得惟妙惟肖。例如,《組曲集》中“篝火旁的安代”,樂曲的第一段由三個聲部組成,高音聲部是安代舞曲典型的旋律;中聲部十六分音符緊拉慢唱的半分解伴奏音型模仿了蒙古族三弦的演奏效果;低聲部的復調旋律則模仿了馬頭琴的音色,達到了立體化的音響效果。《風流的捷哲爾娜娜》,則運用小二度音程模仿了四胡的抹音效果。《多姿的科爾沁姑娘》和《美麗的烏云珊丹》,運用低聲部均勻、跳動的分解和弦伴奏音型模仿了蒙古族彈撥樂器三弦的演奏效果;高潮及結尾部分的華彩樂句模仿了蒙古族樂器雅托克的彈奏效果,具有濃郁的蒙古族韻味。
將這些民族樂器獨特的音色引用到鋼琴曲創作中,既要通曉各種樂器的演奏特點、音色,又要精通鋼琴創作與演奏技能,才能實現用鋼琴演奏來表現民族樂器的音色之美,李世相運用鋼琴的演奏將蒙古族樂器豐富的音色呈現出來,不僅豐富了鋼琴的音色變化,而且推動了鋼琴演奏技術的進步。
(三)中西合璧的作曲技法為民族鋼琴曲創作拓寬了思路
中國鋼琴音樂作為一種獨特的音樂語言,其民族風格體現在多個方面,如旋律、調式、節奏、節拍、曲式、織體、音色,都成為民族風格的載體。
作曲家以蒙古族音樂為母語,擺脫以往民歌加和聲的單一創作技法,獨辟蹊徑地將蒙古族音樂元素成功地運用于傳統的西洋作曲技法中來表現蒙古族音樂風格:多樣化的音樂織體、獨特的和聲語言、靈活的曲式結構都是展現蒙古族多姿多彩音樂風貌的手段。作曲家在挖掘蒙古族音樂素材方面不是僅僅將一段耳熟能詳的民族旋律外殼搬上鋼琴,更重要的是運用五聲性縱化和聲、蒙古族風格音列、完整的主題樂句發展手法等作曲技法來詮釋著蒙古族音樂的內涵,使其成為表現蒙古族風格鋼琴作品的典范。
作曲家在《微風撫動的炊煙》中運用音列或小動機式的寫作手法,由6個32分音符組成的小動機進行小三度模進,同時又采用了具有濃郁蒙古族風格的音列,并以音型作為全曲的結構元素來發展樂思。在和聲上追求色彩的效果、突出特殊的音響,來營造樂曲所需的意境。
《組曲集》的出版發行證實了作者在運用鋼琴這一載體來體現蒙古族音樂風格方面的成功之處。在挖掘蒙古族音樂獨特的表達思維方面所作出的成就,體現出作者對蒙古族音樂的通曉;在民族風格鋼琴作品創作方面所作出的積極而有成效的探索,成為相關愛好者學習民族音樂創作的典范教材。
四、《蒙古族風格鋼琴組曲集》的價值定位
(一)社會價值
音樂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組曲集》素材源于蒙古族音樂,具有傳播蒙古族音樂文化的功能,它承載著蒙古族人民的風俗、信仰、情感,傳播著蒙古族音樂文化精神。《組曲集》的問世是迄今為止運用鋼琴這一載體較為全面地展現蒙古族音樂風貌的一部組曲集,利用鋼琴音色變化豐富、旋律性強、易被人們所喜愛的優點,縮短了創作者與欣賞者在審美心理上的差距,無論在傳播蒙古族音樂文化方面,還是在振興民族音樂方面都有著積極的社會效益。
(二)學術價值
1.為研究民族音樂創作者提供了學習的經驗
作曲家在創作時采用了多樣化的音樂織體、獨特的和聲語言、靈活的曲式結構展現蒙古族多姿多彩的音樂風貌。同時,創作者將蒙古族語言的韻律運用到鋼琴曲的創作中,使蒙古族風格更具直觀性、趣味性;對于代表蒙古族音樂特點的長調音樂,采用了結構自由、散而不碎的拍子來表現蒙古族“曲調性強,節奏性弱”的音樂特點,為民族鋼琴曲創作拓寬了思路;用鋼琴表現蒙古族樂器:四胡、三弦、雅托克、馬頭琴等獨特的音色,不僅豐富了鋼琴的音色變化,而且推動了鋼琴演奏技術的發展。可見,《組曲集》的出版是作曲家將兩類具有明顯差異的音樂文化通過創作技法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實現了音樂內容、民族風格與演奏技巧完美結合,為研究民族鋼琴創作在音樂語言和創作手法上做了有益的嘗試。
2.為編配蒙古族民歌伴奏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組曲集》中,和聲語言的民族化原則和伴奏織體的多樣化傾向成為學習蒙古族民歌伴奏編配的范例。作曲家在和聲技法的運用上突破了大小調式的局限,從民歌自身的旋律與調式中去探索新的和聲語言,在不影響作品五聲性格調的前提下,將傳統和弦增加色彩性附加音或臨時變化音;在和弦結構上突破了常規三度疊置的和弦結構而更多地采用了四五度疊置的和弦;在三和弦的主音下附加一個小三度或附加一個大二度,使音響復雜化,也解決了和聲寫作的民族化問題。如《路邊歡跳的小鹿》中作者采用了B羽的五聲性縱化和弦,用了雅樂中的變徵音。
蒙古族民歌體裁豐富,所用的伴奏樂器也多種多樣,作者借鑒了蒙古族各種樂器的奏法來編配伴奏織體,如《美麗的烏云珊丹》低聲部均勻、跳動的分解和弦伴奏音型模仿了蒙古族彈撥樂器三弦的演奏效果;《微風撫動著炊煙》運用32分音符短小的固定音型作為背景音樂,是通過模仿雅托克的彈奏來襯托旋律的行進,解決了為節奏自由的蒙古族長調歌曲編配鋼琴伴奏的困難。
五、結語
《組曲集》的創作凝聚了創作者多年的心血,不僅體現了創作者堅持不懈、嚴謹治學的態度,同時表現出其廣博的音樂學識和豐富的蒙古族文化修養,通過此作品,讓蒙古族音樂通過鋼琴這一載體廣泛傳播開來,對傳播本土傳統音樂文化有著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