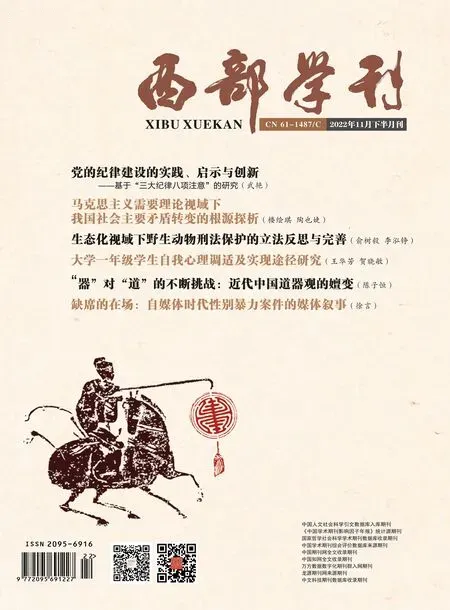五禮制度與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及對當今的啟示
王桂祥
政治儀式通過一系列規范化、程序化的實踐方式傳播主流價值,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具有重大意義。古代社會同樣重視政治儀式的重要作用,五禮制度作為古代政治儀式的集中體現不斷地被修訂與完善,以更好地發揮對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作用。五禮制度作為古代社會培育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舉措,為當代重大政治儀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建立和規范一些禮儀制度,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慶典活動,傳播主流價值觀,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1]。目前,重大政治儀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問題還沒有引起學者應有的重視,因此,探析五禮制度與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一、五禮制度與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闡釋
(一)五禮制度的內涵與發展
“五禮”一詞較早地記載于《周禮·春官》,書中記載“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基于此可知,五禮在內容上主要包括吉禮、兇禮、賓禮、嘉禮和軍禮。其中,吉禮是有關祭祀方面的禮儀;兇禮,是救患分災之禮的統稱,伴隨著封建君主制度的確立與加強;兇禮逐漸演變為“喪禮”的代名詞;賓禮,是維持君主與大臣、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禮儀;嘉禮與日常活動和人生過程聯系緊密,與之相關的飲食之禮、婚冠之禮、賓射之禮、賀慶之禮等均屬于嘉禮范疇;軍禮則是有關軍隊建設和戰爭方面的禮儀。
五禮制度孕育于漢末三國時期,發展于魏晉之際,成熟于蕭梁至隋朝時期[2]。在此之后,雖然歷代王朝對于五禮制度的內容與規則進行局部的調整,但并無脫離五禮體系大致的內容框架。
五禮制度在漢末三國時期得以孕育,從當時的學術背景來看,主張研究古代典章制度的古文經派在重視傳承的基礎上提出經世致用的觀點,逐漸在這一歷史時期崛起,它所推崇的《周禮》與其包含的五禮體系相應地受到重視并得以傳播。從社會現實需要的角度來看,《周禮》比《士禮》體系更完善,更能滿足當時社會的迫切需要。漢末時期的禮儀規范主要參考的典籍文獻是《士禮》。然而,《士禮》對于禮的范圍界定有限,無法涵括國家生活的各方面。因此,學術背景的嬗變以及社會現實的需要使得五禮制度在這一時期得以孕育。
以五禮為中心的禮儀制度在魏晉之際已經出現。《晉書·禮制上》記載:“臣典校故太尉顓所撰《五禮》”,此句中明確指出編纂的是《五禮》,不同于漢代的士禮。這一時期的五禮制度具有不成熟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五禮制度的分類不穩定,處于變化之中。以婚禮為例,三國時期,婚禮屬于吉禮的范疇,魏晉之際,婚禮被納入到嘉禮中,到了東晉,婚禮再次成為了吉禮的組成部分。第二,五禮制度的規則內容更迭頻繁。例如,在明堂祭祀中,漢魏時期需要祭祀五帝,然而新編纂的五禮制度認為五帝與上帝都是同一個神明,不需要祭拜,元康年間又將五帝納入到祭拜的對象中。第三,五禮制度中某些禮儀制度也不健全。例如,東晉的明堂制度不完善。由于建國初期國力較弱,又恐民眾積勞致怨,在東晉初至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明堂。由此可見,五禮制度在魏晉時期還處在一個不斷探索和發展的階段。
五禮制度經過南北朝歷代的改革和發展演變,在南朝蕭梁時期逐漸趨于穩定,走向成熟。南朝蕭梁時期,梁武帝重視禮儀制度的改革,主張建立強有力的制禮隊伍,并汲取歷代制禮的教訓與經驗,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以為永準”的規模龐大的五禮體系。從內容角度看,該時期所修訂的五禮體系為后代王朝所沿襲。北魏時期,魏孝文帝進行“王度惟新”,即實行五禮制度,五禮制度的實踐準則在朝堂活動中深入人心并得到廣泛應用。王肅自南朝歸魏以后,將南齊中的新五禮與北魏的五禮制度相融合,加之歷代君王對五禮的修訂與完善,使得五禮制度更加成熟,成為后世完善修訂禮儀制度的準則和典范。
(二)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內涵
從漢代以來,儒家學說一直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雖然在發展的過程中,正統的地位受到其他學說的沖擊,但是由于歷代學者對儒家主流價值不斷地繼承與創新,儒家價值觀一直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對于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研究主要以儒學所倡導的價值觀為主。
儒家文化價值觀產生于春秋時期,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以私學作為教育媒介進行儒家學說的宣傳。這一時期,儒家文化價值觀的主流觀點是“仁愛”,孔子主張“愛人”;孟子在此基礎上加強與國家政治的聯系,提出“仁政”的觀點。由此看來,先秦時期儒學以“仁”作為主流價值觀念,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漢代,董仲舒在吸取了秦亡教訓的基礎上,主張強化社會等級秩序和思想道德規范,將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附魅化,賦以神權的色彩,為統治者的統治合法性提供了思想基礎。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的主流包括“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等擁有神秘色彩的等級化價值理念。到了宋朝,儒學發展為一種超凡脫俗的自我思辨學說——理學應運而生。理學以傳統儒學為基礎,更加強調人本身的道德養成,主張人通過“存天理,滅人欲”而自覺地遵守三綱五常的道德準則。因此,這一時期的儒學價值觀主要是修生養性、積極入仕等。明清時期,伴隨著中央集權和封建君主專制的強化,儒學的發展也逐漸僵硬化、畸形化,儒學失去了本身具有的教育價值,成為統治人心的思想枷鎖。在這一背景下,一批儒學者為了還原儒學的本質,對僵化的儒學進行批判,即可看作是對儒學的一種改良運動,同時期有關儒學的價值觀主要是經世致用、以民為本的思想。
二、五禮制度是培育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舉措
五禮制度與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表明,五禮制度和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在理論層面上存在著密切的內在關聯。五禮制度是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軟性約束力,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是五禮制度教化世人的主要內容,兩者互為表里,相互統一。正是基于兩者理論上的聯系,五禮制度成為了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重要舉措,在實踐層面上成為了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制度保障、教化工具以及實踐方式。
(一)五禮制度是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制度保障
五禮制度主要以參與者的具體行為是否符合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為標準,通過自身的激勵與外在的約束機制,實現對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保障作用。一方面,對符合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行為進行精神上的鼓勵。例如,魏晉之際盛行軍禮鼓吹制度,鼓吹對象為每次戰事中有軍功的將領,西晉時期“扶風王司馬駿……斬殺數千,招降二十余萬口,進位征西大將軍,徙封扶風王,給羽葆、鼓吹。”通過這一活動,可以促進將士們對忠國忠軍的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另一方面,對于不符合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行為會受到世人的批判和道德的約束。例如,孝文帝為文明太后服喪三年,與“既喪公除”相悖行,東陽王丕上書勸誡,服喪時間過長,會對三個月之后的祭祀大典造成影響。孝文王的行為對祭祀大典造成了影響,與順承天意、敬神保民的社會價值觀相違背,所以受到大臣們的制止,希望通過勸誡的方式以使祭祀大禮可以順利進行。因此,五禮制度通常利用精神激勵和道德約束等方式作為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制度保障。
(二)五禮制度是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教化工具
五禮制度基于古當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教化方式主要有直接教化、隱晦教化、綜合教化三種[3]。直接教化主要表現為五禮制度的相關禮儀內容規定具有明顯的目的性,即內容本身就規定著要傳達某種社會價值觀。例如,明朝時期,朱元璋主張鄉里舉行嘉禮中的鄉飲酒禮時,需要向民眾宣傳《六諭》中的部分內容,包括“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由此看來,朱元璋以直接教化的方式向民眾傳達出尊老愛幼、和睦共處的價值觀念。隱晦教化則意味著需要借助一定的象征符號實現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影響。儀式參與者在舉行儀式時會受到象征符號的影響,進行自我思考和反思,從而實現了五禮制度對其的隱性教化。綜合教化則是指將五禮制度需要借助其他工具,共同實現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教化,如禮與樂的結合。根據《通典》記載,唐初祭祀使用的樂曲會隨著對象不同而改變。“凡祭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在樂曲的渲染上,人們會受到順遂天意,萬物太平的價值觀的教化。
(三)五禮制度是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實踐方式
五禮制度作為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實踐方式,實踐范圍涵括了國家、社會和民眾的各方面。國家層面上,主要通過國家祭祀、慶典等實踐方式培育社會核心價值觀。例如,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注重等級關系,君主與大臣之間的地位界限十分嚴格,這種嚴格的等級觀念便通過祭祀大禮中君王與大臣在天壇的祭拜位置的規定深刻地展示出來。社會層面上,人際關系交往成為了社會實踐方式規范的重要內容。例如,在賓禮中規定,相迎于遠到之客以表尊敬,《禮記·鄉飲酒禮》記載:“主人拜迎賓于洋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通過三揖三讓,培育和傳達出以禮待人、和睦友善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民眾層面上,通過對個人日常生活的具體規定,使人們在人生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受到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影響。例如,在嘉禮中的養老禮中就有“致仕官僚”一說,《禮記·曲禮》記載到:“大夫七十而致仕”,說明魏晉時期官員到了七十歲便可辭官返鄉,享受與做官時同樣的厚祿,蘊含著尊老、愛老、以仁待人的價值觀念。由此看來,從國家到個人生活,五禮制度的相關規定貫穿到生活的各方面,通過對五禮制度的具體實踐,將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價值理念表達出來。
三、五禮制度培育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對當今的啟示
(一)完善政治儀式法律保障體系
五禮制度作為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制度保障,除了發揮五禮制度本身的作用以外,還通常與法律相互配合,共同促進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在這一過程中,也促進了二者自身的完善與發展,古代法律體系對五禮制度的作用集中體現為法律為五禮制度的具體實施提供了制度保障,這對當代重大政治儀式的完善具有重大啟發。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重要舉措,當代重大政治儀式也需要相應地納入法治軌道。目前我國法律層面有關政治儀式的規定存在分散化、模糊化、低層次的問題,為了實現政治儀式的法制化,更好地發揮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作用,建議從幾下幾方面入手:首先,提高政治儀式的法律層次,使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從根本上保證政治儀式的權威性和神圣性,提高儀式參與者的思想覺悟,在心中建立起對政治儀式的敬畏感,自覺地參與到政治儀式的具體實踐中。其次,通過法律規定促進政治儀式的制度化、體系化。需要通過法律條文明確政治儀式的構成子系統的界限范圍,深刻了解每一政治儀式組成部分的內容安排和深層理念,更加準確地設計相應的規則程序,使其每一步表演程式更加明確清晰,從而走出政治儀式處于分散化、模糊化的困境,更好地發揮政治儀式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作用。
(二)推動政治儀式融入日常生活
五禮制度作為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實踐方式,覆蓋到人生的全過程。因此,古代五禮制度更加重視禮儀的日常融入,借助五禮制度的日常性來培育社會核心價值觀。
日常生活深刻作用于政治儀式,相應地,政治儀式也需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首先,日常生活理論更加凸顯人性的價值,因此政治儀式需要更加注重人性的需求[4]。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縮短政治儀式與人們之間的距離,將政治儀式融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充分了解到人們真正的現實需要,充分考慮并盡量滿足人類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需求。其次,通過創新溝通渠道消除隔閡。需要將技術賦能助力政治儀式傳播,采取線上線下多種傳播形式,以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和內容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進而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最后,實現政治儀式與日常生活雙向交流,形成“由上至下”的政治儀式推行,“由下至上”的政治儀式執行結果反饋,兩者處于動態地雙向交流過程中,更好實現政治儀式對于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融入,更快地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
(三)發揮領導表率典型示范作用
五禮制度作為古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教化工具,直接教化的主體往往是學識淵博的教師,或是具有領導力的地方官員和君主,他們往往通過自身模范帶頭作用,參與相關的政治儀式,宣傳其所內涵的社會核心價值觀。
當代重大政治儀式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應該重視領導的表率和示范作用[5]。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帶頭學習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眾、帶動群眾。”[6]因此,領導干部應該憑借個人特質表現出凝聚力與號召力,激發追隨者效仿實行的心理意愿,通過親自參與政治儀式,引導追隨者對政治儀式的親身實踐,促進儀式參與者自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先進典型模范作為一個時代的先鋒,發揮著人格示范感召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行各業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包括航天英雄、奧運冠軍、大科學家、勞動模范、青年志愿者,還有那些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誠實守信、敬業奉獻、孝老愛親的好人,等等。”[7]總之,借助典型模范的社會角色影響廣泛的特點,可以激發公眾參與政治儀式的熱情,更廣泛地實現政治儀式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