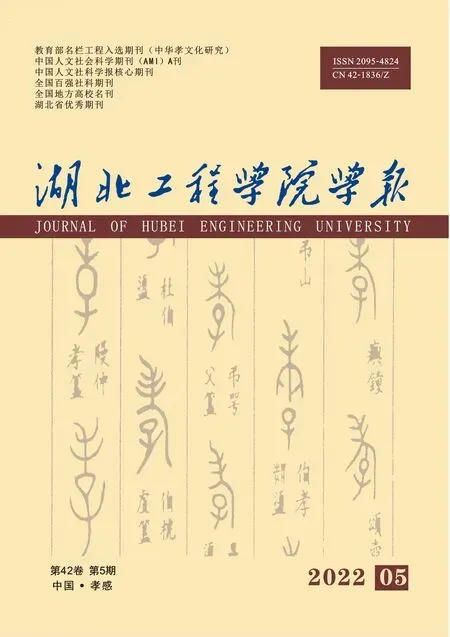傳統孝道倫理的存續動力及其現代轉化
王文娟
(北京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1)
梁漱溟先生曾指出“孝”是中國文化的“根荄所在”[1]307,“孝”作為中國人最核心的價值理念與傳統美德,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并形成廣泛而普遍的文化認同。本文擬從探究傳統孝道倫理在現代社會的存續動力出發,探討其作為當代精神文明建設和倫理道德建設的重要構成的合理性,并嘗試論證傳統孝道倫理在現代社會的轉化與構建,在實現傳統孝道倫理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為推進社會價值秩序的重構和道德進步提供參考。
一、傳統孝道倫理的存續動力
孝道倫理的產生和發展源于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條件下諸合力的作用,即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的經濟基礎、以血緣宗族為根本的政治文化以及以儒家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土壤。進入到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之后,傳統孝道倫理延續的原有基礎與條件不復賡續,但是其存續的合理性與其發展的動力依然存在,具體體現在社會實踐的動力與個體發展的內在需要兩個層面。
(一)傳統孝道倫理存續的實踐動力
實踐是促成認識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也指明了認識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傳統孝道倫理,是中華民族關于古代社會發展秩序和道德規范的認識成果,既是社會歷史實踐的產物,又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得到深化和發展,并將在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進程中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繼續發揮其應有作用。
第一,實踐創造和發展了傳統孝道倫理,形成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既創造了物質財富,也創造了精神財富,而傳統孝道倫理則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人們通過實踐活動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倫理規范,形成的對傳統社會道德實踐和社會秩序整合的經驗總結。
從歷史實踐的層面來看,孝道倫理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其內涵得以深層化、具體化,外部呈現也逐漸制度化、現實化、普遍化。孝道倫理根源于夏、商、周三代祖先崇拜與“敬祖”的觀念,通過“修宗廟、敬祀事”(《禮記·坊記》)等“享孝”祖先、“追孝”祖先、祈求祖先保佑等活動,使得宗族內部獲得一致的族群認同,從而達成凝聚宗族內部情感、維系宗族團結的功能。[2]74-79因此從起源上看,孝道倫理與族群認同有著密切的關系,并在早期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民族認同的產生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先秦時期,《論語》《孟子》《禮記》所提出的孝親、敬親原則與規范,奠定了孝道倫理的基本內涵。漢代出現的《孝經》則為孝道的社會化、政治化準備了條件,“孝治天下”成為最核心的統治思想,并逐一落實在制度和教化媒介的實踐上。在制度方面,漢代開始設立“孝廉”以全國性大力表彰、褒獎孝悌行為,宋代以后朝廷完善旌表制度,增加旌表種類和人數,明清時期則通過圣諭宣講及定期頒布的教化書籍落實孝治教化機制,發揮其公共性規范的作用。同時,民間的家訓、族規在勸勉孝德、具體的獎勵與懲處措施方面與朝廷的政策舉措相輔相成,成為推動孝道教化的重要力量。[3]35-41而《孝子傳》《二十四孝》等書籍的流布與傳播,以及圖像、戲劇、歌謠的繁榮發揮其教化媒介的作用,引導人們在日常活動領域樹立道德意識和價值觀念,塑造社會良好風氣。在長時段的制度與媒介雙重作用的實踐過程中,孝道倫理以自覺的形式融入了社會的價值系統中,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并深入民族心理和文化基因,為古代社會集體情感的凝聚、族群的整合及社會秩序的建構和維護提供擔保。
第二,社會實踐的發展仍然要求孝道倫理持續發揮價值整合作用和提供精神支持。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發展改變了傳統社會原有的結構和運行機制,在價值觀念上也與以往社會的傳統觀念存在差異。但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人們以家庭本位的生命根源意識仍然存在,基于自然性的血緣關系是無法解除的,而由此產生的親子間的原初性情感也是無可替代的。尤其在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宰制下的現代社會,人的功利性思維、物質欲望被無限放大,人文精神日漸萎縮,價值虛無主義、社群倫理盛行,社會、文化層面的認同難以達成。這些實際要求人們積極思考和處理傳統和現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呼喚人們從最穩固、最持久的核心文化認同入手尋找重建社會價值和秩序的良方。
傳統孝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中華民族區別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質。孝道倫理依據家庭本位的生命根源意識與自然性的血緣親情,在現實生活中結成牢固的“慈”“孝”一體的情感聯結,是個體身份認同不可磨滅的文化胎記,是孝親實踐得以發生的根本因素,也是建立共同文化心理與社會認同的基礎。西方哲學注重個人的理性、智慧等德性,對家庭的關注與重視遠不如儒家。儒家文化強調愛有差等,也就是說,仁者固然要愛人,但是“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親親為大”(《中庸》),這一點不同于墨子的“兼愛”、佛陀的“平等心”與“無分別心”以及基督講的“愛你們的敵人”(《馬太福音》)。“愛有差等”這一立場是基于人類特殊生存關系所作的合理判斷,因為親子關系在人類所有的關系中,是最親密、最純粹的,孝親是一種基于自然性血緣關系的最原初情感,自然而然,無從推拒。相反,不從父母、親人出發的愛既違背了人類自然情感,也極不現實,所謂“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孝經·圣治》)。認識孝道倫理這一獨特意涵及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優勝之處,進而升起對自身文化的自覺領會,為培育文化認同奠定根基。對日益人情冷漠的現代社會中的孤立個體而言,孝道倫理所飽含的充沛情感關懷不僅成為個體生命根源意識確立的來源,而且為個體在現代快節奏、高壓力的生活提供精神價值上的寄托與文化上的歸屬感,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通過一個個個體的自我身份及文化價值觀的確認形成一種整體的社會意識,是重建真正具有約束力的社會文化認同的必由路徑。同時,孝道倫理包含的具體規范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心理紐帶的作用,其中愛敬、忠勇、誠信等為人處世之道始終處于中國文化共同理念的統攝之下,這些共通的價值和規范早已厚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融入人的基因之中,并將繼續為傳承和發展傳統孝道倫理發揮作用。
實踐是傳統孝道倫理得以存續與發展的不竭動力之源,傳統孝道倫理在實踐中的不斷發展也昭示出其未來將繼續在實踐的檢驗下不斷調整和自我更新,實現對自身的揚棄與創新。而現代社會結構轉型、新型家庭關系的構建、人口老齡化等社會問題,也呼喚并將推動孝道倫理不斷向前發展,在形式和內容上不斷地更新以適應現代化進程。
(二)傳統孝道倫理存續的內在動力
傳統孝道倫理在現代社會的存續和發展既有社會實踐的需要,也有個體發展與完善自我的內在的精神需要,后者更有不隨外部條件變化的穩定性特征。這種內在需要不同于現實中事物因其自身的缺乏或不平衡而產生某種需要,而是出于發展自身、完善自身的內在動力。馬克思曾指出:“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從而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某種新的生產對象具有什么樣的意義。人的本質力量得到新的證明,人的本質得到新的充實。”[4]233人的需要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文明發展的尺度。人的需要的豐富性標志著人的本質力量的證明和充實,人的需要既有現實物質的需要,也有發展與完善自我的精神需要,不能因為強調物的尺度而忽視人的尺度,忽視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實現。傳統孝道倫理不僅為個體在實踐中形成統一的德性人格與美德的養成提供條件,更為個體在社會實踐中提供道德原則與公共性規范指導。
第一,個體人格的成長與統一需要以孝道倫理為核心的德性實踐來完成。“孝”首先是一種私人性美德,“愛”與“敬”是孝道的核心精神與道德準則。孝養父母不僅僅體現在物質方面的贍養,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 孟子也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因此,真正的孝養是心理與精神方面關懷、尊重父母,對父母的尊敬與發自心底的愛讓父輩在精神上感到愉悅,人格得到尊重。王陽明曾指出:“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5]3這說明對父母的“愛”“敬”與孝不是簡單的外在規范,而是內在的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統一,日常生活不能履行孝道,其根源在于個人的道德責任感和意志力的缺失。這就需要從個體內在意識層面的統一結構即統一性人格的養成,并在實踐中貫徹執行。而孝道也不是一時一地的私人性美德或家庭內部規范,而是如《孝經》指出“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道實踐的對象是處理家庭、社會、國家的關系,是不斷自我反思、人格成就的德性修養過程,最終的落腳點乃是成就自身人格、完善個體德性。在這個過程中,孝道倫理不完全是一種外在的律令,而是以主體人格的德性養成為基礎,因而能產生持續的、自發的道德行為。正如麥金太爾所說,只有擁有正義等德性的人,才可能理解如何去運用法則,[6]9否則只是徒有其文。孝道倫理只有以個體人格完整、德性完善為基本價值尺度,否則就只是一種社會外在的義務、規范,最終淪為外在的形式。因此,真正的孝道是以道德人格培養、美德養成為起點,從愛親、敬親、尊親情感的培養逐漸將“愛”“敬”的情感內化為美德,最終形成統一的德性人格。孝道倫理的存續和發展符合個體發展的內在需要,首先就在于其實踐是個體德性人格和美德養成的基礎。
第二,個體需要奉行和貫徹孝道倫理道德準則及公共性規范,以達成個體與家庭、社會、自然的和諧。孝道倫理包含具體而全面的道德規范,旨在促進個體內在意識層面統一結構在實踐中的形成。如《孝經》中所指出的:“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顯然,“孝”的對象除了父母之外,還包含君、友、民等維度所涵括的規范,除了愛、敬的德性,還有莊、忠、信、勇等品德。這些規范不局限于家庭內部的代際倫理關系,而且為個體在社會的行為劃定提供規范和原則,可橫向拓展至社會倫理、生態倫理領域,并指向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重維度。[7]23這里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心理基礎即人人皆有慈、孝、愛的同理之心。《孝經·天子》指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關愛、尊重自己的親人,有此同理之心,就不會輕視、慢待他人,而是以此心推度他人,從他人立場出發,想他人之所想。這樣,孝道就從私人領域的和睦家庭,推展到公共領域中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孝經·廣要道》指出:“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孝道不僅僅是家庭生活倫理與個人美德,也是政治意義的公共性規范,還可以在族群與族群、人與自然生態領域中貫徹。以同理之心推度族群與族群的交往、后世的資源可持續與生態平衡的問題,則是代際倫理向社會倫理、生態倫理的過渡。因此,由孝道倫理所包含的“愛”與“敬”的核心精神與道德原則,由此從代際關系拓展到社會關系、生態問題,成為處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準則,構筑一個以“愛”為起點、“敬”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和公共價值規范系統,最終能在實踐中促進個體與家庭、社會、自然的整體和諧。
個體是孝道倫理最初的實踐主體者和直接受益者。傳統孝道倫理經由家庭內部的父慈子孝,再由個體向外逐一推擴到社會的愛敬有禮、友愛互助,最終又反過來使每一個個體從社會整體的提升中獲益。因此,個人的內在需要是推動傳統孝道倫理存續與發展的直接動力。
二、個體主義情境下傳統孝道倫理的困境
從社會實踐和個人內在需要的層面來看,傳統孝道倫理存續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現代社會,理性個體、自由意志成為道德敘事的主要進路,某種程度上傳統孝道倫理對禮教權威、道德反身性的強調與非條件性的絕對立場,與現代社會所強調的個體權利、自由和情感之間存在極大的張力,使得傳統孝道的履行在現代社會走入困境。這些困境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絕對禁錮性的禮教宗法權威與個體權利和自由人格追求的矛盾。現代社會道德倫理領域的實踐,其核心是強調個體的自由、平等與權利,本質上是依托理性個體、義務論來實現人際關系的有序與和諧。而傳統儒家的孝道原則從根本上來講是基于血緣關系和宗法觀念的產物,在歷史實踐中體現為以“三綱”為代表的禮教與君權、父權的絕對權威。近代以來,受西方自由平等觀念的影響,強調個體的權利與獨立人格的聲音頻頻出現,如譚嗣同痛切詆斥“三綱”之說:“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8]65,就是對包括父權在內的三綱對子女自由和靈魂的壓制進行批判。流傳至今的二十四孝中的某些故事如“臥冰求鯉”到底是“大孝”還是“愚孝”,其判別分野就在于個體是否在此過程中,還保有理性思考能力與自由判斷。如果不論事實與對錯,一味地將責任歸之于子女,在現代的視角下并非“大孝”而是“愚孝”,是現代社會不能認同的觀點。對于這一點,陳獨秀也極力批判,更指出以忠孝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四大惡果:“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平等之權利(如尊長卑幼同罪異罰之類);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9]37盡管孔子也有“諫親”、“不順其于親”的說法,但是站在維護絕對父權的立場上要求子女無條件孝順父母,即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的觀念,在歷史上乃至當今社會某些地區和家庭的觀念遺留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盡管近代以來聲音的批評可能部分誤解了孔孟傳統孝道的真正意涵,同時也存在將對形式主義的孝的反對擴及到整個傳統人倫價值這種以偏概全的嫌疑,但他們捍衛個體的平等權利與獨立人格,以及倡導從單向順從到雙向互愛的親子關系,無疑更符合現代社會的觀念和價值取向。而絕對禁錮性的禮教宗法權威下的傳統孝道與現代社會所存在巨大的張力,勢必會與現代社會個體主義情境下對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的追求發生沖突。
其次是單向的道德義務與現代社會責任與義務對等及親子間的雙向道德的矛盾。傳統孝道倫理強調子女一方對父母一方的道德義務,當親子關系出現不諧時,主張子女一方應反省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而導致方父母的不滿,但并不重視對父母一方責任的要求。現代社會則強調不同個體之間責任與義務的對等關系,如果單向地從一方身上找問題,就會導致對責任方過錯的忽視,以及對義務方的過度責難,從而將親子之間的雙向關系轉變為子女對父母的單向關系。民國時期施存統在報刊上發表《非孝》一文,指出“孝是一種不自然的、單方的、不平等的道德,應當拿一種自然的、雙方的、平等的新道德去代替它”,就指出其中的實質差異,因此引起了巨大的震動。[10]2現代社會觀念更肯定在親子關系中的雙向道德,子女有履行孝道的義務,父母輩也有撫育、教養的責任。現代社會的輿論對親子關系中未盡到撫育與教養責任的父母,大多抱持批評的態度。比如近年來社會新聞中虐待、苛待孩子的父母,招到大眾輿論的一致批評,對孩子的身心健康冷漠以對的父母、不盡教養之職的父母也都持批評態度。一旦發生此類父母年老被棄養的現實案例,輿論中就有站在同情孩子的立場而批評父母的。棄養父母一事固然有待商榷,但是輿論的偏向反映出對未盡責任之父母的批評。還有近期社會發生的事件,某女士將孩子送養他人多年后,又要求孩子為自己養老,不但輿論傾向于站在孩子的立場,法律也傾向于認可孩子只有贍養其養父母的義務。而更深層次的對是否需要重新定義父母的追問,則反映出對僅由血緣而單方面生成的親子關系的反省:父母與子女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與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形對等,對于沒有盡到父母義務的人,他們要求子女兌現贍養義務的權利理應被忽視。這些看法都更重視個人的責任與義務的對等,與傳統孝道倫理的要求大異其趣。
而一味地要求義務方通過單向的道德自省來化解親子沖突,不僅與現代社會以及法律所遵行的責任與義務的對等原則相沖突,也會造成對義務方的過度責難,導致親子關系的單向化與片面化,最終成為孝道履行的現實障礙。因此道德自省要設定界限,不能無限地將責難歸諸于義務方,這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當然,只要求責任與義務的對等是一種較低層次的要求,傳統孝道倫理所體現的是對個體更高一層的道德要求,如何使這兩者相適應,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再次是對道德理性的過度強調與自然人情之實的矛盾。現代社會人際關系除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自由選擇的權利,也充分肯定自然情感的作用,呼喚以合乎人情的方式解決矛盾沖突,而不是通過硬性要求或者強制來實現。但在傳統孝道領域,對人的真實情感多有忽視,而主張用道德理性來戰勝情感的沖突,甚至否定真實情感。以古代以“孝”聞名的圣人“舜”為例,舜的父親瞽叟、繼母及繼母所生弟弟象,不但沒有善待他,反而多次欲置他于死地,但是舜依然孝敬父母、關愛兄弟,因此被視作古代圣人,他的“孝”為世人所尊重并視為榜樣。孟子注意到在舜的內心深處可能存在情感郁積,稱這種情感為“怨慕”,意在表明舜的心里既“怨”且“慕”的真實情感狀態,同時孟子認為舜以高潔的道德與人格修養化解了其間的緊張。但在宋代以后的闡釋中,無不突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的絕對立場,同時將“怨親”轉向“責己”,傾向于取消人的真實情感沖突而抬高道德理性的價值。這一做法無疑是對人的真實情感的簡化和背離,而一旦背離人的真實情感,道德要求容易淪為一種外在的壓力,有抵消道德自覺努力的消極影響。這也是清代學者批評宋代理學家以外在的道德規范壓制人情,即“存天理滅人欲”、“以理殺人”的根由所在。
事實上,現代社會人們更崇尚自然性情的流露,主張人的情感中有正面的情緒,也有負面的情緒,這兩種情緒并非完全對立,而是互相映照。比如“愛”和“恨”都屬于人的自然情感,一般而言,“愛”則是一種正面的情感,對人產生較為積極的影響;“恨”對人的行為產生消極的影響,是較為負面的情感。當遇到內心渴求、喜愛的人或物時,“愛”隨之而生;而當遭遇不公時,“恨”這一情緒就會在主體心里產生。在家庭成員之間,人們主要的情感取向是“愛”,而否定“恨”。但是作為不同個體的家庭成員之間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完全沒有沖突的愛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最親密的愛人、親子之間也會存在一定的沖突。因此,隨著現實生活的復雜展開,“愛”與“恨”同時會出現在家庭關系、人際關系中,這才是人情之實。一味回避成員之間的差異、矛盾和沖突,視抱怨、怨恨不具正當性,或者要求人們用“愛”去包容“恨”、抵消“恨”,不但不利于緩解矛盾,反而會稀釋原有的“愛”。[11]47正確的途徑反而是尊重人情之實,讓抱怨與不滿抒發出來,在家庭、人際關系中尋找“恨”的根源,用公正、平等的機制、自由與開放的交流化解矛盾和不公。這也是“恨”的意義所在,即迫使人在愛恨情感的沖突中運用智慧達成理智與情感的統一,明瞭愛的本質和生活的真諦,并促成現實生活的改善。因此,現代社會家庭更加重視家庭成員尤其是親子之間的理解溝通,通過情感的交流互動自然地達成內部的和諧。
此外,還有一些具體條件的變化也使得傳統孝道的奉行面臨困境。比如,現代社會精英化教育中,更突出個體權利與自由,對道德情感、孝心的培養、有所削減;城市化進程中,不少人為改善生活而選擇離開家鄉工作,親情淡薄、親子關系疏離的背景下造成的留守兒童問題也日益突出,更遑論奉行孝道;還有隨著男女地位漸趨平等,女性能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改變了原本母親教導照顧兒童的社會習慣,家庭教養的功能有所減損,孝德的培養不夠完整。這些問題都將引發傳統孝道倫理如何進一步融入現代社會的深入思考。
三、傳統孝道倫理現代轉化的路徑建構
以上我們梳理并分析了傳統孝道倫理存續的合理性及其在個體主義情境下與現代社會的張力與矛盾,在此基礎上我們嘗試建構當下傳統孝道倫理現代轉化的路徑。
第一,以對傳統孝道倫理的現代闡釋為著力點完成現代轉化。傳統孝道倫理的現代轉化要以其現代闡釋為著力點,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樹立整體思維和全局視野,立足新時代的社會實踐,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尤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標準對其內容做出合理選擇,對其中符合世界文明的普遍發展趨勢、反映中國社會發展客觀要求以及人民群眾合理需要的價值,用當代中國的語言概念詮釋和轉化,使之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為現實社會服務。如對作為孝道倫理核心的“愛敬”的原則進行現代激活與闡釋,使之適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與培育;而“敬養”、“色養”的概念則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和重構,使其獲得現代的表達方式與思想內涵,為現實服務。而孝道所包含的繁衍、養育、庇護后代的內容,在當代仍然是人類最重要的情感關系和生活方式,孝道包含的尊親養親、扶老攜幼的基本義務,也具有超越時間和地域的普遍性意義與內在價值,這些內容如何在變化的現代社會情境發展和弘揚,并應對新出現的如留守兒童、家庭教養功能趨弱的社會實際,是其轉化和創新應著力解決的問題。與孝道倫理相聯系的仁(愛)、敬、忠、勇、信的道德觀念,對于處理好個人、家庭、社會、國家、自然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和功利主義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這一方面的內容也應得到挖掘和闡揚。
傳統孝道倫理盡管傳承了千年,但其中包含的某些內容不完全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理念,或者與新的時代出現了不太融合、不太適應的情況,需要在內在批判的基礎上進行合理選擇與現代轉化。比如傳統孝道倫理中包含的“父為子綱”的等級制度、絕對父權與人身依附觀念,無疑與“獨立”“自由”“平等”的現代意識背道而馳,因此應當堅決地予以摒棄。對于片面強調單向的道德義務以及子女一方的責任,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發揚其慈孝一體、愛敬一心的雙向倫理關系,與主張平等的現代社會家庭倫理與雙向道德相融合。此外,孝道倫理所包含的對道德理性的過度強調,也應與現代社會對自然人情的重視相貫通,從情感的角度入手,呼喚親子關系中的情感交流、平等尊重與有效互動,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實現家庭內部和諧。總之,傳統孝道倫理的傳承、轉化與創新必須基于當代社會實踐和人民需要,為支撐和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而主動地實現其自我更新和現代轉化,與當代中國價值理念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第二,以家庭教育與個人教育為切入點,建立生命根源意識和文化認同。家庭是人們最早接受道德教育的地方,盡管現代家庭結構與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但家庭依然是社會最基礎的構成單元,家庭教育也依然是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基于自然性的血緣關系而生發的原初情感仍然深厚而無可替代與解除,因此以家庭為單位,從個體教育入手,在家庭內部建立起深厚親密、平等尊重的親子關系,并倡導家風、家訓文化建設,為個體提供一般性的道德意識與道德觀念,進而深化對孝道倫理的生命根源意識、慈孝一體的情感關聯以及愛敬一心的倫理原則的認識,從個人內心建立起核心文化認同,緩沖現代社會文化沖突帶來的割裂感。個體通過家庭教育踐行孝道倫理,找尋自我成長與價值實現的寄托與安慰,確認和深化個體生命根源意識,在日益人情冷漠的現代社會,建立自我認同和社會文化認同的歸屬感,為鞏固主流意識形態存在的社會文化心理基座,有效應對社會信仰坍塌、規則失序等日益泛濫的現象,以及人情淡漠、孤僻焦躁、暴力傾向甚至反社會人格等心理疾病而引發嚴重的社會道德危機準備條件。
第三,以當代社會實踐與現實生活為落腳點,培育道德自覺與德性人格。當前社會的道德危機,某種程度上是現代社會流行的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所引起的價值危機,弘揚孝道倫理背后隱含的中華傳統文化價值本位、道德優先的立場,從家庭道德出發,培養個體的德性人格和修養,能有效地糾偏這種價值傾向,從而扭轉和化解道德危機。要立足當代實踐,直面時代問題,探索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個人層面相結合的多維路徑,通過官方制度建設引導與社會教化相配合,規定不同成員在社會共同體中應當履行的義務和責任,使之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內在肌理之中,從而發揮“潤物無聲”的導引作用。官方制度層面,可以借鑒恢復部分禮樂、旌表等方法推廣孝道、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構建和完善道德評價體系與社會輿論機制,規范社會共同體中不同成員的相互交往與行為協調。社會教化方面,則通過書籍、廣播、電視、網絡、報業、微信、微博等多種媒介建立宣傳網絡,創新宣傳手段,發揮耳濡目染、日熏月染的習成作用和場域作用,用讀本、圖像、戲劇、歌謠等多種形式大力弘揚孝老愛親、孝敬文化等中華傳統美德,運用巧妙的文創產品真正融孝道倫理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于一體,積極引導與激發自覺齊頭并進,使社會大眾在渾然不覺的日常生活中建立起道德自覺。而在個人層面,最根本的是把德性人格的培育作為教育的核心,將孝道的德性培育理念融入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當中,塑造具有穩定、統一的德性人格的個體,為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的實現奠定基礎。只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體層面深入人心,才能逐漸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的現實中生根開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12]傳統孝道倫理存續的合理性,既有其歷史依據和現實需要,也存在貫通古今的合理內核。而針對傳統與現代的疏離,傳統孝道倫理與現代社會個體主義情境的矛盾,我們所進行的傳統孝道倫理的現代構建,就是為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找尋與時俱進的模式和實現路徑。當下,只有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挖掘其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為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也只有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的豐富營養,積極運用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實踐中,才能激活其生命力,增加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在充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和實現。在此背景下,積極探索與構建傳統孝道倫理現代轉化的深層理論和現實路徑,有助于其在新時代的價值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