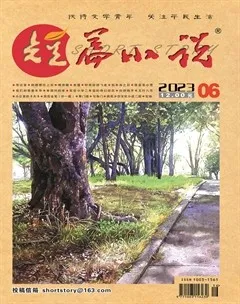我在小學二年級的奇幻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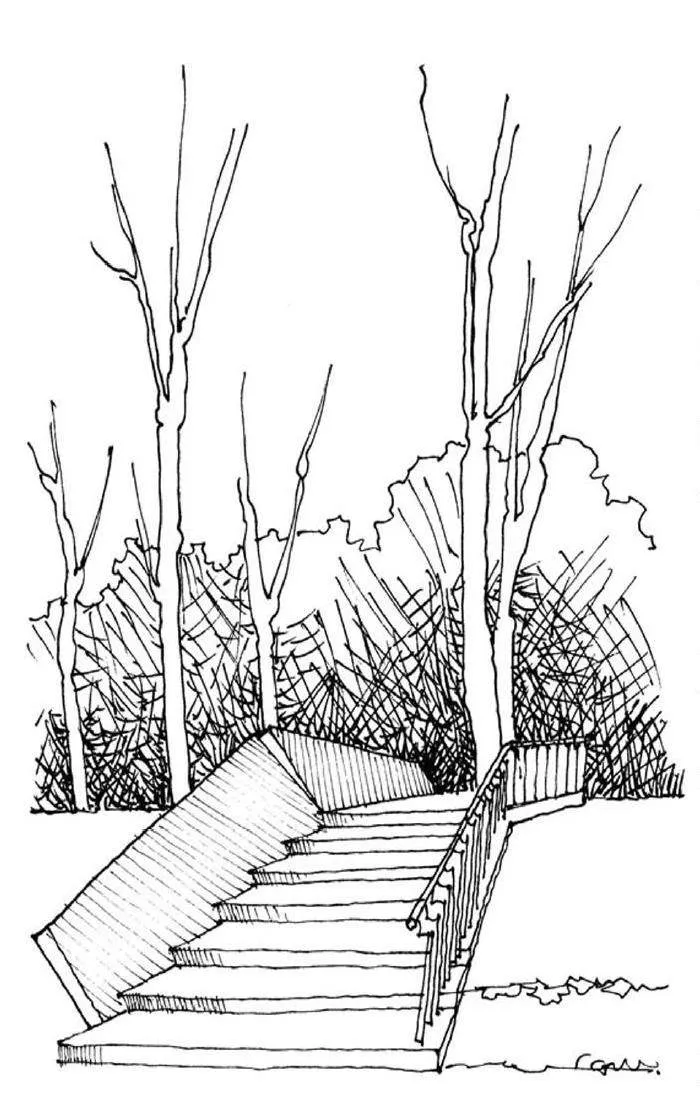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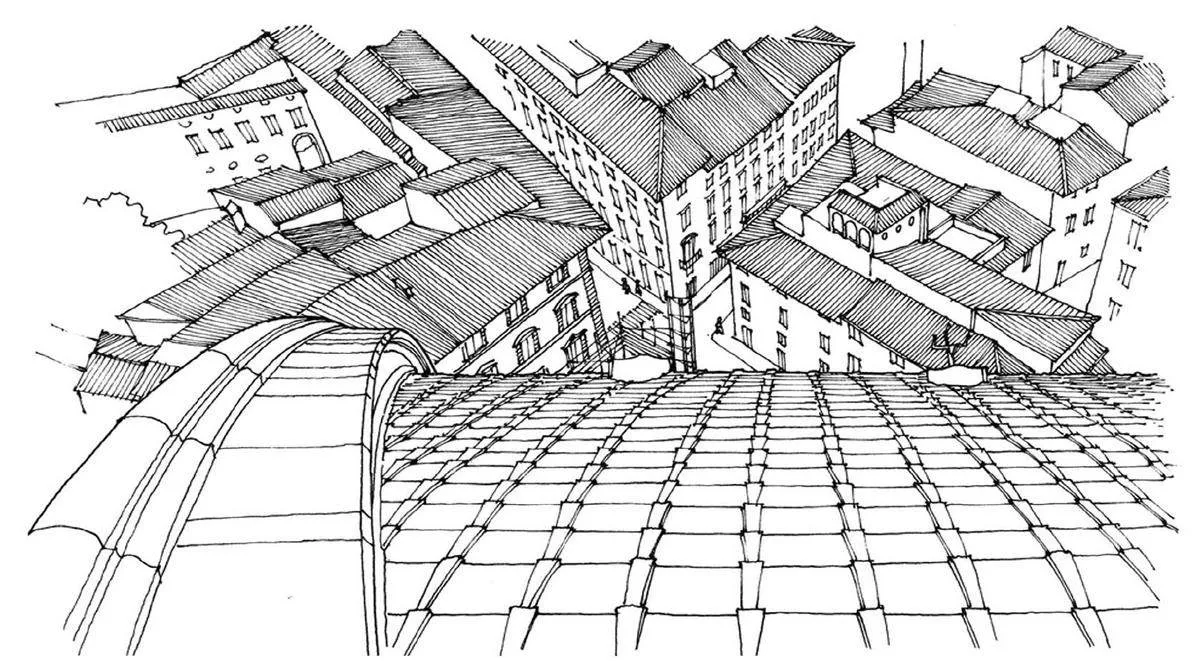
作者簡介:
盧海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有400余萬字作品散見于《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鐵路文藝》《滇池》等報刊。作品多次被《讀者》《青年文摘》等雜志轉載。已出版文集《東北的土灶》《在路上,遇見時光》《微風輕拂》《光陰深處的東北表情》。
李軍和董良到校的時候應該是下午兩點半還多。被我們當作操場的小院子里,張小紅和于大海帶領十幾個同學正在玩“打仗”,那天玩的是“紅色娘子軍”,張小紅扮演吳瓊花,于大海假裝洪長青。他倆帶了幾個人繞過刺棘和柞樹棵子圍夾成的廁所,繞過附近的兩棟草房,繞到教室后頭,繞得“敵人”徹底蒙圈了,才借墻角作掩護,隱蔽起來。
學習成績最差、長著傻大個的劉真文扮演南霸天,他和幾個嘍噦兵就是所謂的“敵人”。劉真文帶著他的手下滿操場尋找,虛張聲勢地吆喝:“出來!”“出來!”他們哪里想到,已進入了“八路!軍的包圍圈”,只聽得教室墻角處于大海興奮地大喊一聲:“打!”頃刻間由算草紙包著的泥沙包如子彈一樣向他們飛來,這便是“八路軍”的手榴彈,劉真文帶領的人群中籠起一片煙霧,中了彈的孩子們四散逃跑,跑出包圍圈后,氣喘吁吁地拍打頭上身上的灰土,吐出嘴里的泥灰,有人急了,哭哭唧唧地號“不帶這樣式的”“不帶這樣式的”。劉真文剛要罵幾句,猛聽得“沖啊!”好幾個人的嘶喊,接著張小紅于大海舉起柳條編織的手槍沖出來,他們見人就推,推倒為止,沒有武器的同學拿著柳條棍子白蒿鞭子也叫喊著沖上去。因為人多,劉真文和他的部下被張小紅他們摔在地上,用棍子和鞭子抽打得嗷嗷直叫,最后還要被于大海一只腳踏在肚子上或是屁股上,嘭的一下“槍斃”。
“南霸天”一伙有幾個人被打哭了,張小紅和于大海全不在意,罵一句問:“還能不能玩了?玩不起滾犢子!”抽抽搭搭的也就止了哭聲,勝利的這一幫氣勢高漲。
其實,誰都不愿意當南霸天,誰都不愿意跟劉真文一伙,可惜,想加入哪一伙不是自己說了算,要聽張小紅的,因為她是班長。每次玩打仗,贏的總是張小紅和于大海,他們永遠都要扮演“八路軍”,那時候我們分不清部隊的稱謂,只知道八路軍是“好人”,“好人”就一定要打敗“壞人”,所以,扮演壞人的,活該要挨揍。
我和曹艷躲在屋子里,看得觸目驚心。再快樂的游戲都沒有我們什么事,我倆是不被待見的北頭二隊的孩子。這個名叫高麗屯的小村子共有四個生產隊,一隊和四隊在南頭,二隊和三隊在北頭。一隊勢力最大,屯子里的占山戶連同他們的大家族都在那里,連大隊書記家也分在一隊,二隊是七拼八湊的外來戶,窮人最多,三隊在溝里,離屯子三里路,四隊在最南頭,是我們老師家歸屬的生產隊。張小紅是大隊長的女兒,于大海是一隊隊長的兒子,這響當當的身份,連我們老師也得讓三分。
那天中午,本來,我和曹艷訕訕地站在教室門口賣呆,不時發出討好的笑,有一次可能是笑錯了,于大海看到我們,他脖子一歪,對我倆吼:“看什么看?滾回去。”曹艷被罵得滿臉通紅,白了他一眼,我膽小,趕忙轉身進屋,老老實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手伸到露出一個大洞的桌膛里,下巴拄在殘破的桌面上——這是我們班最破的桌子。我不知道老師什么時候會來上課,也不知道那時候幾點鐘,只覺得午飯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甚至感覺有些餓了。教室里靜悄悄的,我和曹艷也無話可說,只有聽到外面聲音特別大時,才會抻長脖子偷看一眼。
這是村子南頭一座廢棄的草房,大約20平方米,凹凸不平的黃土地面總是煙塵斗亂,灑多少水也壓不住四處飛散的灰塵。窗子窄小,窗框破舊,屋子有些暗。一進門左手邊的墻上掛的是破了一個大洞的黑板,右手靠墻放一張桌子,上面放著我們的作業本,這個角落可以算作老師的辦公室。黑板對面放了八九張長條桌子,桌膛里是五花八門的書包,桌與桌之間是常常會掉腿的長條板凳。
教室后面的墻角處堆了一些黑黢黢的磚頭,那是留待冬天砌爐子用的。另外的墻角堆著樺樹枝掃帚、糜子笤帚,還有扁擔和水桶。也不知是誰的命令,從二年級開始,我們就告別了屯子北頭那幢磚瓦結構、有校長有高年級同學有體育老師的正經學校,成了后娘養的,被派到南頭的破爛教室上學,一上就是兩年。
這里天高皇帝遠,沒有音樂體育自然常識課,只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姓孫的女教師,我們的課有三種:數學、語文、自由活動。這里沒有鈴聲,下課聽老師的,上課則全靠喊——老師對著某位同學說,上課吧,這位同學立刻接了軍令,飛奔著出門,對著操場上玩得正開心的同學,兩只臟手圈成喇叭狀放到嘴巴上大喊:“上課啦!”接了軍令的同學接著喊“上課啦!”人體鈴聲響過,同學們呼哧帶喘地跑回教室。
一天上幾節課,什么時候上課,每節課上多久,悉聽老師安排。
那天中午,和許多炎熱的午后一樣,老師一直沒來,我和曹艷坐在教室里,百無聊賴。外面的同學玩得人聲鼎沸,我們熬不住,坐到窗子邊上向外看。根據“紅色娘子軍”的劇情,吳瓊花要“被捕”,但憑借劉真文他們是根本抓不到張小紅的,所以有些情節只能一帶而過,張小紅打得膩了,便主動跑到劉真文面前,表示算自己已經被南霸天抓住,要于大海來救。
追捕,拷打,救援,逃跑,犧牲……打仗的元素一直如此,游戲也是一樣,張小紅蹲在一根電線桿子下面,那里便是她的牢獄,劉真文的手下,一個叫王樹寶的拿了一根柳條站在她身邊,假裝是監獄的看守。王樹寶舉起樹枝,做出一臉狠樣向張小紅抽去,他可不敢真打,只能作勢抽打電線桿子。于大海帶剩下的人繼續與劉真文周旋,他要把吳瓊花救出來。
李軍和董良就是這時候到的,他倆家住三隊,三里多路的螞蚱蜻蜓就是他們的絆腳石,他倆幾乎天天遲到,通常的理由是“吃飯晚了”,然后絞著手指低著頭,站在門前看老師的白眼,聽老師咒罵訓斥,拿小眼睛掃視對他們擠眉弄眼的男生們,直到一節課過去,老師心氣平了才可以回座位。
因為老師來得晚,李軍和董良總算沒有遲到,看到同學們幾乎全員參加的課間游戲,他倆沒有直接進教室,站在教室門口賣呆,滿眼都是羨慕的神色。
許是玩得膩了,或者劇中人物上身,于大海在經過兩人身邊時,忽然出手把他倆狠狠推了一把,把紙包的泥沙砸在他們胸前的衣服上,嘴里還不干不凈地罵著,歪著腦袋說,看什么看?
李軍和董良踉蹌了幾步,董良一屁股坐在地上,泥沙包弄得他滿頭滿臉都是泥灰,他閉著眼睛,呸呸呸想要吐出嘴里的沙子,吐了一會兒,低下頭撲落發里的沙子,又使勁拍打衣裳,拍得煙塵四起,不過他總算晃晃悠悠站了起來,用臟手背揉眼睛,揉得臉上黑一道白一道的。
李軍摔了個狗搶屎,跌得滿嘴泥沙,他用雙手撐起身子,爬起來,往外一吐,竟然吐出一口血來,原來被小石頭磕破了牙齦。李軍是個白胖小子,因為胖,臉大,眼睛格外小,見了血,小眼睛瞇成一道縫,張開大嘴號啕大哭起來。
董良是李軍的姨表哥,聽見李軍哭了,勉強睜開眼睛,見他嘴角流血,嗷的一聲沖過來,瘋子一樣推了于大海一把,磕磕巴巴地罵了一句。
于大海的腦袋歪得更厲害了:“嚓,你敢動我?還敢罵我?”說罷沖過去,一腳踹向董良的肚子。董良個子大,說話磕巴,人也傻里傻氣,那天也不知道哪來的一股勁,竟然一下子躲過于大海那一腳,反手過來給于大海一個大嘴巴。
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于大海哪受過這個,他愣了一下,反身沖進教室,正當大家莫名其妙時,于大海已經拽出一長條凳子,抱住,凳腿就像兩只腳,揸開,于大海舉起凳子向董良砸去
畢竟人小力微,凳子沒夠到董良,落到地上,董良嚇得臉都白了,轉身就跑,于大海抓了一把沙子追過去,一邊追,一邊把沙子揚到董良身上。看熱鬧的沒有一個想要拉架的,反跟著起哄,像玩打仗一樣跟在于大海身后一起去追董良。
一大幫人圍著教室轉了一圈,又來到教室門口,見于大海扔下的凳子還在,董良撿起來,準備負隅頑抗,于大海見近不了董良的身體,又沖進教室,這回他直接沖到教室后頭,抓起扁擔就往外跑。
于大海掄起扁擔就打,董良舉起凳子迎上去,乒乒乓乓又是一頓混戰,于大海的腿被板凳砸了,一瘸一拐,董良的臉和后背都被扁擔掄了,臉上青紫一塊,衣服被扁擔鉤刮了一個大口子。
李軍也來幫忙,抓起沙子往于大海的臉上揚,這時候張小紅發出命令:“揍他。”看熱鬧的不知班長讓打誰,見張小紅進屋撈了板凳,也跟著進屋撈板凳,見張小紅去打李軍,也跟著去打李軍,李軍又胖又笨,兩板凳就被拍倒了,昏死過去,董良嚇壞了,扔了板凳去喊李軍,張小紅和于大海也住了手,大家全都住了手,圍著李軍忐忑。
王樹寶嘀咕說,他是不是死了?這一問,大家都怕了,不約而同扔了凳子,好像打人的是板凳,跟他們全無關系似的。
當老師的大概都會神機妙算,總是能在關鍵時刻上場——正當大家束手無策時,孫老師像沒睡醒似的,邁著懶洋洋的步子走過來,眼尖的同學看到了,一句“老師來了”就像強心劑,讓同學們瞬間元神回籠,大家自覺把凳子拿回教室,掉了腿的凳子被小心支好。連李軍也無聲無息地爬起來,揉揉這,揉揉那,蹣跚著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董良臉上的青紫,李軍腫得像桃子似的眼睛,孫老師連問都沒問一句,倒是于大海吸著氣揉膝蓋時,孫老師溫和地問他怎么了,于大海笑得天真又可愛,跟老師說,卡的。
卡就是摔倒,孫老師摸摸他的頭,慈愛地說:“又淘氣了是不?”
于大海不好意思地一笑,其他同學也看著老師笑。
上課了,老師教我們讀課文:“一只小公雞,來到樹林里,伸長脖子高聲啼:小白兔,快來呀,這邊有塊青草地,青青草地多柔軟,咱倆一起來游戲……”教室里書聲瑯瑯,其樂融融。
那天只上了一節課,放學后,有人報告說凳子壞了,張小紅于大海領了幾名同學修理板凳,正好我和曹艷都是值日生,他們還把這件事記錄在班級學雷鋒做好人好事的本子上。
期末考試就要到了,我們馬上要升入三年級,老師說這次是公社通考,會有別的屯子的學校老師來監堂,考不上,只能做留級生,做降級包子。
我們不想做降級包子,誰都怕考砸了。不知從哪里學的,于大海說他可以算出誰會升級誰會降級。他拉過一個人來,握住手腕,左手右手交替向上量,每一握分別代表升級和降級,于大海一邊捏住人的胳膊往上握,一邊念念有詞:升級降級,升級降級……一直量到手肘,最后那一手所代表的,就是這個人的命運。
轉眼這種測量就風行起來,一下課,大家就開始互相測量小臂,以至于后來這種測量竟然變成了我們的課間游戲。
老師不信這個,老師自有高招,她給我們重新排了座位,每一個成績好的同學都給安排一個“趴子”,讓我們考試時好好關照他們,美其名曰學習雷鋒結對子,互幫互助。只是,班里的“趴子”實在太多,最后剩下董良和李軍,還有劉真文,實在沒有誰可以帶上他們幾個。老師無奈地嘆氣,斜睨著他們,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我的新同桌叫劉定榮,她是我們老師的鄰居,是個比我大三歲的女孩,除了學習成績差,她別的方面都不錯:懂事,能干,聽話。老師給我下了死命令,我得確保她考試及格,平安升入三年級。
劉定榮啥也不會,怎么教她她都弄不懂,好在她乖,會照葫蘆畫瓢,抄起來字還寫得挺工整,于是,老師留的作業我都讓她好好抄一遍,只希望考試時她也能抄到。
離考試還有十幾天,數學課本還沒講完,老師領我們搞突擊,大家天天拘囿在教室里做陌生的習題,只有上廁所的時候才可以報告后出去一次。
中午休息的時間忽然就短了,董良和李軍天天遲到,老師一看到他倆就板起臉,兇巴巴的連我們都膽戰心驚。
天氣干燥,暑熱難當,屋子里的灰塵蟄伏在地面,給老師檢查算術題時,腳步稍微重一些,灰塵就會飛起來,桌子上那層灰常常被我們當驗算紙,我們以手指做筆,在上面列豎式。
灰塵揚起時,老師便讓兩個人去抬水,通常,這兩人就是李軍和董良,抬水算是對他們遲到的懲罰。他倆像老師說的“大蘿卜臉不紅不白”,也不在乎,還跟同學擠眉弄眼。出門時他倆一人扛扁擔,一人拎水桶,回來時水桶掛在扁擔中間,扁擔重重壓在兩個人的肩膀上,水桶搖搖晃晃。兩人一前一后進教室,房門太窄,但通過水桶應該綽綽有余,可他倆每次都會讓水桶碰上門框,濺一身一地的水,老師氣得直咂嘴,罵他倆沒記性,完蛋貨。
進門之后,李軍和董良放下水桶,抽出扁擔,兩人抬水桶的鐵絲梁,踉蹌著走到黑板前。灑水的活一般由曹艷來做,她是班里的衛生委員,曹艷用手捧水往地上澆,水噗的一聲落到地上,濺起一片灰塵,依次灑下去,地上像畫了地圖般出現幾個黑色的板塊,灰土暫時被水鎮壓住。
等到灑向課桌附近時,矛盾又來了,水滴濺到誰的腳上,灰塵沾了誰的腳脖……曹艷都要挨罵甚至頭上挨一巴掌。老師正在檢查作業,可沒工夫管這些閑事。
曹艷委屈巴巴地灑了水,還要拿抹布擦那張放作業本的桌子,下課還要擦黑板,擦窗臺,放學后要看看值日生是否把地掃干凈,是否灑了水,每周還要檢查個人衛生,看看同學們是否洗臉洗頭剪指甲……工作任務挺嚴峻。
考試之前要檢查一遍衛生,老師說,把教室打掃干凈,大家也都洗洗臉,洗洗脖子,別一個個大脖子賽車軸,讓監考老師笑話。也不知道是怎樣認定的,那天早上,曹艷檢查過后,老師又看了一遍,她認定董良那天沒洗臉,董良支支吾吾,說是洗了,雖然只洗了一把。
老師把錯誤算在曹艷頭上,斥責她說:“你這個衛生委員怎么當的,班級里竟然還有人不洗臉,你還沒檢查出來——你倆都上前邊來,曹艷,你朝他臉上吐唾沫,讓他用唾沫洗,他媽那么懶,他家肯定是沒水了,咱給他省省水。實在不夠,全班同學都上來,每人吐他一口唾沫。”
董良豁出去的樣子,手往桌子上一撐,站起來走出去,他到前面站著早已是家常便飯,曹艷慢騰騰地挪到董良跟前,不知如何是好。
老師緊追不放,說:“快吐呀。”
于大海他們也跟著起哄,嬉笑著說:“吐呀,吐呀,快吐呀。”
曹艷臉漲得通紅,狠狠地吸了一口氣,努起嘴唇一可惜,沒吐出來。
老師瞇細眼睛,不屑地說:“完蛋玩意兒,這么點兒事也做不來,還衛生委員呢,什么也不是。”
又叫李軍,說:“你倆是親戚,你給他吐點兒唾沫,幫他洗吧。”
李軍站起來,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出來,頭低得幾乎碰到桌面上。
老師說:“瞅你那扎一千錐子也不出血的慫樣,八輩子也出息不了,你爹媽怎么養活出你們這些完蛋玩意兒?”
老師不搭理李軍,伸出食指去點董良的腦門,那食指看似毫無力道,卻點得董良身子一歪差點摔倒,我們不得不佩服老師內功了得。老師舉重若輕,用手撥弄董良的腦袋,撥得他左歪一下右歪一下,又捏他的臉,把他的腮幫子拉得老長,拉得董良齜牙咧嘴,樣子猙獰難看。董良哎呦叫了一聲,似乎很痛,老師的火更大了,說董良和李軍天天遲到,是不是家里的媽都懶死了?說他和李軍是一對笨蛋,學習什么也不是,連個人衛生都做不好,就能給班級扯后腿,給老師抹黑……老師說得唾沫星子飛濺,我們全都噤若寒蟬。曹艷陪站,縮成一團,老師罵起來,仿佛也有她一份。
董良不敢吱聲,被撕扯得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一縷光線照進屋來,穿過滿屋子的灰塵,照在那些不斷墜落的眼淚上,照得它們七彩繽紛,晶瑩艷麗。那一天,我忽然就忘記了煙塵飛舞的教室,忘記了怒容滿面的老師,只記得那些眼淚,像串串珍珠流光溢彩,發出璀璨的光芒。
老師那次發火很有震懾作用,后來幾天同學們全都老實起來,個個都表現得用功又積極。獲得的巨大成果就是,期末考試我們取得了好成績:我考了第一名,張小紅第二,劉定榮第十。董良和李軍也忽然變得懂事了——考試的時候沒來,理由是,不念了。沒有董良和李軍扯后腿,劉定榮之類同學又跟我和張小紅等結成了對子,考試那天監堂又不嚴,我們的好成績顯而易見。至于有多好我不知道,反正老師眉開眼笑,說是聽分那天要領我們去大河洗澡。
聽分那天董良和李軍又來了,雖然來得仍然很晚。老師沒搭理他倆。
快到中午的時候,老師領我們去洗澡,我膽小怕水,加上個子矮小,剛一進水就喘不上氣來,怯生生跟老師說我怕水,老師不屑一顧地撇了撇嘴,用鼻子嗤了一下。
我淡白白很無趣地被允許留在河邊,張小紅和于大海已經會“狗刨”,可以噼里啪啦在深水里游,其他同學互相牽手,最后圍成一個圈,圍在老師身邊。
董良和李軍想加入,沒人理,只好在淺水里爬,兩只腳用力拍水,也像是會“狗刨”的樣子。
老師站在河中央,同學們圍在她身邊,像“老抱子”領著一群小雞仔。大家都扯著嗓子爭著搶著跟老師說話。
我聽見老師親熱地問張小紅說:“沒考上第一,你爸怎么說的?”
張小紅說:“我爸說我完蛋貨,去年沒考過曹艷,今年又沒考過她——”
說到這里同學們的眼光大概都往我這里瞅了,我感覺有萬千的冷刀子向我飛來,陽光刺得睜不開眼。
老師呸了一口,說:“今年批卷太嚴,給你扣一分,要是我批,哼!”
“考第一”好像是我做的又一件錯事。為了表示我的懺悔,我起身,向老師靠近。
忽然,腳下一滑,我摔倒在水里。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襲來,涼涼的像軟綿綿的繩索捆住了我。我不知道我掙扎了沒有,但肯定是在往深水里滑。老師絮絮的說話聲,同學們圍在老師身邊小鳥一樣嘰嘰喳喳的歡笑聲,忽然就遠了,好像所有人都走遠了,只把我孤涼地留下。我很想追趕他們,融入他們,可是卻身不由己,不斷下沉,下沉……
老師帶領的那個快樂的小圈子沒有人注意到我,把我拽起來的是董良和李軍——我被跌跌撞撞地拖到滿是泥漿的岸上,恍惚中,我的眼前就是他倆:一個磕巴傻乎乎,一個胖臉小眼睛,我們班里最不討人喜歡的兩個大“趴子”。
那天,曹艷沒去,我是老師同學最不待見的女生。爬到岸上時,于大海哈哈大笑說:“怎么沒淹死你,讓淹死鬼把你抓走。”
說完,還做了個恐怖的鬼臉,引得老師和同學們笑聲一片。
那是二年級的最后一天,老師領我們去洗澡,可是,一起玩的就是我們三個:董良磕巴得那么厲害,卻偏要說繞口令:扁擔長,板凳寬,板凳沒有扁擔長,扁擔沒有板凳寬……
那個繞口令,他一下午都沒說完整,舌頭一直在打結。
陽光熱烈,河水清澈,老師領著她喜歡的學生快樂地戲水,我和另外的孩子坐在骯臟的河岸上賣呆,百無聊賴。
那是我和董良李軍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升入三年級時,他倆真的輟學回家,不念書了,跟他們一起輟學的還有曹艷。
責任編輯/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