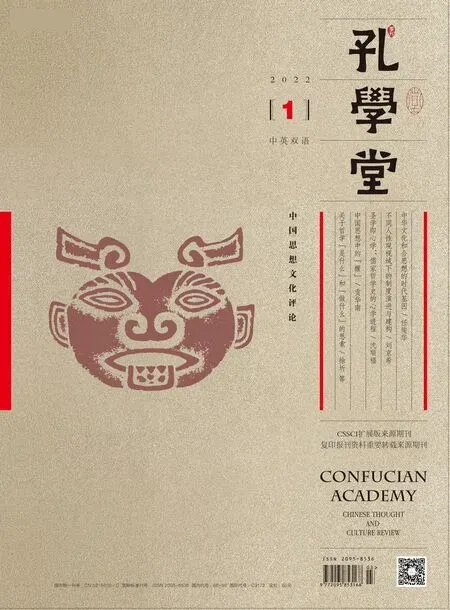兩創”①
——從經史關系的角度?
□ 任蜜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了一系列講話,其中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一觀點最早見于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他說:“要繼承和弘揚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堅持社會主義道德觀,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如果說這次講話還局限于中華傳統美德方面的話,那么隨后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之后,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談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總書記說:“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這一觀點后來也被寫入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成為指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內容。在“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那么在新時代如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核心就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其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表現也就是常與變的關系問題。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常與變的關系有著不同的表現,而經與史的關系問題無疑是其核心表現。在早期經史關系的演變過程中,孔子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對于“六經”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一、經、史溯源 [見英文版第14頁,下同]
據現有資料,“經”字始見于西周金文,其初寫作“巠”。郭沫若《釋巠》說:
《大盂鼎》“敬雝德巠”,《毛公鼎》“肇巠先王命”,均用巠為經。余意巠蓋經之初字也。觀其字形,前鼎作,后鼎作,均象織機之縱線形。從糸作之經,字之稍后起者也。《說文》分巠、經為二字。以巠屬于川部,云“巠,水脈也,從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聲。一曰水冥巠也”。說殊迂闊。①郭沫若:《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82頁。
郭氏認為巠乃經之初字,并指出《說文解字》以巠為水脈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在他看來,巠應該是織布機之縱線。按照這種解釋,《說文解字》對于經的解釋就容易理解了。《說文·糸部》說:“經,織從絲也。從糸,巠聲。”段玉裁注曰:“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②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44頁。《說文》又言:“緯,織橫絲也。從糸,韋聲。”經與緯對,分別指織布的縱絲和橫絲。段玉裁認為,織布的時候必先有縱絲,然后才有橫絲,故而先經后緯。后面的“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顯然是從引申意義上講的。但從經為縱絲的含義上,似乎推不出經之恒常的意義。東漢劉熙《釋名·釋典藝》說:“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其《釋道》又說:“俓,經也,人所經由也。”蘇輿注曰:“徑,古讀如經。本書《釋典藝》‘經,徑也。’互相訓。”③劉熙撰,畢沅疏證:《釋名疏證補》,王先謙補,祝敏徹、孫玉文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11、43頁。經、徑可以互訓,皆指道路。因為道路無所不通,又為人所必須,故可訓為常。根據古代文字譜系的研究,凡是從巠派生的字,如經、脛、徑、莖等,皆含有直義或其引申義。④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125頁。由此可見,縱絲為經之初義,直為其引申義,其余道路、常等則是其更進一步的引申義。
周代之書,以青銅器、竹、木等為介。竹簡之間以絲連接,故當時一切書寫之文均可名之為經。范文瀾說:
眾札之間,必有物聯綴,始便翻誦,或用韋,或用絲,而絲之用尤便于韋,故因絲而得經名。⑤范文瀾:《群經概論》,《范文瀾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頁。章太炎說:
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義為經,蓋彼以為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①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董婧宸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99頁。
中國古代以絲編連竹簡,就如同印度佛書以修多羅編連貝葉成書一樣。故經在起初并無特定之含義,其只不過為當時書寫憑借的編連方式。章太炎又說:“經之訓常,乃后起之義。《韓非·內外儲》首冠經名,其意殆如后之目錄,并無常義。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用繩貫穿,故謂之經。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②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諸祖耿等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42頁。正因如此,范文瀾認為,孔子之前鑄于金版的朝廷大典、圣賢大訓皆可稱經。并認為經乃金之假借,“‘金’‘經’既可通用,或孔門諸儒,以金策尊夫子手定之書,其后金字廢而經字用,遂以常道為訓,其實常道固為后起之義,即織布先經之說,亦未必得其朔也。”③范文瀾:《群經概論》,《范文瀾全集》(第1卷),第2頁。范氏以金為經之說,未必確切。然可以肯定的是,西周之前,雖無經名,但未必無其實。《尚書》說:“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尚書·五子之歌》)、“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前者為夏太康之事,說明在夏、商之時已有典冊。典即當時經也。《說文·丌部》說:“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此說“五帝之書”即“五典”。典即置于丌這種器具上的冊子,以示尊貴。在甲骨文中,典的字形即為雙手捧著冊子的樣子。《爾雅·釋言》曰:“典,經也。”鄭玄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亦云:“典,常也,經也,法也。”④孫詒讓:《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8頁。可見,典有經的含義。
以經為縱絲,故凡書寫之文均可稱經,故《老子》有《道經》《德經》之分,《墨子》有《經上》《經下》之篇,《荀子》有“道經”之引。此從廣義上釋經。
狹義上講,經僅為“六經”之專稱。“六經”之說,始見于《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天下》篇曰:“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勸學》也有關于“經”的論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可見,此時“六經”已經為儒家之專屬。后來《樂》經佚失,僅有“五經”。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經學于是成為國家之正統思想。其后,經之數目又屢有增加,遂有“七經”“九經”“十三經”等名稱。
與經字相比,史字出現得更早,在甲骨文中已經有著不同的寫法。寫法雖多,然大多從又從中,表示手有所持之義。到了西周,金文中的史字形狀雖有變化,但含義并無改變。⑤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第250—251頁。“又”表示右手。在殷商金文中,中字多書寫為旗幟形狀,表示旗幟飄揚之形。在殷周文字中,多在旗桿中間加□、○、■等形狀表示方位居于正中,屬于指事字。除了旗幟的含義外,中在甲骨文中還有表示方位、軍制之名、宮室名等含義。⑥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第1165—1166頁。可以看出,史的原始含義可能指的是右手把持旗幟的意思。
《說文解字·史部》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于“記事者也”下注曰:“《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云記言者,以記事包之也。”于“中,正也”下注曰:“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①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116頁。這里以“正”釋“中”顯然是引申義。對于許慎的說法,王國維《釋史》提出不同的看法。在王國維看來,古文的中字沒有寫作,只有到了篆文中才寫作。而且“中正無形之物德”,不能用手把持。那么史所從的“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王國維之前,吳大澂、江永等都對“中”的含義作了新的解釋,如吳大澂以“簡形”釋“中”,江永以“官府簿書”釋“中”。但在王氏看來,這些解釋都有未盡之處。通過對《周禮》《儀禮》等相關材料的考察,王氏認為“中”應為“盛算之器”。古代算、策常互通用,故“中”又為盛策之器。王國維說:“算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算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較便。”②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3頁。在此基礎上,王氏把史字“從又持中”解釋為“持書之人”。可以看出,王氏雖然對“中”作了進一步的考察,但其最后得出的結論卻與吳、江二人相差不多。對于王國維的說法,徐復觀提出了反駁,認為以“盛算之中”來解釋史字右手所持者是不能成立的。徐氏考察了甲骨文、金文、篆書中近百種史字的寫法,認為沒有一個從形,而皆為形。而中字則從,其本義為射箭靶子的中央,引申為中央之中、伯仲之仲、中正之義。“盛算之器”也是由此引申出來的。因此,徐氏斷定“盛算之器”的橢圓形當為冊字而非史字的。并推測冊字是由中字演進而來的。徐氏之所以繞了這么大一個圈子就是為了說明史字并非從中而是從口。其說:
應該來說,徐氏把史的起源與祝、卜、巫等聯系起來是正確的,但其對史“從口”的解釋卻顯得迂曲,還是從“從又從中”的角度來解釋史字更為顯豁直接。從上面的解釋來看,無論吳大澂、江永還是王國維、徐復觀都把“中”與冊、書等聯系起來。這樣看來,“中”應該是當時書寫的憑借,包含龜甲、簡冊等。“從又持中”也就是以手記錄的簡冊。記錄簡冊的人即是史官。
據徐復觀考證,在甲骨文中,史字較為少見。到了周初,“作冊”即是史,后面則出現“祝史”的連詞。④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3卷),第134—135頁。從現有文獻來看,至少在西周初年就有了專門負責記錄國家重要事情的史官,如《尚書》說:“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尚書·金滕》)、“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尚書·顧命》)此言“史乃冊,祝曰”更能證明徐復觀“史”與“祝”的關系問題。在《周禮·春官·宗伯》中,對于史官更有著詳細的劃分,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每種史官都有其具體的職責。除此之外,《周禮》的每種官職下面幾乎都有士、府、胥、徒的設置。這些都表明至少在西周時期我們已經有著豐富的史官文化。
從上可知,經、史在開始并沒有具體的指稱,它們包含的范圍都非常廣。可以說,當時一切書寫的文字都可稱作經或史。因為無論經還是史,起初都是從書寫憑借的角度來講的。故在后人看來的經書在當時有的是史官書寫的,“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玉藻》),“動為《春秋》,言為《尚書》”(《申鑒·時事》)。
二、經、史的分化與經的經典化過程 [17]
經、史一開始并無太大的區別,它們都是從書寫憑借的角度講的。隨著人類歷史的不斷發展,人類記載的不斷擴大,經和史也就逐漸開始分化開來。
未有文字之前,人類僅憑記憶或比較簡單的方式(如結繩等)記事。但隨著文字的誕生,人類政治社會的形成,就有了專門記載人類政治活動、社會風俗等各種事情的官員,即史官。史官之源,眾說紛紜,迄無定論。徐復觀認為源于古代祝、史、卜、巫之官。張爾田認為源于黃帝。其說:“中國文明開自黃帝,黃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職,以貳于太史。”①張爾田:《史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頁。黃帝之時有無史官,尚難斷定。由此來看,徐氏之說更為合理。按照《說文解字》的記載,史是記事的意思。如此看來,古代一切之書皆可歸為史。實際上,在早期中國文化學術尚未分化的時期,史官起著傳承中華文化的重任。正如徐復觀所說:“我國古代文化,由宗教轉化而為人文的展開,是通過古代史職的展開而展開的。文化的進步,是隨史官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而進步的。史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是古代文化由宗教走向人文的一道橋梁,一條通路。……欲為中國學術探本朔源,應當說一切學問皆出于史。”②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3卷),第140頁。
據史料記載,最早的史書當屬“《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曰: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已佚,其內容不得而知。對于它們,歷來有不同的解釋。如孔安國認為:“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孔安國進一步指出它們都是“上世帝王遺書”。賈逵認為,《三墳》指三皇之書,《五典》指五帝之典,《八索》指八王之法,《九丘》指九州亡國之戒。馬融認為《三墳》指天、地、人三氣,《五典》指五行,《八索》指八卦,《九丘》指九州之數。鄭玄認為《三墳》《五典》指三皇五帝之書。以上各說解釋③參見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04頁。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認為它們是上古時期記載帝王活動的典籍。從《左傳》前后文來看,這些顯然都屬于“史”。否則,楚王也不會有“良史”之嘆。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否三皇五帝之書,頗難斷定。然《詩經》《尚書》《儀禮》《周易》《春秋》等“六經”起初無疑具有史的形態。“六經”之中,以《易》形成最早。《易》包含《易經》和《易傳》兩部分,其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漢書·藝文志》說:“《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這是說,《周易》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伏羲畫八卦、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和孔子作《易傳》。伏羲屬于傳說人物,其畫八卦的說法顯然不可信,但其說六十四卦是在八卦基礎上形成的卻是有道理的。對于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史記》亦有記載:“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周本紀》)、“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日者列傳》)。六十四卦是否為周文王所作也無充分的證據,但《易經》至少在西周初年已經形成。從現有資料來看,《周易》的形成受到了史官文化的影響,或者說其作者本身即是史官。①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1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12頁。
《詩經》是我國古代的詩歌總集,現存三百〇五篇。其由《風》《雅》《頌》三部分構成。古代有采詩之官,《詩經》就是由采詩之官獻給當時朝廷的。《漢書·食貨志上》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說苑·修文》說:“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岳,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因此,《詩經》的作者也多不可考,不過其由采詩之官獻之朝廷,然后由太師進行甄選、選編而成則是沒有疑問的。太師、太傅與太保并為三公,雖非史官,但與史官有著密切關系。《大戴禮記·保傅》說:“天子不論先圣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禮,不博古之典傳,不閑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先圣王之德”“博古之典傳”都屬史之內容。
《尚書》是古代政治文獻的合集。其時代始于堯,終于秦。其內容包含典、謨、誥、誓等。所謂“尚”就是“上古”的意思。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說:“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②陸德明:《經典釋文》,張一弓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頁。孔穎達《尚書正義》也說:“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③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頁。因此,“尚書”就是上古文獻的意思。《尚書》包含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今文《尚書》指經秦火之后伏生所傳之書,有二十九篇。古文《尚書》則指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之書,有五十八篇。現存的古文《尚書》,一般認為是后世偽作。從內容看,《尚書》顯然為史官所作。此點《禮記·玉藻》《漢書·六藝略》已經明言。
《禮》包含《儀禮》《禮記》《周禮》,后世合稱“三禮”。其中《儀禮》為今文經學,《周禮》為古文經學。《禮記》則內容駁雜,有今文,也有古文。《儀禮》在漢代又稱《士禮》,現存十七篇。其之所以稱作《士禮》,蓋因其首篇為《士冠禮》。《周禮》又稱《周官》,王莽時劉歆改《周官》為《周禮》,凡六篇,亡《冬官》一篇,后人以《考工記》補之。對于《周禮》之年代,歷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現在一般認為其是戰國時人所作。《禮記》則有《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之分。《大戴禮記》為戴德所編,《小戴禮記》為戴圣所編。前者八十五篇,后者四十九篇。現存十三經中的是《小戴禮記》。據《漢書·藝文志》,當時“禮”類文獻有“《記》百三十一篇”。對于大、小戴《禮記》的關系,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德從《古禮記》二百多篇中刪取八十五篇為《大戴禮記》,戴圣又從《大戴禮記》的基礎上刪取四十九篇為《小戴禮記》;一種不信小戴刪大戴之說,認為二書皆從多種《古禮記》刪取而成。由于現存《大戴禮記》只存三十九篇,其余諸篇已經佚失,我們無從斷定二戴《禮記》關系如何。不過二戴《禮記》大都輯自河間獻王、孔壁等發現的《古禮記》則無疑問。“三禮”之中,《儀禮》成書最早,其作者尚無定論。從其內容來看,其當屬《大戴禮記·保傅》所記“太師”職責之內。因此,也與史官有著密切關系。
“六經”之中,《春秋》本即魯國史書。春秋時期,各國皆有史書,《墨子》所說“百國《春秋》”是也。因此,不獨魯國有史,其余各國皆有史書。然名稱或有不同,如《孟子》所說“晉之《乘》”“楚之《梼杌》”。從現有材料來看,魯國《春秋》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春秋公羊傳·莊公七年》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論衡·藝增》說:“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④王充:《藝增》,黃暉:《論衡校釋》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1頁。所謂“不修《春秋》”,即未經孔子刪定過的《春秋》。《左傳·昭公二年》也記載了晉侯派韓宣子使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春秋》之所得名,亦因此編年史性質。杜預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①孔穎達:《春秋左氏傳序》,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第3—6頁。
從上可知,“六經”原出于史。此點前人多有論述。如隋王通說:“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②王通:《王道》,《文中子中說》,阮逸注,秦躍宇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2頁。明王陽明說:“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五經亦只是史。”③王守仁:《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卷一,吳光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頁。明王世貞也說:“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④王世貞:《藝苑卮言校注》卷一,羅仲鼎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第32頁。這一思想后來為清代章學誠發揚光大。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⑤章學誠:《易教上》,《文史通義》,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頁。章氏此說影響甚大,幾乎成為史學界之共識。
從文獻內容上看,一切著述都可當作史。此史乃廣義,非狹義上的歷史學。但如果僅僅把“六經”當作史,即把“六經”當作當時史實的記載,則會只見事不見理,只見變不見常。這樣經的地位和意義就無法凸顯出來。經之所以能夠稱作經,就在于其能突破史的束縛,看到歷史變化中的不變之道。但經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經典化過程。
“六經”的具體作者雖然不能確定,但其主體部分形成于西周至春秋時期。其形成以后,也就開始了經典化的過程。陳來說:“中國文化的第一次經典形成的過程或原始經典的形成,是在西周到春秋。在這一歷史時期,《詩》《書》的文獻體系和《詩》《書》的經典地位漸漸形成和確定。特別是《詩》,在西周春秋的禮樂文化體系和禮樂文明制度中更享有明確的突出地位。”⑥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69頁。從西周到春秋時期,是《詩》《書》等經典確立的時期。這種經典確立的過程,并非靠外在權力實現的,而是靠經典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和知識階層的反復引證逐步實現的。陳來說:“西周春秋的經典化過程,不是靠政治權威來宣布的,它一方面與西周春秋的朝聘制度和禮儀文化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如《詩》),另一方面是在知識階層(包含各類士大夫)的反復引證中逐步集中和實現的。”⑦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第170頁。這一點可以在《左傳》和《國語》等文獻中得到驗證。
對于春秋時期的征引“六經”的情況,前人已有論及。如顧棟高說:“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言《易》十有七。”⑧顧棟高輯:《春秋大事表》,吳樹評、李解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549頁。對此,顧氏還制作了《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加以說明。對于《左傳》中的引《詩》《書》《易》的情況,我們不能詳列。下面僅舉幾個例子以展現其經典化的過程。我們先來看引《詩》的情況。《左傳·僖公十九年》說: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后動。”
引《詩》出自《詩經·大雅·思齊》。意思是說,周文王能夠修德,以成為妻子、兄弟的示范,并推到治理國家上。宋國圍攻曹國,以討伐不服。子魚以周文王征討崇侯虎的故事來說明以德服人的重要性。其引用《詩》也是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
《左傳·文公三年》說: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引《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出自《詩經·國風·采蘩》;“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出自《詩經·大雅·烝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出自《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這段主要記載了秦穆公攻打晉國以雪崤山之恥的事情。《左傳》作者認為秦穆公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一方面在于自己能夠知人善任,另一方面在于孟明、子桑等大臣能夠夙夜在公,知人舉善。引用《詩經》主要為了說明作者對于秦穆公、孟明和子桑的評價。
對于《尚書》,《左傳》也多有引用。如《左傳·僖公五年》說: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丑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這是對晉國假道于虞而伐虢的記載。虞國宮之奇勸說虞公,虞、虢兩國唇亡齒寒,不要假道于晉。在勸說過程中,宮之奇三引《尚書》以說明自己的觀點。所引《尚書》分別出自古文《尚書·周書》的《蔡仲之命》《君陳》《旅獒》。
《左傳·成公二年》說: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楚莊王欲討伐陳國,以納夏姬。申公巫臣以為此事不可。在他看來,討伐諸侯是為了討罪,而不是為了貪色。貪色是不好的,必然帶來懲罰。并引用《尚書·康誥》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楚莊王聽了之后,也就停止討伐陳國了。
在《左傳》中,我們也能看到其對《周易》的征引。如《左傳·襄公九年》說: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死于東宮。在此之前,她曾占筮,得《艮》之《隨》。史官認為,《隨》乃出走之意,因此勸說穆姜迅速出走。穆姜則沒有聽從史官的建議,認為沒必要出走,并用《周易》隨卦卦辭進行解釋。在穆姜看來,隨卦所說的“元亨利貞”是對有德性的人講的,她自己品德惡劣,因此必然死于此地。
《左傳·昭公五年》說: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后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穆子出生的時候,其父莊叔以《周易》卜筮,得《明夷》初九爻。明夷卦卦象為離下坤上,初九為變爻,故曰“之《謙》”。其初九爻辭為:“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卜者楚丘結合《明夷》初九爻辭對此作了解釋,認為穆子不能得其善終。
除了《詩》《書》《易》外,《左傳》對于《春秋》《禮》《樂》也有征引或論述。《左傳》本身就是對《春秋》經的注解,因此,其對于《春秋》本身的引用是很少的。即便如此,其也數次提到了《春秋》,如《成公十四年》說:“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說:“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這兩條都涉及了《春秋》的基本條例。除此之外,《左傳》還記載了韓宣子出使魯國,看到“魯《春秋》”的情況。《昭公二年》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對于《儀禮》,《左傳》雖然沒有引證,但其卻有大量涉及“禮”的內容。如: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隱公五年》)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隱公六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隱公八年》)
秋,公子翚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于 ,非禮也。(《桓公三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桓公九年》)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公十五年》)
這些都以是否合“禮”作為判斷事情是否正當的依據。此外,《左傳》對禮的作用還有詳細的論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隱公十一年》)、“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昭公二十六年》)。可以看出,禮在國家政治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其是國之大經、民之大義,是一切秩序運作的依據。因此,它可以與天地相并。至于“樂”,在《左傳》中是包含在廣義的“禮”中的,如《桓公九年》說:“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襄公十年》說:“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丐,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由上可知,在春秋時期,以《詩》《書》為代表的“六經”已經成為士大夫官僚階層普遍引用的經典。士大夫官僚階層之所以對于“六經”如此重視和熟悉,在于它們從小就受到了此類教育。《國語·楚語上》說: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申叔所提到的《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皆是當時士大夫官僚階層培養子弟所用到的類似教材的文獻。其中多有與“六經”相關者,如《春秋》《詩》《禮》《樂》等。雖然沒有提到《尚書》,但應該也包含類似的文獻,如“訓典”等。處于蠻夷之地的楚國當時的貴族教育已經如此,中原各國的貴族教育可想而知。除了上面晉國韓宣子所說的“《易》象和魯《春秋》”外,《國語》還有“羊舌肸習于《春秋》”的記載。
春秋時期,士大夫官僚階層對于“六經”的征引表明“六經”在當時已有較高的權威性,這也是他們之所以引用“六經”說明自己觀點的原因所在。而這些又與當時士大夫官僚階層的教育有關。這也是當時“六經”經典化一個重要的動因。陳來指出:“經典的神圣權威性不是先驗的決定的,而是在共同體的文化生活實踐中歷史地實現的,是在人與人、人與歷史的關系中建立起來的。在中國,更是在文化交往、語言交往和禮儀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一個經典之成為經典,在且僅在于群體之人皆視其為神圣的、有權威的、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經典的性質并非取決于文本的本身,而取決于它在一共同體中實際被使用、被對待的角色和作用。我們從‘引證’來了解春秋時代對經典的需求,和詩書在春秋文化的地位,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①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第216頁。當時士大夫官僚階層對于“六經”的經典化過程雖然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僅限于士大夫官僚階層和政治活動過程中,其影響范圍相當有限的。另外,他們對于“六經”的征引和解釋還是比較零散的,并沒有系統性。因此,如何對“六經”進行系統闡釋使其在當時社會煥發新的生命力、如何把“六經”教育普及到廣大平民百姓當中使其在當時社會有廣泛的影響,就成為春秋后期“六經”經典化過程中面臨的兩大任務。這兩大任務是由孔子完成的。
三、孔子對于“六經”的整理、創新及史觀思想 [22]
在先秦時期,經有六種,被稱作“六經”或“六藝”。司馬遷說:“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在郭店楚簡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關于“六經”的相關記載,如《性自命出》就提到了《詩》《書》《禮》《樂》:“《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于人。《詩》有為為之也;《書》有為言之也;《禮》《樂》有為舉之也。”《六德》則對“六經”都有提及:“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語叢(一)》對“六經”的宗旨還進行了概括:“《禮》,交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書》……者也。”“《詩》,所以會古今之詩者也者。”“《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據《莊子》所說,在孔子之前就已經有“六經”的說法了,但《莊子》頗具寓言性質,其顯然不能作為文獻依據。不過至少在孔子弟子的時候,“六經”在當時已經比較流行是可以斷定的。
對于孔子與“六經”關系,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后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這里對于孔子編定“六經”的過程作了詳細的論述。孔子所處的時代,周王朝衰微,天下混亂,禮壞樂崩。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想要恢復三代之治,因此對“六經”要重新編訂。對于《書》,以堯、舜為始,訖于秦穆公。對于禮,則在損益夏、商之禮而從周。對于《樂》,則使其音正,而歌唱之《詩》各得其所。對于《詩》,則從三千多篇中選取三百〇五篇,以使其符于禮義、合于《雅》《頌》之音。對于《易》,則序《彖》《系》等傳以明其義。對于《春秋》,則明其志。如此而“備王道,成六藝”。
對于司馬遷所說,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有著不同的看法,前者認為“六經”乃孔子所作,后者認為“六經”為孔子所編定。從現有材料來看,“六經”為孔子所作說顯然不確,因為“六經”在孔子之前顯然已經存在。至于“六經”為孔子編定的說法,雖不必盡然,但有其合理之處。
對于孔子刪《詩》,歷來有不同說法。有贊同者,王充、班固、歐陽修等人持此觀點。如王充說:“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①王充:《正說》,黃暉:《論衡校釋》卷二十八,第1129頁。班固說:“虙羲畫卦,書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漢書·敘傳》)有懷疑者,孔穎達、朱彝尊、趙翼、崔述等人是其代表。如孔穎達說:“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②鄭玄:《詩譜序》,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頁。應該來說,刪《詩》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可信的。因為在現存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未被《詩經》收入的逸《詩》。別的不說,在《論語》中就有,如《子罕》說:“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在《左傳》中也存在一些不見于《詩經》中的逸《詩》,如《莊公二十二年》說:“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成公九年》說“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等。這些《詩》篇可能即是孔子所刪《詩》的一部分。
對于孔子刪《書》,《尚書緯》說:“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這是說孔子從三千多篇的古書中,選取一百二十篇作為后世之法。其中一百零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除緯書外,孔子刪《書》之說未見于其他文獻。因此,此說頗為可疑。不過“百二《尚書》”的說法則于史有征。《漢書·儒林傳》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后樊并謀反,乃黜其書。”這里明確指出百二篇乃張霸根據《尚書》二十九篇、《左傳》、《書序》等而作。他把《尚書》二十九篇分成數十,然后又采取《左傳》《書序》作為首尾,這樣就湊成百二之數。漢成帝時,求知古文《尚書》之人,張霸以“百二”應征。成帝以所藏中秘本校之,二書完全不同。因此此事敗露。“百二《尚書》”為張霸偽造,故不足信。但漢代有著“百篇《尚書》”的記載。班固說:“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漢書·藝文志》)《尚書》遭遇秦朝禁毀,伏生藏之墻壁,后來僅存二十九篇。后來經河間獻王獻書、魯恭王壞孔子壁所得,《尚書》文獻又有所增加。因此,到了劉向、歆父子整理中秘文獻的時候,又有“《周書》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的記載。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也。”①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6頁。這說明孔子從三千多篇中刪《書》的說法雖不可靠,但從百篇中刪《書》的記載卻是合理的。
其他《易》《春秋》《禮》等也經過了孔子的編訂或解釋。對于孔子與《易》的關系,除了司馬遷所說外,《漢書·藝文志》也有孔子作《易傳》的說法:“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的說法是孟子,其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到了漢代,董仲舒、司馬遷都有類似的說法。如董仲舒說:“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瑞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后圣。”(《春秋繁露·俞序》)司馬遷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記·孔子世家》)《春秋》顯然非孔子所作,此點前已辨之。對此,今古文經學有著不同的看法,如今文經學認為“孔子作《春秋》”乃是做成一書,非抄錄一過,是萬世作經,非一代作史。古文經學則認為“作”乃“為”義,此是說孔子因古史而成《春秋》也。兩相比較,后者較為合理。對于《儀禮》,亦有認為是孔子所刪定者。皮錫瑞說:“《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并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②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9—20頁。
如果孔子僅僅局限于對“六經”編訂或解釋的工作上,那么孔子對于“六經”的意義就顯得沒有那么重要了。其實,孔子之所以對“六經”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就在于其在“六經”具體事實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出了“六經”之恒常之道(即“義”)。這一點孟子已經指出: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
在文字表達和歷史記載上,孔子所作《春秋》與其他諸國之史書并無太大區別。孔子對于《春秋》的偉大意義就在于發明了其中之“義”。司馬遷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這里明確地記載了孔子根據當時的史書作《春秋》以明其道。《春秋》與一般的史書不同,其不僅僅記錄史事,而且還要表明孔子的“貶損之義”。
不獨《春秋》如此,孔子對于《詩》《書》《易》等其他諸經也著重探討其背后之“義”。對于《詩》,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 》篇。“思”為發語詞,本無意義。孔子在這里對《詩經》斷章取義,進行了創造性轉化,把“思”解讀為“思想”,并用以概括整部《詩經》的宗旨。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在新發現的上博簡《孔子詩論》中看到孔子與弟子討論《詩》義的記載。如其說:“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見歌也……”“則《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蓋曰動而皆賢于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于禮。……”可以看出,孔子對于《詩》主要看重其所蘊含的大義,如通過《葛覃》以觀民性,通過《關雎》以知禮等。對于《尚書》亦是如此。《孔叢子·論書》說:“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勛焉;于《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范》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于《尚書》也是觀其大義,而非囿于其所記載的具體事情,如于《帝典》以觀堯、舜之圣,于《皋陶謨》以觀政,于《五誥》以觀仁,等等。對于《周易》,孔子更是作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把《易經》從卜筮之書解釋成哲理之書。這一點帛書《易傳·要》有著明確記載: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而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與祝卜不同,孔子對于《周易》注重其“德義”思想。僅能幽贊神明而不通曉筮數則為巫師之道,僅能通曉筮數而不能達至德義則為史官之道。對于巫師、史官之道,孔子雖然喜好但并不認同。孔子之所以能夠超越巫師、史官之道就在于他不僅看到《周易》的幽贊神明、占卜筮數的一面,而且能夠看到關乎德義的一面。這也是其異于巫師、史官的根本之處。故于《周易》,孔子特別注重其中的“《易》道”“《易》義”:“故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兇,順于天地之心,此謂《易》道。”(帛書《易傳·要》)“《易》之義誶陰與陽。”(帛書《衷》)這一點在《論語》中也有反映:“南人有言:‘人而不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孔子于《周易》非徒注重其占筮功能,而更多地關注其背后隱藏的具有道德性的價值意義。
正是發掘了“六經”之恒常之道(“義”),才能使“六經”從史官檔案中脫離出來,從具體史料中脫離出來,具有恒常之道的性質。即“六經”非徒史料之堆集,而有變中之常。正如錢穆所言:“《六經》既為其時之衙門檔案,故遂綜之曰王官之學。惟孔子則研求此種檔案而深思獨見,有以發揮其所涵蘊之義理,宣揚其大道,自成一家之言。后世推尊孔子,乃推尊及其所研習,而崇其名曰‘經’。”①錢穆:《孔子與論語》,《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第238頁。正唯如此,孔子在中國經學史上才有不可替代之地位。孔子所開創的這種經學傳統,也為乃后之儒家所繼承、所發揚。馮友蘭說孔子的“述而不作”,“實乃以述為作也。此種精神,此種傾向,傳之于后來儒家,孟子、荀子及所謂七十子后學,大家努力于以述為作,方構成儒家思想之整個系統。所以《易》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系辭》《文言》等,則儒家所作,而《易》在思想史上的價值,亦即在《系辭》《文言》等。《春秋》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公羊傳》等則是儒家所作,而《春秋》在思想史上的價值,亦即在《公羊傳》等。《儀禮》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禮記》則儒家所作,而《禮記》在思想史上的價值,則又遠在《儀禮》之上。……由此言之,后來之以孔子為先圣兼先師,即所謂至圣先師,亦非無因。因為若使《周易》離開《系辭》《文言》等,不過是卜筮之書;《春秋》離開《公羊傳》等,不過是‘斷爛朝報’;《儀禮》離開《禮記》,不過是一禮單;此等書即不能有其在二千年間所已有之影響。”②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7—58頁。
孔子之所以能夠對“六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變化的歷史事實中抉發其恒常之道,與其史官思想有著密切關系。表面看來,孔子似乎是守舊的復古主義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論語·述而》)。因此,孔子對于以周禮為代表的古代文化表現出了相當的信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但實際上,孔子所說的周文化,已非舊有的周文化,而是經過孔子理解的理想化的周文化。因此,孔子常常對周文化作出新的解釋以使其更好地適應當時的社會形勢,如其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孔子認為禮的本質并不僅僅在于其外在形式,而主要在于其內在價值。如果內在價值消失了,其外在形式則不足以表現禮的本質。當孔子弟子林放問“禮之本”的時候,孔子非常稱贊他的提問,并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因此,孔子所說的周禮是在損益夏、殷之禮的基礎上形成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也是孔子推崇周禮的原因所在。在孔子看來,周禮之所以高于夏、殷之禮就在于他采取了二者之長。孔子并非讓大家固守周禮,其后世繼承周禮也要損益周禮。這說明孔子并非守舊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是與時俱進的文化創新主義者,這也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除了對“六經”進行系統闡釋使其在當時社會煥發新的生命力外,孔子對于“六經”的貢獻還在于使“六經”教育普及廣大平民百姓使其在當時社會產生廣泛影響。這一點前人多有論述,如馮友蘭說:“故以六藝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眾化,實始于孔子。……故大規模招學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后則各家蜂起,竟聚生徒,然此風氣實孔子開之。”③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第45—46頁。正是因為孔子完成了當時“六經”所面臨的兩大任務,“六經”的經典化過程才真正實現,中國文化也由此煥發出新的生機。
四、當代啟示 [26]
從上可知,經、史關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在起初,經、史都是從書寫憑借的角度講的,并沒有太大的區別。隨著歷史的發展,經、史逐漸發生了分化,經演變成了具有經典性的著作,而史則成為記載具體歷史事件的載體。二者的地位隨著孔子對“六經”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變得越來越懸殊了。孔子之后,“六經”雖然沒有在政治上取得獨尊的地位,但其對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且一直持續到漢代。到了漢代,董仲舒通過對《春秋》公羊學理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回應了當時時代所面臨的擺脫秦制、建立漢制的問題,使得儒家經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從此之后,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莫不以經學為尊,盡管其內容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表現。在大一統政治背景下,經學取得了獨尊地位,同時就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要以經學為指導并受其制約,史學也不例外。因此,大一統政治背景下的史學創新都是以經學為指導的。
經學與史學的關系實質就是常與變的關系。經代表著常道,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以貫之的內容,是普遍的、抽象的。史代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具體事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是個別的、具體的。經學的發展離不開史學,因為普遍的、抽象的常道必須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同樣,史學的發展也離不開經學的指導,因為脫離經學而書寫的史學必定是散亂的、零散的記載,這樣的史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經學之所以對史學有著指導意義,就在于從價值上肯定了中國王朝歷史存在的正統性。而正統歷史的書寫首先就是以正統性為基礎的,這在歷史上分裂的王朝時代表現得尤為明顯。《春秋》公羊學之所以能夠獲得大一統政治統治者的肯定,就在于其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這也是中華文明雖歷經千難萬苦、戰爭紛亂而終能走向統一的內在動力。正是因為大一統理論的存在,中華文明才能在歷史的演進中不斷保持其統一性而綿延不絕、延續至今。
在新時代,經學和史學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封建王朝體制解體之后,經學依附的物質載體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經學所體現的在過去看來具有普遍性的常道也變得不具有普遍性了,其本身也被分化解構到哲學、史學、文學等現代學科中了。而史學也擺脫了“尊經衛道”和鼓吹王侯將相、一家一姓的王朝歷史的書寫方式,變為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新史學。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經學,還是史學都面臨著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問題。那么如何實現它們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呢?具體來說,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與當代中國現實、當今時代條件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說:“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①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習總書記的這段話為古代的經、史之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指明了方向。這就要求我們在對待古代經、史之學的問題上,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使其適應現實的時代和文化發展要求。
- 孔學堂的其它文章
- Call for Papers
- On Wang Yangming’s View of the‘Unity of Activity and Tranquility’:A Monistic and Two-Level Conception of Effort Devoted to the Original Substance?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 The Idea of ‘Maintaining Fullness’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Governance
- The Mission of Wisdom:A Reflection on What Philosophy Is and What Philosophy Can Do
- The Philosophy of the Sages Is the Study of Mi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Mind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