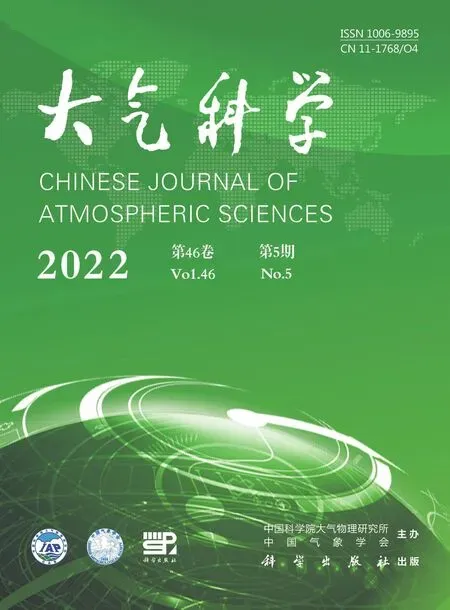青藏高原深對流及其在對流層—平流層物質輸送中作用的研究進展
陳權亮 高國路 李揚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大氣科學學院/高原大氣與環境四川省重點實驗室, 成都610225
2 四川省雅安市氣象局, 雅安625000
1 引言
深對流在對流層向平流層的物質輸送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深對流中強烈的上升運動能夠在數小時內將水汽和污染物從邊界層和對流層低層輸送到十幾公里以上的上對流層和下平流層(UTLS)(Dessler and Sherwood, 2004)。進入平流層的水汽和氣溶膠又對輻射平衡、平流層臭氧恢復產生顯著的影響,通過正向或負向的輻射強迫控制著全球變暖的趨勢(Kirk-Davidoff et al., 1999)。對流層—平流層物質交換(STE)對全球氣候變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國內外的一些學者對此已做過一系列綜述(Holton et al., 1995; Shepherd, 2002; 楊健和呂達仁,2003; 陳洪濱等, 2006; 呂達仁等, 2008)。
近年來,青藏高原和亞洲季風區被認為是對流層向平流層物質輸送(TST)過程中除熱帶地區以外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窗 口(周 秀 驥, 1995; Fu et al.,2006a; Park et al., 2009)。卞建春等(2011)評述了這一重要的進展,并強調了亞洲夏季風在對流層向平流層物質輸送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衛星觀測,發現在青藏高原上空存在明顯的臭氧低谷(周秀驥, 1995; Bian, 2009)、水汽極值中心(Gettelman et al., 2004; James et al., 2008)以 及 氣 溶 膠 層(Vernier et al., 2011, 2015)。卞 建 春 等(2013)綜述了這些重要的觀測事實,并對比了亞洲季風區和北美季風區在UTLS 大氣成分、卷云以及深對流活動特征等方面的差異,討論了南亞高壓對UTLS大氣成分分布的重要作用。Bian et al.(2020)綜述了亞洲季風區近地面污染物向UTLS 輸送的物理機制,以及污染物傳輸造成的區域和全球氣候效應。
上述研究均指出亞洲季風區UTLS 存在的臭氧低谷、水汽極值中心和氣溶膠層與青藏高原及其周邊的深對流有密切的關系,近年來關于青藏高原及其周邊的深對流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進展,這些研究有助于進一步理解深對流的物質輸送作用,以及青藏高原對全球大氣和氣候的調制作用。本文對此進行了回顧,并對一些科學問題進行了討論和展望。具體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簡述了對流層向平流層物質輸送的主要途徑,并且列舉了近年來青藏高原地區作為對流層向平流層物質輸送窗口的觀測事實。第三節概述了目前深對流觀測的主要手段,總結了通過衛星識別深對流的兩類主要方法。第四節描述了深對流向平流層物質輸送的物理過程,討論了對流層頂過渡層在傳輸過程中的影響。第五節對比了青藏高原、亞洲季風區和熱帶地區深對流的活動特征差異,并從云微物理、對流層頂最冷點溫度和環境場相對濕度的角度,討論了影響深對流輸送過程的主要因素。第六節對本文的主要內容做了小結和展望。
2 對流層向平流層的物質輸送與重要的輸送窗口——青藏高原
2.1 對流層向平流層物質輸送的主要途徑
平流層的水汽和氣溶膠能夠為平流層和對流層提 供 顯 著 的 輻 射 強 迫(de F. Forster and Shine,2002),影響平流層的臭氧恢復和全球的變暖趨勢(Kirk-Davidoff et al., 1999; Solomon, 2010, 2011)。跨對流層頂的水汽傳輸貢獻了平流層水汽約50%的來源,另外50%則主要來自甲烷的氧化反應(Oltmans and Hofmann, 1995)。平流層的氣溶膠也來源于對流層向平流層的輸送(Etheridge et al.,1998)。這種對流層向平流層的物質輸送在全球尺度上主要受Brewer-Dobson 經向環流(Brewer,1949; Dobson, 1956)的影響。Holton et al.(1995)指出這種Brewer-Dobson 環流是由于行星波和重力波向上傳播到平流層以上高度破碎后,產生動量通量的輻合輻散,形成一種全球尺度的“流體動力抽吸泵”。因此,這種全球尺度的經向環流也被稱作“波驅動環流”。
在熱帶外的中緯度地區,天氣尺度系統也對TST 過程有重要影響。這種輸送過程主要是一種沿等熵面的絕熱過程,通過渦動來完成。例如:在穩定的急流軸和高空鋒區附近(Kelly et al., 1990)、高空槽及切斷低壓的發展過程(Wirth, 1995)中都會發生對流層向平流層的物質輸送。但這種物質輸送是相互的,例如:伴隨著上對流層氣旋生成及大尺度斜壓波的“對流層頂折疊”也是導致平流層空氣進入對流層的重要過程(Hoskins et al., 1985)。
與行星尺度和天氣尺度的TST 過程相比,中小尺度的深對流是另外一種重要的平流層—對流層物質交換的系統(Poulida et al., 1996; Fischer et al.,2003)。在時間尺度上,深對流能夠在數小時內將對流層低層的物質輸送到UTLS,而天氣尺度和行星尺度系統通過斜壓和渦動的傳輸方式,使得這種過程往往需要數天的時間。在空間尺度上,深對流的傳輸則更具有局地性,準確的理解深對流的物質輸送,對于認識平流層水汽和氣溶膠的緯向分布不均有重要意義(Dessler, 2002)。從傳輸方式而言,深對流提供了一種更為直接的傳輸路徑,近地面的水汽和氣溶膠能夠通過對流的絕熱上升過程被快速抬升到UTLS,這有效提高了邊界層水汽和氣溶膠向上的傳輸效率。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認為熱帶平流層緯向風的準兩年周期振蕩能夠通過其次級環流影響TST 過程(Giorgetta and Bengtsson, 1999)。Wang et al.(2009)認為重力波在對流層頂的破碎,以及不穩定切變引起的湍流混合過程,也會引起跨對流層頂等熵面的物質輸送。另外,上對流層是洲際航空運輸的主要通道,飛機尾氣的排放對于UTLS 的化學成分也有一定影響(陳洪濱等, 2006)。
2.2 UTLS 水汽、氣溶膠和臭氧在青藏高原的極值區
早在20 世紀90 年代,周秀驥(1995)使用TOMS 衛星資料發現,在6~9 月的青藏高原上空存在一個明顯的臭氧總量低值區,并稱之為青藏高原臭氧低值中心。周秀驥(1995)推測青藏高原周圍數百公里范圍內的低空污染物可能在夏季向青藏高原輻合,然后上升到平流層下部,對流層低濃度臭氧向平流層的輸送以及低空污染物在平流層引起的物理化學過程,可能是引起夏季青藏高原臭氧總量異常降低的重要原因。Tian et al.(2008)使用TOMS 和SAGEⅡ衛星觀測數據以及數值模擬對青藏高原臭氧的進一步研究發現,對流傳輸過程相比化學過程對青藏高原臭氧低谷的形成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Park et al.(2007)使用Aura MLS 數據研究了北半球夏季的一氧化碳和臭氧分布,結果發現在南亞反氣旋區域存在一氧化碳的極大值和臭氧的極小值,其分布與深對流的強度和頻率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Park et al.(2008)進一步指出南亞反氣旋內的污染物主要是來自近地面的傳輸。反氣旋內的污染物濃度變化也被認為是近地面污染物排放留下的“指 紋”(Li et al., 2005; Randel and Park, 2006;Park et al., 2009)。Randel et al.(2010)指出亞洲季風區向平流層輸送的大氣污染總量甚至強于整個熱帶地區。Yu et al.(2017)使用模式模擬的結果也表明亞洲大量增長的人為氣溶膠,通過季風對流的快速傳輸對整個北半球下平流層的年平均氣溶膠貢獻,達到了顯著的15%,這一貢獻相當于2000年至2015 年火山噴發氣溶膠的總量。
Gettelman et al.(2004)通過衛星觀測發現了UTLS 水汽的極大值中心更多的位于青藏高原而不是南亞地區。James et al.(2008)也發現100 hPa水汽的大值中心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地區。Sun et al.(2017)發現這種水汽的大值區又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東南側。Fu et al.(2006a)使用WACCM模式對100 hPa 大值中心的CO 和水汽進行后向軌跡模擬的結果表明,青藏高原及其南坡深對流對平流層水汽和CO 的輸送作用要大于南亞季風區。
3 深對流的觀測與識別方法
3.1 深對流活動主要的觀測途徑
TRMM 衛星從星載測雨雷達的角度,最早提供了一個觀測深對流的視角(Simpson et al.,1996)。盡管極軌衛星觀測到深對流的頻率較低,但是仍然為研究熱帶和副熱帶地區深對流的結構、頻率和時空分布提供重要的觀測事實(Liu and Zipser, 2005; Liu et al., 2007; 劉鵬等, 2012)。TRMM衛星從1997 年發射到2015 年退役運行了長達17 年,較長的時間序列也使得研究深對流的年際變化以及對氣候變化的響應成為可能(Zipser et al.,2006)。2014 年,美國宇航局和日本宇宙探索管理局在TRMM 衛星的基礎上成功發射了GPM 衛星(Hou et al., 2014)。GPM 衛星作為TRMM 衛星的升級版,一方面將觀測的范圍從副熱帶和熱帶地區擴展到了中高緯度,這為研究中高緯度的深對流提供了重要幫助(Gao et al., 2019),另一方面,由于GPM 衛星將測雨雷達增加到了雙頻,提升了對降水粒子滴譜的反演能力,從而有效提升了對深對流云微物理結構的描述和理解(Chen et al.,2020a, 2020b)。
A-train 衛星編隊為理解深對流與環境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另外一個更為全面的視角。Atrain 系列衛星在一個相近的太陽同步軌道上,以大約15 min 的間隔相繼掃描同一地區(L’ Ecuyer and Jiang, 2010),并分別觀測大氣的云物理結構、溫濕的垂直廓線,水汽、氣溶膠和臭氧等痕量氣體的時空分布(Stephens et al., 2002)。CloudSat 和CAL?PSO 搭載的云雷達和激光雷達與TRMM 和GPM 搭載的測雨雷達相比有更短的波長,可以更好地識別云滴粒子和深對流云上部尺寸較小的冰晶粒子,對于深對流的上沖云頂和云砧的細微結構有更準確的分辨能力(Stephens et al., 2008)。CloudSat/CAL?PSO 與Aqua、Aura 的結合,使深對流的云觀測與大氣環境的衛星探測融為一個整體,為研究深對流向平流層的物質輸送作用,以及深對流與周圍環境的夾卷和溢出過程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觀測手段(Savtchenko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19)。
除了星載雷達觀測以外,一些空基的飛行試驗也為理解深對流的物理細節提供了重要幫助。例如,1996 年6~7 月在美國科羅拉多開展的對流層—平流層試驗和深對流領域項目(Dye et al., 2000),以及在2005~2006 年期間連續開展的三次觀測試驗:2005 年1~2 月在巴西阿納薩圖巴的熱帶對流、卷 云 和 氮 氧 化 物 試 驗(Konopka et al., 2007),2005 年11~12 月在澳大利亞達爾文的上對流層—下平流層與平流層氣候聯系的熱帶試驗(Vaughan et al., 2008),以及2006 年8 月在非洲布基納法索開展的非洲季風綜合分析試驗(Cairo et al., 2010)。這些試驗通過大量使用飛機進行繞云和穿云飛行,對深對流云內的冰水粒子和痕量氣體分布以及溫濕結構都進行了更為準確的觀測。
由于深對流對物質的輸送作用,一些痕量氣體的濃度變化也被用作深對流活動的示蹤劑。例如:Dessler(2002)使用臭氧和CO 量化地計算了深對流的顯著溢出能夠發生在高達380 K(約17 km)的高度。Hanisco et al.(2007)通過觀測 水汽和HDO 在平流層的變化認為熱帶外的深對流對平流層的水汽有顯著的影響。CO、HCN 和SO2等污染物在平流層的濃度變化也被認為與深對流活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Park et al., 2008; 孫一和陳權亮, 2017)。
3.2 基于衛星觀測的深對流識別方法
根據衛星搭載的儀器不同,深對流的識別方法主要分為基于亮溫和基于反射率因子兩種。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僅對這兩類方法延伸出來的部分研究進行討論。
在基于亮溫的識別方法中,11 μm 通道的亮溫更為普遍的用來指示深對流。在11 μm 通道,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深對流的最低云頂亮溫通常被要求低于210~245 K(Houze, 1989; Sherwood, 2002;Liu et al., 2007)。在篩選出足夠高度的云后,MOD?S反演的光學厚度產品則被用來排除那些高度較高,但是厚度較薄的卷云或云砧(Yuan and Li, 2010)。除了一個固定的亮溫閾值被用來判斷云頂高度以外,Rossow and Pearl(2007)認為11 μm 通道的亮溫如果比對流層最冷點溫度低就可以表示為穿透性對流。Devasthale and Fueglistaler(2010)則通過判斷AVHRR 探測的云頂亮溫是否低于A?RS 探測的200 hPa、150 hPa 和100 hPa 等壓面的環境溫度來判斷是否為深對流。多通道亮溫數據的結合也可以用來識別深對流,Hong et al.(2005)利用深對流云頂在AMSU-B 三種水汽通道上的散射差異,定義了識別熱帶深對流的方法。Setvák et al.(2008)討論了深對流在Meteosat 靜止衛星6.2 μm 和10.8 μm通道的輻射亮溫差異,并認為正的亮溫差異在深對流發展階段的增加,是由于深對流將水汽從上對流層向下平流層輸送所致。
基于反射率因子的識別方法與基于亮溫的識別方法相比,不僅關注了云頂的高度和云的厚度,還關注了云內降水粒子和云滴粒子在深對流內的垂直結構與分布。Liu and Zipser(2005)最早定義了TRMM 衛星識別深對流的方法,在Nesbitt et al.(2000)發展的降水特征(PFs)數據集基礎上,如果PF 內20 dBZ最大回波頂高度超過14 km 則被認為達到了深對流的標準(Alcala and Dessler,2002)。基于此方法,大量的研究使用TRMM 觀測數據,從頻率分布、垂直結構、日際變化等諸多方面,分析了深對流在熱帶和副熱帶的活動特征。后來,很多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還對Liu and Zipser(2005)提出的方法做出了進一步的擴展(Zipser et al., 2006; Houze et al., 2007; Liu et al.,2007; Romatschke et al., 2010; 劉 鵬 等, 2012; Xu,2013; Qie et al., 2014)。由于隨后的GPM 衛星同樣搭載了Ku 波段雷達,因此這一方法被沿用在中高緯的深對流識別上(Liu and Liu, 2016; Gao et al.,2019)。使用CloudSat 來識別深對流的研究總體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同樣是通過判斷特定回波值的最大回波高度和回波面積等方式來對深對流系統和深對流核進行區分(Chung et al., 2008; Sassen et al., 2009; ?wasaki et al., 2010; Luo et al., 2011; Bedka et al., 2012; ?wasaki et al., 2012)。
由于極軌衛星對同一地點觀測的時間分辨率和深對流的發生頻率都比較低,因此極軌衛星只能偶爾觀測到一次深對流的剖面,無法觀測深對流云演變的整個生命周期。反射率因子和云頂亮溫的結合,則為分析深對流云的生命周期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Luo et al.(2008)結合CloudSat 和MOD?S 將深對流根據云頂高度和溫度分類為三種類型,討論了深對流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垂直結構特征。Takahashi and Luo(2014)將CloudSat 與靜止衛星反演的?SCCP-CT 數據集相結合,定義了深對流的整個生命周期,發現強的穿透性對流主要出現在深對流的初期增長階段。
3.3 深對流在青藏高原的觀測限制
衛星資料的豐富為深入研究深對流的時空特征提供了基礎,特別是對于人跡罕至的高原、沙漠和海洋地區,衛星觀測目前已成為研究深對流最主要的手段。但是這些衛星反演產品在青藏高原地區仍然需要地面觀測的進一步驗證。例如,Fu and Liu(2007)發現了TRMM 反演算法中對青藏高原對流云和層云降水的明顯誤判,Gao et al.(2019)在GPM 的反演結果中也同樣發現了這一問題。因此,對于衛星產品在高原地區的準確性仍然存在疑問。
搭載氣象探測儀器的飛機對深對流進行穿云和繞云飛行,對于獲取深對流云內溫濕廓線和滴譜分布的準確數據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其高昂的觀測成本,這種觀測試驗比較匱乏。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氣科學試驗(T?PEX-Ⅲ)將通過地面、飛機和衛星對青藏高原的地表、行星邊界層、對流層和下平流層開展為期8~10 年的聯合觀測。這一觀測試驗將有助于補充和完善青藏高原稀缺的觀測資料,也有助于提高對青藏高原深對流、對流層—平流層物質交換以及青藏高原對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理解和認識(Zhao et al., 2018)。
4 青藏高原深對流向平流層物質輸送的物理過程
4.1 穿透性對流
在關于深對流如何向平流層進行物質輸送的研究中,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深對流直接穿透局地對流層頂,影響平流層大氣成分的現象(Alcala and Dessler, 2002; Gettelman and de F. Forster, 2002)。Dessler(2002)指出深對流多達60%以上的溢出質量能夠穿透380 K 的等熵面。Dessler and Sherwood(2004)使用局地觀測和模式數據發現,穿透性對流對平流層的注入可以發生在至少390 K等位溫面的高度。Chaboureau et al.(2007)使用一種非靜力平衡的三維模式和衛星觀測數據證明了穿透性對流的存在,深對流輸送的冰相粒子能夠存在于局地對流層頂以上2 km 處。除了直接穿透對流層頂的上沖云頂,Wang(2003)認為深對流云頂附近在重力波破碎的作用下會出現一種快速向上發展的跳躍性卷云,水汽也能通過這種羽狀的卷云注入平流層。Sang et al.(2018)通過大渦模擬也發現重力波的破碎和冰晶的升華是穿透性對流加濕平流層的主要原因。
在 青 藏 高 原 地 區,Fu et al.(2006b)使 用TRMM 衛星觀測發現青藏高原上存在高聳的對流塔,這種對流塔相比周邊地區有更為孤立的雨區。Houze et al.(2007)同樣使用TRMM 衛星觀測在青藏高原的南緣發現了回波頂高度可以超過17 km的深對流。Long et al.(2016)發現青藏高原東側深對流的云頂高度超過16 km,并且顯著改變了UTLS 區域的水汽含量。Qie et al.(2014)統計了長達14 年的TRMM 衛星觀測數據,統計結果表明約9%的深對流能超過18 km 高度。借助于GPM衛星對青藏高原更廣的探測范圍,Gao et al.(2019)發現青藏高原上云頂高度超過17 km 的穿透性對流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東側和南坡。
4.2 對流層頂過渡層與青藏高原深對流的主要溢出高度
上述研究表明深對流能夠穿透對流層頂,并影響平流層的大氣成分,但是深對流能夠直接穿透對流層頂的比例仍然是十分低的。Gettelman et al.(2002)發現穿透熱帶對流層頂的深對流,僅占對流比例的0.5%。雖然單一的穿透性對流事件也可能向平流層注入大量水汽(Chemel et al., 2009),但是這種直接的注入輸送對于全球尺度的平流層影響可能是微乎其微的(Highwood and Hoskins,1998; Folkins et al., 1999; Corti et al., 2008)。深對流直接向平流層注入水汽和污染物更多的以間接的方式,先通過深對流抬升到一個對流層頂過渡層(TTL),然后再向上輸送。對流層頂過渡層被認為是一個具有一定厚度的氣層,對對流層物質進入平流層有著重要的影響(Sherwood and Dessler,2000, 2003)。
在Fueglistaler et al.(2009)對TTL 的定義中,深對流被認為主要在凈輻射層的高度附近出流。凈輻射層之上的非絕熱加熱對于水汽的抬升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對流層上部的溫度非常低,深對流輸送的水汽可能在還沒有被抬升進入平流層前,就會直接凝華為冰晶粒子降落回對流層,從而產生脫水作用(Mote et al., 1996)。因此,一個較高的溢出高度更有利于深對流向平流層的水汽輸送。
Gettelman et al.(2002)認為熱帶深對流的主要 出 流 高 度 大 約 在12 km。Folkins and Martin(2005)指出熱帶的深對流溢出層高度在10~17 km范圍,并通過溫濕的垂直廓線診斷出最大的深對流輻散層高度在12.5 km 左右。Park et al.(2008)發現南亞反氣旋內污染物濃度的最大值處于13~15 km范圍內,因此推測這一高度可能是亞洲季風區—青藏高原深對流的主要出流高度。這一高度范圍明顯高于熱帶地區深對流的出流高度。由于深對流通過夾卷、溢出和湍流混合等復雜的方式與環境空氣相互作用,每一個深對流的主要出流高度可能都是不盡相同的。因此,簡單通過測算大氣成分、環境場溫濕廓線和凈輻散層高度的方式來代表深對流的出流高度可能是不足夠準確的。Takahashi and Luo(2012)提出了一種用云砧高度來直接測量深對流出流高度的方法,該方法使用CloudSat 的衛星觀測數據,將云砧的上下邊界定義為深對流的出流高度范圍,將云砧內的最大回波高度定義為最大質量出流高度。Chen et al.(2019)采用這一方法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區的深對流出流,發現青藏高原及其南坡深對流的主要出流高度分別為12.9 km 和13.3 km。深對流更高的出流高度意味著青藏高原對平流層水汽可能有著更重要的影響。
5 青藏高原、亞洲季風區和熱帶海洋地區的深對流特征差異及其對平流層水汽輸送的影響
5.1 深對流的活動特征和云微物理結構差異
從TRMM 和GPM 衛星的全球觀測來看,深對流主要分布在亞洲季風區、西太平洋暖池、非洲的西海岸、亞馬孫流域和北美的大平原地區,并且又以亞洲季風區—西太平洋地區的強度最強、頻率最高(Zipser et al., 2006; Liu and Liu, 2016)。除了頻率分布的差異,深對流的日際循環、垂直結構、水平尺度和微物理結構也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這種差異又會影響深對流對平流層的物質輸送。
在日際循環上,深對流在陸地上的日際變化要明顯大于海洋地區,并且主要存在兩個峰值。一個峰值出現在午后,可能與午后增加的局地非絕熱加熱有關,另一個峰值出現在午夜,夜間深對流出現的原因相對更為復雜,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認識(Hong et al., 2008)。青藏高原地區深對流的日際循環主要呈現為單峰型,最大的峰值出現在午后到傍晚時段(Gao et al., 2019)。
青藏高原的深對流在對流強度和水平尺度上要明顯弱于南亞、東亞和熱帶海洋地區。Devasthale and Fueglistaler(2010)使用云頂亮溫數據對比了深對流在孟灣、印度和青藏高原地區的氣候態特征,發現印度地區深對流的頻率受季風影響較大,青藏高原地區深對流的頻率受季風影響較小。Luo et al.(2011)使用CloudSat 和CAL?PSO 觀測數據對比了青藏高原和南亞季風區的深對流,結果發現青藏高原地區的深對流云頂更為緊密,回波頂高度相對較低,對流的水平范圍也較小。Qie et al.(2014)使用TRMM 觀測數據對比青藏高原主體、青藏高原南坡、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深對流,發現強的深對流最多在青藏高原南坡,其次為青藏高原主體,再次為南亞和海洋。Xu(2013)同樣使用TRMM 觀測數據對比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東部的山地、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海洋地區的深對流,結果發現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四川盆地深對流的混合相位降水占比更高,青藏高原地區的混合相位層比其他區域都要更小,同時也指出深對流系統的水平尺度在青藏高原地區是最小的,最大的平均水平尺度出現在海洋地區。夏靜雯和傅云飛(2016)使用TRMM 觀測數據和全球探空數據集?GRA 對比東亞和南亞的對流降水發現東亞季風區的降水強度相比南亞更大,對流的回波頂高度也要比南亞地區高約1 km。
盡管上述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地區的深對流在頻率、強度和水平尺度上與周邊區域相比都較弱,但是青藏高原地區的深對流仍然有可能向平流層輸送更多的水汽。從深對流云頂溢出的較大半徑的冰相粒子,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會從TTL 內墜落,但是小的粒子可能下落的很緩慢,能夠在TTL 內存留較長的時間,然后在TTL 內蒸發或者升華,從而進一步向平流層輸送水汽(Alcala and Dessler,2002; Sherwood and Dessler, 2003)。因此,深對流云頂粒子的滴譜分布可能對最終的水汽輸送過程有著重要的影響。Yuan and Li(2010)發現高海拔地區的深對流在云頂區域的平均粒子尺寸更小。可以進一步猜測,青藏高原地區的深對流云頂可能有最小的云滴粒子半徑。最近,Chen et al.(2020b)通過GPM 衛星觀測發現了青藏高原和青藏高原東側平原地區的對流云滴譜分布存在著明顯差異,但目前關于青藏高原深對流滴譜分布的研究仍較缺乏。
5.2 環境背景場差異對深對流物質輸送過程的影響
UTLS 的溫濕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深對流是對平流層產生加濕作用,還是脫水作用。對流層頂最冷點的溫度決定了水汽進入平流層的多少(Mote et al., 1996),如果最冷點的溫度更低,那么意味著能進入平流層的水汽可能是更少的,極低的溫度甚至可能使對流層頂飽和的水汽混合比低于平流層原本的水汽混合比,從而對平流層產生脫水作用(Danielsen, 1982, 1993)。Fu et al.(2006a)指出青藏高原相比南亞季風區有一個更暖的對流層頂,水汽更容易通過青藏高原上空的對流層頂進入平流層。Randel et al.(2015)的研究也發現對流層頂的溫度控制著北半球季風區平流層的水汽分布。上對流層的環境場相對濕度也強烈地影響著深對流的溢出過程,如果環境場處于相對較干的未飽和狀態,那么溢出的冰晶粒子傾向于升華產生加濕作用,如果環境處于過飽和狀態時,冰晶粒子傾向于吸附環境中的水汽凝結后降落,反而產生脫水作用(Grosvenor et al., 2007; Jensen et al., 2007; Hassim and Lane, 2010)。Luo et al.(2011)指出青藏高原的深對流相比亞洲季風區的深對流處在一個更干的環境中,Chen et al.(2019)也指出青藏高原南坡的環境場冰水含量要明顯高于青藏高原主體,但是青藏高原主體的深對流對UTLS 的加濕作用卻明顯更大。因此,盡管青藏高原深對流在頻率、強度、垂直結構和水平尺度的統計中,均弱于南亞和東亞季風區的深對流,但是對平流層的水汽輸送影響可能是更大的。
6 小結與展望
通過衛星觀測發現青藏高原是對流層向平流層物質輸送的重要窗口,青藏高原深對流在物質傳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借助于衛星觀測和數值模擬的發展,青藏高原深對流研究在近年來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結果,但是仍有許多科學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1)衛星觀測發現在青藏高原和亞洲季風區上空的UTLS 區域存在水汽、氣溶膠的極大值區和臭氧的極小值區。數值模擬的結果也表明整個亞洲季風區為平流層貢獻了大量的水汽和氣溶膠,但是來自深對流的輸送貢獻還有待研究。除了物質輸送作用,深對流還能明顯改變對流加熱廓線,制造大量的高空卷云,其進一步產生的氣候效應也仍然不清楚。
(2)21 世紀以來,衛星的發展為觀測和研究深對流提供了重要的幫助,但是衛星的反演產品在青藏高原地區還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因此,發展適用于青藏高原的衛星反演算法和反演產品,增加地面和衛星觀測的結果對比對于研究青藏高原深對流具有重要意義。
(3)目前的研究表明,一些罕見的穿透性對流可以直接向平流層注入水汽和污染物,大多數水汽和污染物則通過深對流快速抬升到TTL,然后在大尺度熱力和動力作用下進入平流層。盡管可以使用軌跡追蹤模式來定量化的分析物質傳輸結果,但這些結果仍然缺乏足夠的觀測驗證。
(4)青藏高原深對流與亞洲季風區、熱帶地區的深對流相比,水平尺度和對流強度都要更弱,但是來自數值模擬的結果和痕量氣體的觀測卻發現青藏高原深對流有更強的物質輸送作用。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環境場差異、云微物理結構等影響因子對物質輸送過程有重要影響,但是不同因子對輸送過程的貢獻大小仍然不清楚。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更多的氣溶膠排放對于青藏高原深對流在物質輸送過程中的影響也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