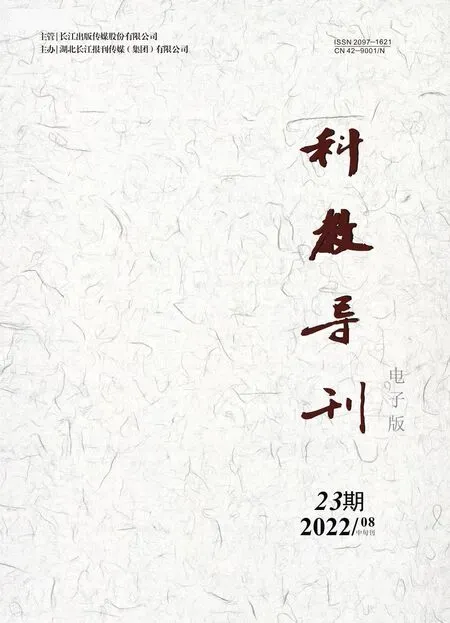壽光“圣文化”的探微挖掘與當代傳承
馬文軍
(濰坊科技學院經濟管理學部,山東 濰坊 262700)
壽光歷史悠久,文化繁盛,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發展演變和凝聚形成了一種以三個著名歷史人物為中心的獨特地域性“圣文化”現象,本文就此進行研究。
1 壽光“圣文化”的探微挖掘
壽光的“圣文化”現象,首先呈現為以賈思勰和他所著的《齊民要術》為代表的農圣文化。賈思勰是北魏孝文帝時期益都(今壽光)人,于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到東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寫成了《齊民要術》。全書凡10卷,計92篇,11萬字,集西周至北魏時期農業與工業生產知識、技術和經驗之大成,可謂是一部農業百科全書。[1]據統計,全書廣征博引前人著述150多種,其中包括西漢《汜勝之書》及之后崔宴的《四月令》等重要但已久佚的珍貴農書。《齊民要術》在唐代傳入日本,后又傳至世界各地。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到,“我看到一部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清楚地記載著選擇的原理”。這里的“古代百科全書”,即指《齊民要術》。總之,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不僅是我國寶貴的科學遺產,也是世界農業科學史上的一顆明珠。而在賈思勰的故鄉壽光,更是推崇備至,尊稱其為農圣,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農圣文化現象。
壽光的“圣文化”現象,還呈現為以夙沙氏“煮海為鹽”為代表的鹽圣文化。夙沙氏,又名宿沙氏,居住在山東沿海大致相當于今天壽光沿海一帶。關于夙沙氏的“煮海為鹽”,春秋時的《世本·作篇》記載,“古者宿(古宿夙通用)沙初作煮海鹽”。關于夙沙氏“煮海為鹽”活動的區域,《太平御覽》卷865記載,“宋衷曰: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衛為魚鹽之利”。夙沙氏與宿沙衛并非同一人,但從字面可以推知,兩者有密切關系,宿沙衛當為“煮海為鹽”的夙沙氏部落的后裔。由此可以推測,夙沙氏“煮海為鹽”的活動區域,當在今天山東省北部沿海地帶。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同。馬繼云先生認為,夙沙氏是一個長期居住在山東半島渤海灣沿岸地區的古老部族。[2]以夙沙氏“煮海為鹽”為代表的海鹽文化已經走向了全國,而在夙沙氏的故鄉壽光,其更是得到了高度的尊崇,被尊稱為鹽圣,壽光也由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鹽圣文化現象。
壽光的“圣文化”現象,進而呈現為以倉頡造字和倉頡墓為代表的倉圣文化。倉頡,俗稱倉頡先師,又曰蒼王、倉圣。《荀子·解蔽》稱,“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呂氏春秋·君守篇》亦記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總之,在中國歷史和民間,倉頡已經成為一位創造文字的文化圣人。與賈思勰不同,倉頡不是壽光本地人。《萬姓統譜·卷五十二》記載,“上古倉頡,南樂吳村人,生而齊圣,有四目,觀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不過,在全國多處紀念倉頡的遺跡中,壽光的倉頡墓建于晉代。《通志》記載,“《蒼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因建立時代較早,壽光倉頡墓與河南南樂的倉頡陵、陜西白水的倉頡廟等,有著較大的影響。總之,由于壽光倉頡墓建立時間極早,文化積淀厚重,且風景秀麗甚至長期榮居壽光八景之首,其就在壽光人民心中擁有了重要的地位,不但被壽光人民尊稱為倉圣,而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倉圣文化現象。
2 壽光“圣文化”的鄉土融入
綜上所述,壽光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以農圣賈思勰、鹽圣夙沙氏、倉圣倉頡三個著名歷史人物為中心,發展演變和凝聚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壽光地域性“圣文化”現象。這種“圣文化”現象已經深度融匯嵌入了壽光鄉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并成為當代壽光整體文化體系建設的重要來源和有機組成。
目前壽光城內的道路取名分別有農圣街、倉圣路、圣城街等,均為壽光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社區機構取名分別有倉圣社區、圣城街道等,其中圣城街道為壽光核心城區和市政府所在地,其名即因境內有“造字圣人”倉頡之墓而來;公共場所取名分別有倉圣公園、農圣公園等,其中倉圣公園建于1991年,占地址50畝,是壽光最主要的公共游樂場所之一;企事業機構取名分別有壽光農圣種業有限公司、濰坊科技學院農圣文化學術交流中心、圣城中學等。
以“圣文化”為依托,壽光還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并開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學術會議。專門的研究機構有濰坊科技學院農圣文化研究中心、濰坊科技學院賈思勰農學院等,前者為山東省高等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和山東省社會科學普及教育基地,后者為濰坊科技學院實體二級學院;研究學會有中國農業歷史學會農學思想與《齊民要術》研究會(掛靠壽光)等,已經連續舉辦十一屆“中華農圣文化”等高水平學術研討會。
特別地,2012年韓國麗水世博會上,山東面向全世界推出了包括“夙沙氏與海洋化工”在內的三件“省寶”來展示山東文化,同年8月23日,中國海洋湖沼學會、中國太平洋學會、中國鹽業協會等在壽光聯合主辦了“鹽圣·鹽都與壽光”的海鹽科技文化座談會,使夙沙氏不僅作為鹽宗形象,而且作為一種海洋文化的符號、現代海洋化工的載體和海鹽品牌的依托,得到了廣泛傳播。[3]
三種“圣文化”中的中心人物,或者已經去日已久,或者僅為歷史傳說,或者本人生非本鄉,但在壽光不但都得到了從官方到民間的高度認可和深度接納,而且進一步脫凡入圣,被壽光人民推崇升格至了可以并列于“孔圣人”的“至圣之人”層次,成為壽光獨特的區域性文化標識。這表明,壽光對作為社會發展長時期深層次積淀而成的各種流派的文化,天然地擁有著一種內在強烈的崇尚追求,而且實現了不同文化流派的交融并匯和相得益彰。
實際上,作為壽光地域性“圣文化”之重要組成的農圣文化、鹽圣文化、倉圣文化,分別蘊含著三種不同的文化流脈和精神承托。農圣文化內在蘊含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體性組成的大陸文明和農耕文化及其背后的勤勞堅忍精神,鹽圣文化內在蘊含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補充的海洋文明和工商文化及其背后的開放進取精神,倉圣文化內在蘊含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體性的儒家文化的耦合響應進而超越之的崇文尚化精神。
3 壽光“圣文化”的當代傳承
三種不同文化流派在壽光的歷史性交融并匯和時代性鄉土融入,以及壽光人民對三種文化流派內在的強烈認同和深度接納,反過來也對壽光經濟和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極大的文化反脯和源力供給。改革開放以來,壽光發展成就巨大。2021年,壽光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3億元列全省第三,金融機構存款1431億元列全省第一,綜合實力名列全國第37位。壽光綜合條件其實并不特別優越,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顯然,文化是一種重要的內在根因。壽光并非冬暖式蔬菜大棚的首倡之地,但卻可以以破釜沉舟之勇氣引進技術推廣生產,將壽光建成全國著名的“蔬菜之鄉”,其背后當是賈思勰農圣文化及其勤勞堅忍精神的支撐。壽光區位交通并不特別優越,至今尚無高鐵開通,但卻可以建成工業強市,在造紙、化工等領域占據重要位置,其背后當是夙沙氏鹽圣文化及其開放進取精神的給力。壽光區區一個縣級城市,人才文化基礎并不雄厚,但卻可以集全市之力建成全國唯一一所縣辦大學—濰坊科技學院,其背后當是倉頡倉圣文化及其崇文尚化精神的使然。
當前壽光發展已經進入了新時代,其要想取得更好的質量發展,顯然應該更加重視對其“圣文化”內在優秀精神的深度挖掘和高效傳承。可以給出三條具體對策:
一是挖掘凝聚三種“圣文化”之精髓,正式明確和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國之“圣城壽光”,集全市之力,久久為功,建出模式,建成品牌。二是面向當前的壽光中小學,在正常教材體系之外組織編寫以三種“圣文化”為核心靈魂的鄉土文化教材,把三種“圣文化”中的精華精髓,以正規的形式和正式的渠道予以合理融入和實現高效傳承。三是以城市建設為重點抓手,合理設計城市布局,合理確定城市風格,加大三種“圣文化”素材和精神的深度融入和優美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