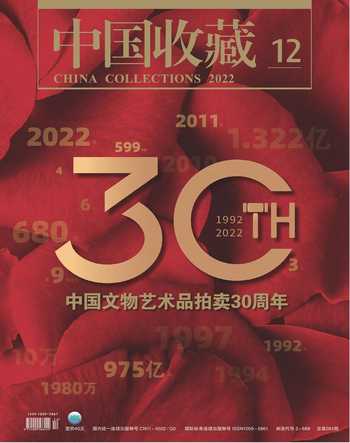胡妍妍:風雨30年與行業一同前行
王菁菁

“那時候一到春天,北京漫天黃沙,大街上跑的不是公共汽車就是‘小面”。我們每天都要著正裝,‘奢侈地坐上招手即停的‘面的,到當時北京最牛的五星級飯店——長城飯店去上班,嘉德的第一個辦公室就設在那里。”
“長城飯店中庭是咖啡廳,一到傍晚,就會有一位菲律賓歌手開唱。我們就伴隨著流行歌曲打電話聯系客戶、看畫,氣氛與我之前的工作環境迥異。估計當年北京城沒有一家拍賣行是這樣的。”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總裁胡妍妍向《中國收藏》雜志記者娓娓道來。
就在接受我們采訪的前一刻,胡妍妍正在為今年秋拍籌備工作而忙碌。當開始采訪,回憶與感慨又使得她迅速地切換到另外一種平和狀態之中。她的講述讓我們看到了這位帶領中國嘉德拍賣創下一個又一個拍場奇跡的“掌舵者”不一樣的一面。
“30周年是我們行業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而明年也將迎來中國嘉德成立30周年。30年變化實在太大了。”胡妍妍感慨道。30年,對于一個人、一家企業、一個行業來說,有很多揮之不去的記憶。當我們將胡妍妍言談間的“畫面”勾勒出來,看到的不光是人的成長、企業的壯大,還有時代的變遷和進步。

帶著好奇與探究之心走下去
背景摘要:1993年5月,中國嘉德成立;同一年,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系的胡妍妍進入中國嘉德工作。她是中國最早獲得文物博物館學科碩士學歷的專業人士。幾乎與行業發展同步的中國嘉德,它的創業初期也是內地文物藝術品拍賣萌芽期的一個縮影。
采訪金句:“近30年來,幾乎所有的崗位我都做過。”
胡妍妍:上世紀90年代初我已大學畢業,在北京做出版編輯工作。1993年,中國嘉德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我應聘成了其中的一員。坦白說,我并未感覺專業給自己最初的入行帶來了多大的優勢。因為這是一個對綜合素質要求很高的行業——不但要具備廣泛的知識儲備,同時要掌握商業運作常識和經驗,還有就是對文物藝術品的熱愛。這些是在書本上很難學到的。
當然,讀書和之前的工作經歷,對初來乍到的我還是有所幫助的。比如,圖錄里需要介紹書畫家生平和藝術成就,對我來講駕輕就熟,馬上就能做好一本“作者簡介”。


那時的中國嘉德剛剛起步,藝術品拍賣在中國內地也剛剛起步,幾乎沒有什么經驗可以借鑒。唯一的學習途徑是向久負盛名的兩家國際拍賣行、向參與過拍賣的港澳臺收藏家請教。從第二次拍賣起,1994年10月,我們就去了香港看預展,結識了很多同行和收藏家,親眼見到了拍賣是怎么一回事,大開眼界。
即便在上世紀90年代初,藝術品拍賣也是動輒幾萬元甚至百萬元一槌定音,嘉德首場拍賣就成交1400多萬元,與當時樸素平淡的現實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這種反差感也形成了一種吸引力,帶著好奇的我們,包括我們的客戶們,踏入一方新的天地。
時至今日,入行工作近30年,可以說拍賣行幾乎所有的崗位我都做過。記得當時辦公室里面有個小屋,作為儲存拍品的庫房,外出征集的同事帶回來的拍品就存放在里面。下班后,大家輪流值班。輪到誰,晚上就睡在辦公室那張大桌子上。有時候剛躺下,外頭咚咚咚敲門,出差的同事回來了,趕緊起來開門,把拍品入庫,做好記錄。白天做業務員,晚上兼職做庫房管理和門衛。創業之初,大家就是這樣忙碌又高興地工作著。
離不開我們專業、嚴謹的初心
背景摘要:眾所周知,近30年來,中國書畫尤其是近現代書畫不僅是中國嘉德的王牌項目,也是整個藝術品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內地文物藝術品拍賣的火爆,中國書畫功不可沒。
采訪金句:“能對中國書畫市場起到推動作用,意義更為深遠。”
胡妍妍:中國嘉德首場拍賣會是1994年3月舉辦的,上拍的拍品不少來自北京市文物商店。大概半年后,北京市文物商店也注冊成立了自己的拍賣公司,即北京翰海。
記得首場拍賣會第一件拍品是吳熙曾《漁樂圖》。編排圖錄時,我覺得漁樂有豐收的寓意,用它來開場是個好彩頭,這幅畫就“歷史性”地成為了嘉德書畫拍賣的“第一拍品”。其1.5萬元的估價是秦公先生定的;一番競價后,被香港著名大藏家張宗憲先生以8.8萬元的落槌價競得。而親自敲響這一槌的則是鑒定大家徐邦達先生。


無論是專場策劃還是拍品編排,首場拍賣會都比較隨意,沒有前思后慮。中國嘉德初創期,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沒有什么束縛,自由發揮,想起來既幸運又幸福。
首場拍賣會,我們選擇了中國書畫與油畫兩個項目拍賣。日后,中國書畫尤其是近現代書畫成了中國嘉德的一個主力板塊,成就了現在這么一個活躍的大市場。在我看來,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我們學習美術史的時候,教科書以及俞劍華、潘天壽、陳師曾、鄭午昌等書畫史著作,都是從三代講到清代,往往就到吳昌碩即止,齊白石、張大千、溥心畬等近現代藝術大師并不在美術史教學體系和學者研究范疇中。老一代藏家的收藏重點是古代書畫,如吳門四家、揚州八怪、清初四僧。但是,如果您翻開嘉德首場拍賣的圖錄,會看到這些大家的名字:陳半丁、豐子愷、馮超然、傅抱石、黃賓虹、溥儒、齊白石、錢松巖、田世光、吳湖帆、張大千……是以20世紀近現代名家作品作為主力。原因大概是近現代書畫作品在民間存留數量比較豐富,市場對近現代作品的熟悉程度和認知程度相較于古代作品更高。由此,嘉德選擇了由此入手,首次書畫拍賣一舉成功。之后,各拍賣行基本循著這條路征集,近現代中國書畫成為拍賣市場中最有價值、最活躍的大市場,創造了不少藝術家作品拍賣的奇跡。
在北京做藝術品拍賣,你會發現但凡遇見手上有點兒藏品的人,肯定會有書畫。而說到齊白石、李可染等近現代書畫大家,婦孺皆知,甚至有的人還跟他們打過交道;你要說起石濤、八大山人,即便不收藏的人,對這些名字都不陌生。在我看來,北京的文化底蘊深厚,臥虎藏龍,是拍賣書畫的沃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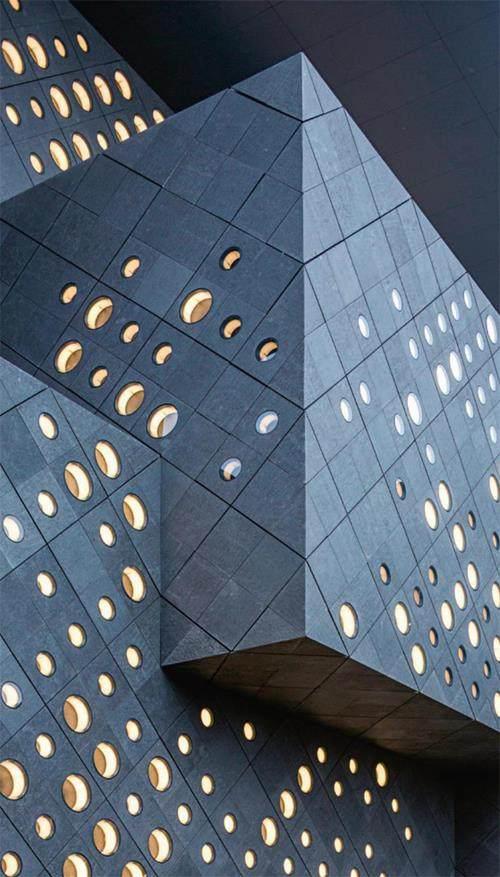

大概是2007年,我們就有做“夜場”的構想。2006年嘉德將原有的每月一次的“小拍”升級為一季度一次的“嘉德四季”,那么春秋大拍如何升級?同事們提出做個“夜場”,起初想得比較多的是在形式上,比如布置漂亮的拍賣現場、穿上晚禮服等等。但當時王(雁南)總認為,春秋大拍模式升級需要慎重。她問了我們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堅持夜場選件的品質。如果夜場的名聲越做越大,賣家肯定會紛紛要求將委托的拍品放到夜場,能不能保持一顆公平的心去選擇?二是如果缺乏優質拍品,會不會以次充好去拼湊?這兩個發問讓我們清醒認識到:拍賣行的根本是把住質量關,做高端細分市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布局謀篇,從拍品上提高質量。
2010年,內地藝術品拍賣市場呈現井噴式行情。當年的秋拍,我們策劃推出的“秋光萬華——清代宮廷藝術集粹”專場,22件拍品成交近7億元,獲得成功。其中,王羲之《平安帖》拍出了3.08億元的天價,明代陳栝《情韻墨花》手卷以1.14億元成交,清乾隆黃花梨云龍紋大四件柜以3976萬元創下了中國古典黃花梨家具拍賣的世界紀錄……應該說,這個專場是一次很好的嘗試,堅定了我們要開設夜場的信心。2011年春拍,我們適時推出“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32件拍品總成交額逾10億元,一炮打響。
現在總有藏家跟我們說:你們每季拍賣的場次太多了,根本看不過來,我就專注“大觀”吧,畢竟拍品是經過你們精挑細選的。“大觀”夜場堅持了11年,成績斐然,這是嘉德不忘初心,精心打造出的一塊金字招牌,對中國書畫市場的細分、升級、引領以及強有力的推動都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路是越走越寬的
背景摘要:2012年,中國嘉德在香港舉辦了首場拍賣會;時至今日,其在港槌起槌落走過了十個春秋。不久前落槌的2022秋拍暨十周年慶典拍賣會以7.63億港元圓滿收官,創下歷來最高的季度總成交。
采訪金句:“不做不知道,只有做了才發現差距。”
胡妍妍:香港是我經常去的一座城市,并不陌生。但自2014年接手中國嘉德(香港)董事總裁一職后,我才意識到即便都是嘉德,內地和香港確實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不做不知道,只有做了才發現差距。
我們內地藝術品拍賣企業歷史不夠長,有短板。比如缺乏一個國際化貨源庫。特別是這三年受大環境影響,你會發現蘇富比、佳士得這樣的國際拍賣行能夠迅速地調整拍品結構,“東方不亮西方亮”,以優勢板塊彌補劣勢板塊,顯現出整體優勢。再如,香港市場對新事物的探索比較超前,像NFT數字藝術拍賣,從中可以感受到香港市場的包容性。再有就是香港的很多商業規則比較務實,比如這兩年,中國嘉德(香港)都得到了香港政府的場租減免政策支持,這一舉措讓我們每年省下了很大一筆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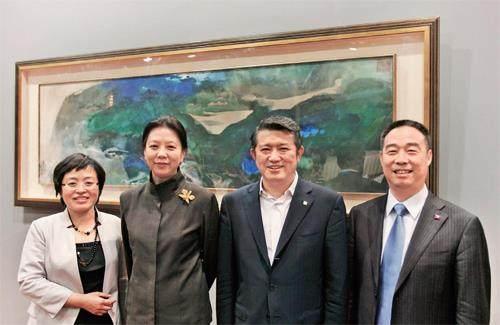
經過這十年的赴港實踐,尤其是近幾年的不斷深耕,現在中國嘉德在北京與香港兩地的拍賣各具特色,為兩地買家提供了差異化服務。以前我們可能會擔心:如果在這兩地拍賣中國藝術品,會不會形成激烈的內部競爭?其實拍著拍著就發現,路是越走越寬的。如今中國嘉德(香港)公司在玉器、瓷器、二十世紀和當代藝術等門類上都找到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為我們整體的發展帶來了更多可能性。
這個行業魅力無窮
背景摘要:文物藝術品拍賣行業的發展不是孤立前行的,離不開方方面面的支持。文博機構、專家學者及相關業界人士的襄助必不可少;藏家、買家群體的一路相伴更是缺一不可。
采訪金句:“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路,是下一個30年值得去關注的。”
胡妍妍:我很幸運,一入行就遇到了嘉德這么好的公司與陳東升董、王雁南總這么好的領導。從業30年來,我充分體會到了文物藝術品拍賣行業魅力十足、魔力十足。在這里,能過手千百年來最好的文物、能欣賞最美的藝術品、能見識最有趣的人們、能觸碰最婉轉曲折的故事,有看不完的風景。我至今不后悔有這么一份職業,或者說是事業。如果讓我現在重新選擇,還真想不出有什么比這個更好玩的工作。
30年前,我們從“一張白紙”起步——沒有客戶名單、拿不準估價、不知道如何組織一場拍賣會,摸著石頭過河,一點點探索,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海內外專家、學者與前輩的支持,結識了很多藏家朋友。內地文物藝術品拍賣事業的發展,是至少兩代人共同參與、推動、努力的結果。
記得我第一次赴外地征集,是和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章津才先生一起去上海拜訪劉湖涵教育基金會。作為民國時期上海灘知名地產商,劉湖涵非常喜歡大尺幅畫作,今年嘉德在香港拍賣的二十六平尺黃賓虹《山水巨幛》,上款人就是劉湖涵。
那次我和章津才先生見到劉湖涵教育基金會的主事人朱曾滸先生,他的愿望是拍賣過后,將拍賣所得全部用于教育基金。章津才先生審看畫作非常快,業務嫻熟,對畫家生平、趣聞軼事、款識鈐印等等脫口而出,我在一旁做記錄,半天就征集了20多件作品,有張善孖《猛虎吞日》,以及吳琴木、鄭午昌等海上名家的作品。
一晃20年過去,前幾年我走在上海馬路上,竟然遇到了朱先生。老人家已經90歲高齡了,街頭偶遇我們都非常開心,站在原地聊了半個多小時。我們做拍賣的初期,行業新、節奏慢,與客人交往不惜時間,自己學到了許多,也交到了朋友。有人說,拍賣行是溫暖的行業,人情味兒是這個行業最值得記憶和珍惜的。
藏家則是這一路走來相伴時間最長的群體。我有個設想,在公司成立3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約30位嘉德的老朋友、老客戶暢談過往。想到這里,劉益謙、王薇、汪健、楊崇和……一串串名字就躍入腦海。
劉益謙先生在嘉德買的第一件作品是郭沫若的書法,第二次買下了陳逸飛《山地風》。回想起來,他幾乎年年來、場場到。有一次為了趕上我們的拍賣,他搶了兩張火車站票,半夜才到北京,真是太感動了!十年前他的龍美術館開幕,開啟了私人美術館的先河,也成為了中國藏家進階的里程碑,這無疑是當前藏家群體中一個重要代表。這種成長的過程,是一種相互見證。
近年來,我發現長期以回報率、成交價、撿漏為樂趣的收藏圈,風氣有些變化。一是不少藏家安心整理研究自己的藏品,并不急于出手;他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拍場收獲,或出書立傳,或舉辦收藏展,或辦私人美術館、博物館。二是將目光拓展到西方藝術品的藏家,他們出入國際拍賣行和藝術博覽會及畫廊,橫向拓寬收藏,與國際接軌。三是普通民眾到訪拍賣預展、參加藝文活動的人越來越多,年齡也愈加年輕化。凡此種種,令人倍感欣喜。傳承文化、熱愛藝術,不僅是一句期許,還已然成為了藏家和民眾由衷的感悟和具體的行動,這或許與我們30年來為藝術普及、傳播、賞析和收藏所做的努力相關吧。
如今,中國內地文物藝術品拍賣步入“三十而立”,已形成了一個基本格局。隨著技術不斷革新,引發交易模式的改變,定會讓藝術品拍賣日新月異,并有更為廣闊的天地。我想,我們只有不斷去探索和嘗試,才能找到屬于自己的路,共同續寫行業下一個璀璨的30年。(注:本文圖片由嘉德拍賣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