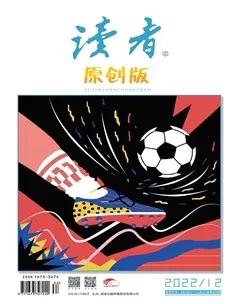西紅柿醬給的底氣
文 | 掛掛釉

一
上禮拜試供暖開始,僅僅一晚,屋里就告別陰冷,早上起床容易了很多。對于北方城市,暖氣片里的流水聲是入冬后最美妙的聲音,可以給人極大的安全感和實打實的溫暖體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供暖比冬季的節氣更有“冬天感”。
同供暖一樣,現代城市里的人們應對冬天比過去簡單了不少,再加上有了網購等科技的進步,以前需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如今都能輕松解決。
頭兩天我媽做了西紅柿炒雞蛋,許是因為這道菜兩個孩子在學校常吃,都沒怎么動筷子,我母親感慨:“以前冬天想吃點兒西紅柿可沒有這么簡單,但凡有,連點湯兒都不會剩下。”
這是實話。
過去每年的這個時候或是更早,家里就開始自制瓶裝西紅柿醬了。
我這個年紀的人大概算是自制瓶裝西紅柿醬最后的見證人,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就越來越少有人再做。也或許是因為搬進了樓房,不似以前大雜院里集體做醬的場面,誰都看得見,真有人做也無人知曉了。
北京的西紅柿醬并非現在商超、網上所見這般。大致來說,就是把西紅柿裝進玻璃瓶,通過蒸煮再密封的方式,做成可以長期保存的罐頭,用來解決冬日北京人民飯桌上菜品單一的問題。
從前的北方冬天菜品單一,做法也粗獷,菜色多暗沉,一番熬、炒、燉下來,土豆、蘿卜、大白菜都變得黑乎乎的,因此,西紅柿醬的這一抹紅色以及它酸甜的口味,很能勾起人的食欲。
自制西紅柿醬的歷史似乎比冬儲大白菜還要早一些,我個人認為,其價值也遠超其他過冬物資。比起對白菜、大蔥等菜類單純的捆綁、碼放、晾曬,西紅柿醬的制作頗具技術性和藝術性,不但實用,還有裝飾功能。如果當年誰見過窗臺上、床沿下、墻根邊那一排排整齊劃一、顏色鮮艷的西紅柿醬,就知道我說的是怎樣的場面。
制作西紅柿醬總給人一種恢宏的氣質,這種氣質一部分要歸功于盛裝它的器皿,我印象中,所有人都只選擇同一種容器——醫院輸液用的液體葡萄糖瓶。
西紅柿醬和葡萄糖瓶是怎么被發現可以搭配在一起的,我不得而知,但我成年后回憶起這件事,總會對第一個做如此嘗試的人生出巨大的欽佩。這是一種充滿智慧的嘗試,“西紅柿醬和葡萄糖瓶”比“下雨天和巧克力”要配得多。
首先,蒸煮是當年民間最安全有效、最有可操作性的消毒殺菌法,而玻璃制品讓人完全不必有器皿炸裂的憂慮。
其次,葡萄糖瓶肚大口小,裝入后傾倒概率小;膠塞封閉嚴實,連打開都難,遑論漏氣,用針管抽氣后制造出了真空環境,不必擔心變質,讓吃進嘴里的東西變得更讓人放心。
最后,一個葡萄糖瓶容量的西紅柿醬剛好夠三口或四口之家吃上一頓,不管是炒菜還是做湯,不欠缺,不浪費。
按照現在的話來說,它解決了所有生鮮蔬菜保存的痛點,可以說是完美容器。鑒于瓶子的重要性和龐大需求量,當年可以找到葡萄糖瓶資源的人就非常吃香,如果誰家有人在醫院工作,那他就得負責一整個家族和身邊好友的瓶子采購工作了。
二
待拿到瓶子,就要開始做醬,這將有不少工作步驟要進行。
第一步是葡萄糖瓶的清潔消毒。瓶身和橡膠塞子清洗后水煮消毒,取出后,瓶口朝下,把水控干。控水是不能含糊的,須得一丁點兒水都不留,否則會讓一瓶醬前功盡棄——
多年后我在歐洲工作時,為解饞,泡了兩大瓶臘八蒜,買米醋和大蒜都花了“大價錢”。我特意看好日子,農歷臘月初八當天封瓶,耐心等待一個月。我又專門跑去采購了做三鮮餡兒餃子的材料,結果餃子包好,下鍋后,我取出瓶子,鄭重開蓋,一股霉味兒沖鼻而來。這全因為瓶子清洗后沒有控干水分。
西紅柿的挑選也不能湊合,有裂紋、坑洞的不行,過熟軟或者泛青不熟的也不行,做醬的目的是能保存得更久,所以選的西紅柿一定要天賦極佳,成熟無傷、飽滿鮮紅、光澤十足的西紅柿才能成為瓶中好物。入選的一大盆西紅柿光是擺放在那里就相當賞心悅目,它們都是西紅柿里的翹楚。
同樣的,所有在制作過程中接觸西紅柿的工具、容器,包括但不限于案板、菜刀、盆碗等,都得經過認真清洗后完全控干水分才算過關。好馬配好鞍,好柿配好碗,這都是“在論的”。
接下來就是裝瓶。
西紅柿要切成小塊或者條狀,以便能順利地塞進葡萄糖瓶的小口兒。為了提高效率,須使用干凈漏斗,還要不時用筷子往里面杵一杵,讓瓶子能裝得更瓷實,這個過程很耗時間。
過去凡做西紅柿醬,都會奔富余了做,一是因為你不能保證每一瓶都成功、不變質,多做點兒心里踏實;二是在有資源、有精力的條件下,做多了可以分給老家兒(長輩)、鄰居、親朋、好友,這是很好的人情往來。所以每家少則十幾瓶,多則三四十瓶,這真是一項大工程。
實際上,我并不喜歡這項工作,費時又費力,本身也沒有趣味性。但我喜歡參與家庭工程的感覺。
往葡萄糖瓶子里揣西紅柿,除了費工夫,還需要點兒智慧,既要盡量裝得滿一點兒,又不能因貪心而塞得過滿,須留出些許空間,這一點很重要,否則,在某個冬日的夜里,發酵了的“西紅柿醬炸彈”會教給你不少科學道理。
裝好瓶后就要蒸。因為量大,家里的灶和蒸鍋疲于應付,至少要蒸上好幾鍋。開鍋后十幾二十分鐘關火揭蓋,待稍涼一點兒、不至于燙手時,就得趕緊用膠皮塞子封瓶,第一時間讓細菌與“柿”隔絕。
這樣一套流程下來,西紅柿醬才算做好。仔細碼放于家中陰涼干燥處,柜櫥里、床沿下、窗臺上、墻根兒邊,那一排排裝滿紅亮的半液體、半固體的瓶子,讓整個家充滿魔幻感。
三
當然,吃它的時候也很魔幻,因為你必須連拍帶甩,才能把醬從瓶子里倒出來,整個過程的強度不亞于健身,尤其對肩膀考驗很大,對治療肩周炎或許有效。
西紅柿醬等同于西紅柿,怎么吃都成,是過去冬日餐桌上難得的尖兒貨。但時至今日,我并不認為西紅柿醬本身有什么優勢,它的味道也未必比得上新鮮的西紅柿。可是,它的確有一些超過它本身的意義在里面。
葡萄糖瓶裝西紅柿醬算得上民間生活智慧的標志性產物,由此可以看出,人類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是如何殫精竭慮地利用所有資源費心經營生活的,只是為了讓自己能過得豐富多彩一點兒。
生活需要點兒技巧和努力,人必須得上點兒心才能讓日子過得更好,懶與不懶、費勁兒與不費勁兒之間的生活質量必然有著明顯差距。
生活并不吝嗇,它會給努力生活的人以更好的回報。
制作西紅柿醬讓過冬有了一種儀式感。在隨后而來的寒冷冬日里,隔段時間,每開一瓶醬,聞到半熟的西紅柿醬的香氣,那種成就感難以言表。更重要的是,西紅柿醬也讓人有了可以踏實對自己說“這個冬天,我能把日子過得還不錯”的底氣。
歲數越大就越明白,回報有多難得,底氣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