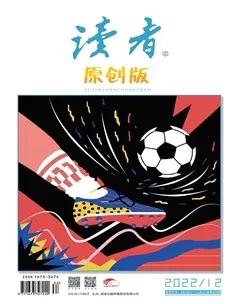見字如晤
文 | 方和斐
一
昨夜收到多年網友的一條消息,說在一條舊帖子里看到我,感覺很親切。我點開那條多年前的帖子,又勾起許多回憶。
初中時,英語考試永遠有一道作文題,例文的落款永遠是“Lei Li”,永遠寫給一個外國小孩。許是受此啟發,我們的英語老師也鼓勵我們聯系國外筆友。微機課上,我們湊在一起,上網站、查字典,各自尋找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外國小孩的聯系方式。于是,就這么稀里糊涂地,我和一個土耳其女孩開始了通信。
遠隔重洋,我們使用電子郵件通信,但即便是字斟句酌,一個詞一個詞地造句,我也倍感吃力——在和真正的外國人交流時,英語課上所學的那些句子遠遠不夠。看著她連篇累牘地描述自己喜歡的樂隊和作家,我捧著一本詞典左翻右翻,卻仍無法理解——為什么說“genre”不說“kind”?她的落款為什么用“cheers”?
土耳其的學生和中國的差不多,大家都要參加重重考試,都爭搶著上那幾所頂尖大學,都想獲得更廣闊的平臺。活在學業的重壓和父母的嚴格監督下,我們彼此能感同身受。
上高中時,我們在同一個聊天軟件上互加了好友,我也第一次聽到土耳其語是什么樣子。她說她在學漢語,如果能考上大學,想來中國留學。
大學時,短視頻還未興起,大家在校內論壇和博客上寫文章,以文會友似乎相當自然。許多帖子都帶著濃濃的才氣和獨特的感情。那時,我和土耳其女孩都看了《瑪麗和馬克思》這部電影,很受感動——跨越大洋的筆友感情,真令人羨慕。
我身邊的朋友里面,誰在和筆友聯系,我們互相都是知道的。在以文科專業著稱的學校,這樣的少男少女可不少。聽說有人有維持了十幾年的筆友關系,卻從未見面,這讓我們聽了大為贊嘆。
二
我還交到一個英國網友。那時很流行一個叫作“技能交換”的概念,我倆以此為契機,我教她數理化,她教我英語。當然,兩個人首先得互相對付,聊聊天熟絡熟絡。
網友列舉了許多破冰話題,其中一個是“分享彼此最想去的地方”。
“帕薩迪納,”我寫,“還有帕洛馬山。那里是現代星系宇宙學誕生的地方,對天文學者們來說,那里是圣地。你看過《生活大爆炸》嗎?主人公們生活的地方就在那里。哦,我想到那里去看白色圓頂的天文臺,那里有個‘通往星空’的路標……你呢?”
她的消息彈出來:“你搜索一下瓦納卡之樹,那是世界上最孤獨的樹。”
停頓幾秒,又一條消息:“我是個思維簡單的人。僅僅是凝望著它,就足以讓我覺得很幸福了。”

天哪,我被震撼了!有種闖進山門,被高人點化的感覺。她竟然活得這樣通透。
多年后,我讀到哈佛大學生物學巨擘愛德華·威爾遜的《給年輕科學家的信》,他說他18歲時和一位比他大7歲的博士生通信。那位筆友的熱情和指導,幫助他走上了正確的人生道路。
我一直覺得結交筆友是一件好事,在習以為常的生活軌跡之外,還能聽到另一種聲音,感知到另一種生活。其實,一切都是淡淡的才好。可惜,“筆友”似乎總帶著太多浪漫意味,而過高的期待往往容易落空。
不過,我從來沒用自己最自如的母語寫過信。生活如同洪流滾滾而來,現實里有無數“正事兒”塞滿時間。滿世界飛來飛去,國內外不同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不再稀罕,寫英文郵件則像《查令十字街84號》那樣,于我成了司空見慣的生活、工作成分。
我找回了那時用來發帖子的論壇賬號,不意外地看到了郵箱里積壓的未讀郵件——落款都是多年前交流過的網友,如今怕早已物是人非。我不知道,現在的他們還愿不愿意再聊詩歌、電影和音樂,抑或只將其看作青春期的一段玩鬧。我忍不住想,如果當時真的和他們中的誰一直通信,現在會是怎樣一番情形。我的抽屜里還躺著一沓星空明信片,那是曾經想寄給朋友們的,但一直都沒來得及貼上郵票……
也許有一天,我真的會再遇上誰,我會把它們寄出去。相知一瞬便是緣分,誰也說不好未來會怎樣。我打開聊天軟件,看到現在在伊斯坦布爾上學的土耳其女孩剛剛曬出她的派對照片。照片風格看起來很像流行網紅們拍的。我點了個贊,放下手機,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