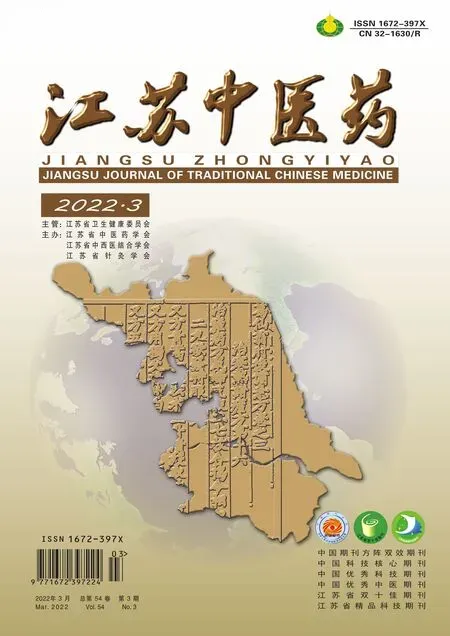經方烏梅丸治療惡性腫瘤擷要
王 熙 張瑩雯
(1.湖北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學院,湖北武漢 430061;2.武漢市中醫醫院,湖北武漢 430014;3.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湖北武漢 430071)
烏梅丸出自《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其主要功效為寒熱并用、清上溫下,主治“蛔厥”。近年來,本方在治療潰瘍性結腸炎、腸易激綜合征、慢性萎縮性胃炎及婦科、皮膚科疑難疾病等各種慢性難治性疾病方面的研究多有報道[1-5],在治療腫瘤及其相關病癥方面的應用報道亦不在少數[6]。筆者臨床常運用本方加減干預惡性腫瘤及其相關病癥,取得滿意療效,現將其治療機理及運用規律總結如下,以為臨床治療惡性腫瘤拓寬思路。
1 厥陰病與惡性腫瘤的關系
《素問·至真要大論》中首論厥陰為“兩陰交盡也”,意為兩陰交盡,一陽初生之經。另《素問·陰陽離合論》從三陰開合樞角度指出“厥陰為闔”,劉力紅教授認為此處之闔,應為闔陰氣,即陰氣逐漸消潛、陽氣逐漸復升之意,厥陰闔的作用即為“闔機”,闔機不調則陰陽序貫相交之穩態遭到破壞,不相協調,不相順接[7],因而出現或寒厥,或熱厥,或陰陽錯雜、寒熱并見的癥狀,《傷寒論》原文326條厥陰病提綱即是寒熱錯雜證的具體表現。惡性腫瘤可歸屬于中醫學“巖證”“積聚”“癥瘕”等范疇,其病因病機尚無統一認識,特征及臨床癥狀也因腫瘤類型而表現為多樣化,甚至同一腫瘤不同病理類型其臨床特征也會存在一定差異,但大多數學者仍認同腫瘤是全身屬虛、局部為實的一類疾病[8]。虛則為正氣虛,實則為痰、瘀、熱、毒邪混雜。李忠教授認為腫瘤常表現為陰陽乖違和寒熱錯雜,患者機體內同時存在截然相反的病理現象,這與厥陰病的特點相合,由此提出腫瘤的根本病位應在厥陰,同時,陰陽氣不相順接影響細胞的分化成熟,從而導致腫瘤細胞即“癌毒”的產生,并使其無限增殖,因此提出臨床治療腫瘤的大法應為寒溫并用、通調陰陽[9]。筆者認為,從劉力紅教授解釋的開合樞氣化角度來看,闔機不調而陰氣消潛不足、陽氣復升不及同樣可導致陰過度成形而陽化氣不及,形成機體內異形之物,并且隨著此平衡穩態的不斷破壞,癌瘤持續生長失控。亦有學者根據《內經》“厥陰之上,風氣主之”理論及腫瘤轉移“內風”學說,推斷惡性腫瘤轉移的相關病機為厥陰風動挾痰、瘀毒流竄[10]。
2 烏梅丸治療腫瘤機理分析
2.1 重塑闔機,調和陰陽 烏梅丸為厥陰病之主方,柯韻伯評價其“寒熱并用,攻補兼施,通理氣血,調和三焦,為平治厥陰之主方”[11]。筆者認為,烏梅丸調和陰陽之功效可從《內經》“陽化氣,陰成形”理論考慮。陰之消潛收斂不足即是陰成形太過,故而生長失序形成“死肌”“惡肉”,臟腑陽氣升發不足,痰瘀毒等病理產物內生,陽化氣不足與陰成形太過相互影響,即是陰陽失和,進一步加劇惡性腫瘤生長。烏梅丸突出地體現了調理闔機的功效,通過主藥烏梅味酸而主合,配黃連、黃柏以苦瀉堅陰、收納陰氣,干姜、細辛、當歸、附子、花椒、桂枝辛溫大熱使陽氣升復,共助厥陰陽復陰闔,從整體上恢復厥陰闔機。因此,烏梅丸治療腫瘤的途徑是調和陰陽,使機體恢復“陽化氣,陰成形”之平衡。
2.2 溫補肝臟,燮理陰陽 國醫大師李士懋認為,厥陰病的本質是肝陽虛導致的寒熱錯雜證,其主方為烏梅丸,治療亦應在溫補肝臟的基礎上寒溫并用,燮理陰陽。李老認為烏梅丸中附子、桂枝、干姜、花椒、細辛皆具辛溫之性以溫肝陽、助“肝用”;烏梅、當歸酸以入肝而補“肝體”;人參補五臟六腑之氣以益“肝氣”;黃連、黃柏瀉肝陽虛不得升發所致之相火郁熱。故全方于補肝的基礎上,寒熱并調,燮理陰陽。同時,李老根據多年臨床經驗明確提出了烏梅丸的應用指征:脈弦按之減即為肝陽餒弱之脈,同時臨床癥狀具備由肝陽虛所引發的一二癥,如精神萎靡、易驚善慮、頭痛頭暈、吐利嘔惡、食少泛酸等,即可用烏梅丸加減以治之[12]。筆者臨床常參考李老應用烏梅丸經驗治療胰腺癌、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腫瘤并取得一定療效,考慮與消化道腫瘤多表現為肝陽虛寒熱錯雜證有關,肝陽餒弱則見乏力、納差、腹脹、腹瀉等臟寒證,陽郁化火則見口干、口渴、吐酸、便秘等郁熱證。其中,胰腺癌上腹飽脹不適、腹痛、食欲下降等癥狀與烏梅丸證最為相似,且胰腺癌具有易出現肝轉移的特性,臨床如能通過辨證靈活加減應用可明顯緩解患者不適癥狀,延緩病情發展。
2.3 暢達氣機,平和陰陽 氣是構成人體的基本元素,氣化是氣、血、精、津液之間相互轉化的原動力,機體正常生理功能的維系,有賴于氣規律性的升降出入運動。如因各種原因出現氣化失常,機體則會出現氣滯、氣郁、氣逆等病理狀態,氣、血、精、津液的生成輸布就會發生異常,體內出現濕、熱、瘀、毒等病理產物,進而出現微環境失調,導致各種疾病發生,包括惡性腫瘤。花寶金教授認為六淫、七情、飲食等因素導致的氣化失常才是腫瘤產生的先決條件,因此提出“調氣”以至平和應是防癌治癌的重要著眼點[13]。彭子益在其《圓運動的古中醫學》[14]中提出:“烏梅丸中附子、蜀椒、細辛溫水寒而培木氣之根,黃連、黃柏清火熱以保木氣之津,桂枝、當歸溫木氣以息風氣,人參、干姜以溫中而補土,烏梅則大生木液而補木氣,水溫火清,木和土復,陰陽平和,運動復圓。”從烏梅丸藥物性味來看,烏梅味酸,與味苦之黃連、黃柏相伍則“酸苦涌泄為陰”,附子、干姜、花椒、細辛、桂枝相合則“辛甘發散為陽”,人參、蜂蜜之甘則補中調和藥性,全方通過辛開、苦降、調中以平和陰陽,暢達氣機。臨床研究證實“調理氣機法”對肺癌患者的治療,尤其是在改善癥狀方面有明顯效果,并且此法對身心癥狀、呼吸系統癥狀的改善優于臨床常用的“扶正抗癌法”[15]。烏梅丸為治療厥陰病之主方,暗含調暢氣機、平和陰陽、破除寒熱格拒之意,對晚期腫瘤患者因臟腑氣血陰陽失調、陰陽不相順接、氣機升降乖戾而出現的諸癥大有用武之地。
3 驗案舉隅
方證對應即“有是證用是方”。“方”是方劑,是治療的主要手段措施;“證”是證據,是診斷的依據憑證。近代傷寒大家劉渡舟先生在其《方證相對論》一文中提出:方證是學習傷寒論的關鍵,只有先抓住主證才能突出辨證的特點[16]。從厥陰病機角度分析,厥陰為兩陰交盡、由陰出陽階段,若陰陽氣不相順接則陽氣難出,無法通達彌漫于人體上下內外、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人體氣機升降出入便不能保持如環無端的狀態,因而化生痰濕、瘀毒等病理產物,郁久成積。因此,“陰陽氣不相順接”即陰陽失和應為腫瘤發生的關鍵病機[17]。厥陰者,陰之極也,寓意兩陰交盡,一陽初生,與之對應的時象為冬至一陽生,在一日之時則為凌晨1~3時,《傷寒論》曰:“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顧植山教授認為“六經病欲解時”體現了辨證的時空方位性,“欲解時”應理解為“相關時”[18],因此臨床各種疑難雜癥,但見在凌晨1~3時出現或加重,皆可選擇烏梅丸[19]。筆者于臨床分別依據厥陰病主證、厥陰病病機及厥陰病欲解時進行辨證,酌情選用烏梅丸為主方治療腫瘤相關病癥,取得較好療效,現各舉1則驗案介紹如下。
3.1 辨厥陰病主證
案1.吳某,女,68歲。2017年11月24日初診。
主訴:胰腺癌綜合治療后半年,上腹隱痛1個月。患者2017年6月因“血糖控制不佳”至當地醫院就診,查血CA199>700 U/mL,上腹部CT示:胰腺體部占位伴遠端胰管擴張,考慮腫瘤性病變。后于2017年7月、9月行2個周期吉西他濱化療,期間出現Ⅱ°骨髓抑制,予對癥治療后好轉。2017年10月至11月行胰腺病灶放療。刻下:患者中上腹隱痛不適,夜間尤甚,口苦、口干,喜熱飲,時有反胃,無腹瀉,無惡心、嘔吐,入睡困難,納食不振,大便干,小便清長量多。舌暗紅、苔薄白,左關脈弦弱。西醫診斷:胰腺癌放化療后;中醫診斷:腹痛(上熱下寒、氣郁血滯證)。治以清上溫下、行氣化瘀、通絡止痛。予烏梅丸合金鈴子散加減。處方:
烏梅30 g,黃連6 g,黃柏6 g,熟附片6 g,桂枝6 g,細辛3 g,花椒6 g,干姜6 g,當歸10 g,黨參10 g,川楝子10 g,延胡索10 g,丹參10 g,腫節風10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2017年12月1日二診:患者諸癥改善,腹痛、反胃減輕,口干明顯緩解,大便仍數日一解。故在初診方基礎上加肉蓯蓉10 g、白術30 g,繼服7劑。
患者病情控制可,生活質量明顯提高,門診堅持中醫藥治療,隨訪1年后終因病情進展去世。
按:《傷寒論》厥陰病提綱:“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本案患者上腹部疼痛不適(心中疼熱)、口干(消渴)、反胃(氣上撞心)、納食不振(饑而不欲食)均屬厥陰病主證范疇。厥陰主風木,內寄相火,喜條達而惡抑郁,邪犯厥陰則木郁化火,在上見口干、口苦;人體胰腺又深居胃之后方,郁火上灼胃脘故見上腹隱痛;木郁土虛則饑不欲食;肝陽郁遏不得升發,陽氣不得舒布,則見喜熱飲而小便清長等寒證。故處方從厥陰病主證入手,選取烏梅丸為主方,寒溫并用、清上溫下。方中重用酸收之烏梅補肝體以制肝用,疏風木之郁結;黃連、黃柏苦寒以瀉郁熱;附片、桂枝、細辛、花椒、干姜辛溫以復肝陽;當歸養肝血以滋肝體;黨參培土以御木郁;金鈴子散(川楝子、延胡索)為治療氣郁血滯而致諸痛的常用驗方,不僅具有抗炎、鎮痛的藥理作用,還可能具有顯著的抗癌功效[20],惡性腫瘤終屬難治頑疾,故稍佐之以增強理氣活血止痛之功。二診時患者諸癥減輕,仍大便難解,考慮陽氣舒布不及,加肉蓯蓉補腎助陽潤腸、白術運化脾陽,同時二者又可緩烏梅澀腸之性,因而取得良好療效。
3.2 辨厥陰病病機
案2.張某,女,62歲。2018年8月12日初診。
主訴:宮頸鱗癌放化療后近1年,間斷便血半年。患者2017年9月因陰道出血至當地醫院就診,行相關檢查后診斷為“宮頸鱗癌ⅢB期”,自2017年9月起行4個周期化療,2017年12月始行放療及腔內后裝放療(劑量不詳),放療于2018年1月結束。術后即出現腹痛、腹瀉伴便血,行腸鏡等相關檢查后考慮為“放射性腸炎”。刻下:患者神清,精神尚可,口干欲飲,小腹間斷冷痛,無腹脹,無陰道出血等,大便次數多伴出血,肛門灼熱不適,小便黃伴尿急,納食不振,夜寐欠安,舌紅、苔薄微黃,脈弦澀。西醫診斷:宮頸癌放化療后,放射性腸炎;中醫診斷:泄瀉(濕熱下注證)。治以清熱燥濕、升清止瀉。予葛根芩連湯合芍藥甘草湯加減。處方:
葛根24 g,黃芩12 g,黃連6 g,白芍15 g,生甘草6 g,側柏葉9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2018年8月19日二診:患者訴肛門灼熱、便血等癥狀有所緩解,但仍見大便次數多,6~7次/d,不成形,仍覺口干,時時欲飲,小腹冷痛。予烏梅丸加減。處方:烏梅50 g,黃連10 g,黃柏10 g,黃芩炭10 g,熟附片3 g,桂枝3 g,細辛3 g,花椒6 g,干姜3 g,當歸10 g,黨參10 g,仙鶴草30 g,紅藤10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2018年8月26日三診:患者腹痛、口干明顯減輕,大便次數減至2~3次/d,3~4 d間斷出現少量便血。
后守上方治療1個月,癥狀基本消失。患者至今健在,定期隨訪,復查宮頸癌相關指標均在正常范圍。
按:患者初診時診斷為放射性腸炎,考慮放射線屬中醫學“熱毒之邪”,故按常規清熱燥濕思路治療,但效果并不理想。二診時從病機考慮,口干欲飲、肛門灼熱、小便黃伴尿急為“熱”,小腹冷痛為“寒”,與厥陰病烏梅丸證寒熱失調、陰陽失和之病機相符,而腹瀉僅為惡性腫瘤及放化療導致的氣機紊亂、陰陽失和的癥候之一,與單純的濕熱下注型腸炎有所區別,應辨為陰陽失和、寒熱錯雜,故改以烏梅丸為主方。方中重用烏梅取其酸收澀腸之性;黃芩炭炒以增強清熱燥濕、涼血止血之力,細辛、花椒辛溫以散寒溫臟止痛,稍佐附片、干姜、桂枝溫中散寒,各藥共奏辛開苦降、寒熱并用之功;紅藤味苦性平,能解毒消癰、活血止痛、祛風除濕,仙鶴草別名脫力草,尤善收斂止血、止痢、補虛,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二藥除有止血抗炎的作用外,尚具有一定的抗腫瘤功效[21-22],因此在辨證選取烏梅丸為主方的基礎上,辨病應用此二藥以解毒祛瘀、補虛止血,終獲良效。放射性直腸炎(腸澼)中醫診療專家共識也將烏梅丸列為其中寒熱錯雜證的主方[23]。
3.3 辨厥陰病欲解時
案3.徐某,女,55歲。2019年2月13日初診。
主訴:宮頸鱗癌術后1月余,反復失眠2周。患者神清,精神欠佳,無腹痛及陰道出血,口干欲飲,口舌反復生瘡,心煩,睡眠不佳,眠淺,每日凌晨1~2時易醒,自覺下肢畏冷,大便尚可,夜間小便頻,納食一般,舌紅、苔薄少津,脈弦澀,左關脈沉取弱。西醫診斷:宮頸癌術后,失眠;中醫診斷:不寐(陰陽失和、陽郁內熱證)。治以溫肝解郁、調和陰陽。方用烏梅丸加減。處方:
烏梅20 g,黃連10 g,黃柏10 g,熟附片9 g,桂枝6 g,細辛3 g,花椒6 g,干姜6 g,當歸10 g,黨參10 g,郁金9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2019年2月20日二診:患者諸癥明顯改善,自覺下肢較前溫熱,能連續睡5 h以上。
后患者開始行術后輔助化療,一直于門診復診,病情穩定。
按:該患者本因腫瘤及手術后機體出現厥陰病之陽郁內熱、陰陽失和狀態,肝陽郁則肝失條達,郁而不暢,甚至化火,《黃帝內經·病機十九條》云:“諸逆沖上,皆屬于火”,故癥見口干心煩、口舌生瘡,“諸厥固泄,皆屬于下”,陽郁不達同時又可見下肢畏冷、夜間尿頻,出現厥陰病上熱下寒的典型癥狀。《靈樞·口問》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由此可見不寐證的中醫病機總屬陰陽不交、陰陽失和,邪氣阻礙陰陽的交合致陽不入陰則不寐。本案患者每日定時于凌晨1~2時易醒,受顧植山教授厥陰病欲解時理論啟發,處以烏梅丸加減溫肝清郁熱、調和陰陽,加郁金解郁安神,全方酸苦涌泄以合,酸辛疏導以開,辛開苦降調整人體全身氣機,促使陰陽趨于平衡,恢復厥陰之常態,則諸癥得以緩解。
4 結語
綜上所述,惡性腫瘤屬于臨床復雜難治性疾病,中醫藥治療惡性腫瘤臨床多沿用扶正祛邪的理念,主張以臟腑、八綱辨證治療,而傷寒六經辨證思想應用得當亦可取得顯著療效。厥陰病從病位、病機、主證等多維度與惡性腫瘤多因素交互致病、易侵襲轉移的特點有著潛在聯系,如能更多地引入現代研究方法將大大增強其理論依據。烏梅丸是厥陰病的主方,將其應用于惡性腫瘤及其相關疾病的治療,能有效控制病情,緩解患者不適癥狀,提高生活質量,臨床應以陰陽為基本大綱,辨清寒熱主次,靈活調整應用。如案1中患者寒證更突出,因此加重了方中辛溫藥的用量;而案2中患者熱證較明顯,故較原方中黃連、黃柏的劑量有所增加。雖然厥陰病與腫瘤可能存在一定聯系,但辨證論治仍是中醫臨床的核心思想,在使用烏梅丸治療腫瘤及其相關病癥時仍應辨明患者癥情是否與烏梅丸證的病機、主證、欲解時等特征相符,切不可生搬硬套、刻舟求劍。烏梅丸治療腫瘤的取效提示我們,中醫藥治療腫瘤除了扶正祛邪,同時也應重視調節人體陰陽與氣機,筆者認為其客觀機制可能與改變患者腫瘤微環境有關,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