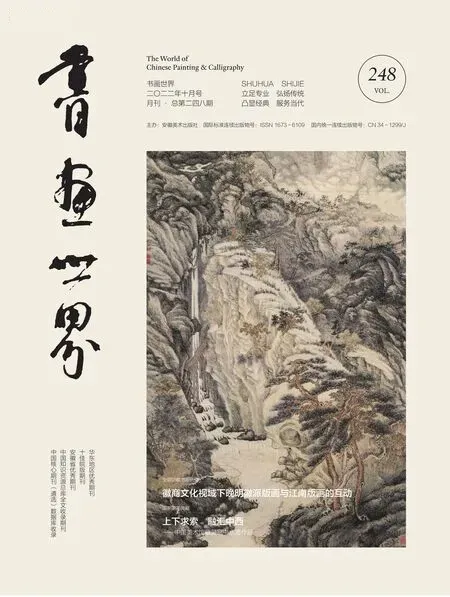羅聘《鬼趣圖》中形神的隱喻研究
文_劉雪
湖北美術學院中國畫系2020級研究生
內容提要:《鬼趣圖》是清代畫家羅聘的畫鬼佳作。本文通過分析畫中的情節內容與鬼怪形象,結合當時社會現象、世人需求及時代背景,并根據對后世題跋的研究,梳理出畫中形與神背后的審美趣味;以霍寶才收藏的《鬼趣圖》畫面內容為主要參考,探索《鬼趣圖》背后隱含的時代內涵。

清 羅聘 鬼趣圖尺寸不詳1771 霍寶才藏
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畫家羅聘曾自云:“凡有人處皆有鬼,鬼所聚集,常在人煙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稀。”其思想與畫作結合促成了《鬼趣圖》的出世,羅聘對鬼怪們的形神諳熟于心,以寫實與夸張相結合的手法塑造出生動鮮明的鬼怪形象。清乾隆時期,社會上流行鬼事怪談。羅聘上京城后,受時風影響,便開始創作符合大眾的審美需求的鬼怪題材作品,形象怪異別致、個性突出。他借鬼怪形象描繪人間百態,其作品的藝術魅力在中國人物繪畫史上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羅聘與《鬼趣圖》
羅聘,字遯夫,號兩峰,祖籍安徽,出生在揚州,年輕時得到金農的賞識,拜金農為師。他擅長畫人物、山水、花卉,在“揚州八怪”中被稱作是“五分人才,五分鬼才”的畫家。傳說中他有著綠色眼眸,他詭稱自己可白日見鬼物。羅聘創作出多本《鬼趣圖》,轟動南北畫壇。其中,流傳至今的《鬼趣圖》有三個版本,分別是藏于香港藝術館的手卷本、方聞舊藏的折扇及霍寶才私人收藏的段本[1]。其中霍氏收藏的圖卷是羅聘三上京城隨身攜帶的版本,本文將根據此版本進行探析。
乾隆時期,社會繁榮,市民消費文化的需求體現在繪畫上,就是畫家群體追求標新立異,尋求突破傳統,注重表達天性和創作的意趣。當時“文字獄”興起,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畫家的創作傾向,也影響到揚州畫壇。1771年羅聘初上京城,爾后結交許多學者高官,并因當時王椷的《秋燈叢話》、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樂鈞的《耳食錄》等鬼怪題材文學的流行影響,開始創作一系列的《鬼趣圖》,因此名噪京師,并得多位名流題跋;1779年羅聘二上京城,但停留十分短暫,當時其妻已病重,待其歸時,早已天人相隔;1790年羅聘再次前往京城,當時他在揚州已頗有盛名,他穿梭于達官貴胄之間,《鬼趣圖》第二次成功吸引諸多名流題跋,但他依舊并不寬裕。法式善曾在詩中描述羅聘在京城的生活,“灶炊茶煙斷,墻出石墨干。雪中蕉葉好,畫向低頭難”[2]。羅聘鬼怪題材的創作,是時代與文化觀念的產物。
霍氏收藏的羅聘《鬼趣圖》共八幅,共描繪了十九個造型各異的鬼怪形象,每幅少則由一個、多則由四個鬼怪形象組成,內容互不重復,經裝裱后以手卷冊頁的形式存在。畫中的鬼怪形象形態各異,造型經過變形,夸張而傳神,凸顯出筆墨在視覺上的情緒感,使得畫面表現出戲劇化的暗諷效果。煙霧繚繞的環境中每個鬼怪面目離奇,似真似幻中顯露驚恐、諂媚的神情。這些鬼怪有的呈靜止低聲細語的狀態,有的前后奔走,盡顯鬼魅之感。鬼怪的手和腳的描繪也各不相同,在五官、神態、衣著、頭發等細節的刻畫上極富變化,每幅中的鬼怪之間都有交流。畫面雖簡省了背景的刻畫,卻清晰地交代出了內容,引人遐想。
二、“形”的符號化
符號化在這里指藝術家將思維賦予描繪對象以形式,并運用藝術手段提煉出能夠表現情感的藝術造型,使描繪的對象更容易被受眾認識。符號化有著可識別和不可復制的特征,藝術家創作中的個人風格特征可以理解為藝術家自身獨具特色的符號,將來自生活中的素材和概念通過美學的形式,形成與眾不同的、獨特的且不可復制的個人符號。在繪畫中,符號化體現在畫家創作的個性化表達手法帶給受眾視覺感受上的獨特性。當然,繪畫作品的符號化不僅僅是帶給人們視覺上的震撼,它更多的是畫家對客觀現實的本質認識及內心情感提煉后的符號化。個人主觀思想意識的不同,是每個畫家創作出個人風格繪畫作品的重要因素。
“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3]因為鬼怪沒有具體的形態,畫家可以把他們畫成任意形態。在追求形似的繪畫風氣下,很多畫家將人形賦予鬼怪,畫中的鬼怪形象便有了世人的影子。不同時期鬼怪題材的創作都有著各自的時代特色與符號。唐朝吳道子《天王送子圖》中鬼神的形態是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演變的結果;南宋李嵩《骷髏幻戲圖》中兒童與骷髏的互動描繪,展現出生與死的對峙;元代龔開《中山出游圖》中的鬼怪以人的形態存在,充滿荒誕、詼諧的趣味,但其中又飽含著無奈,表達出了對當時社會的憎惡嘲諷;明代戴進《鐘馗雨夜出行圖》中鬼怪簇擁下的鐘馗,威嚴兇狠,凸顯出畸形的人格、心理;清代金農、羅聘、黃慎等畫家均有鬼怪題材創作,其中羅聘的《鬼趣圖》尤其突出,其筆下的鬼怪多一分無形,少一分無意。《鬼趣圖》中形的符號化延伸了畫面內容的圖像多樣性,主要表現在造型方面。畫中的鬼怪“角色”形體胖瘦不一,他們的互動之態引人遐想。他們的形態夸張,有拄拐的矮鬼、四肢修長的綠發鬼、頭大身小的大頭鬼、以傘為中心游戲的鬼。畫家通過變形夸張的姿態表現出每個鬼怪的獨特之處,形成豐富多彩的鬼怪世界。但縱觀整體,我們可以發現畫中無論什么形態的鬼怪都帶著凄涼之感,也許只有生活在黑暗之處的畫家才能創作出有悲涼氛圍的畫作;也可以看出羅聘對社會百態細致入微的觀察。他將人生經歷和對社會現實的情感態度融入《鬼趣圖》的創作語言中,使作品具有了特殊情感。鬼怪“形”的符號化特征也表現在技法、線條、筆墨等繪畫語言中。技法上,充分運用水墨的暈染效果,先潤濕紙張,在紙面未干時細筆施墨勾畫鬼魅的形態,畫面鬼怪形象與背景暈染形成實與虛的對立關系,暈痕自然形成神秘的氛圍,自饒別趣;線條上,取法陳洪綬白描人物畫的高古意蘊,在濃霧渲染中簡練勾勒,使得相互滲透,鬼怪形象似取自市井人物,身形簡單僅勾輪廓以成,造型簡練,線條沒有明顯的粗細變化,顯現出鬼魅來回穿梭的靈趣與鬼怪身影婆娑的疏離感;筆墨上,墨色因濕潤而暈開,墨氣的渲染增加了恐怖的意境。《鬼趣圖》畫面簡潔直白,鬼的姿態和表情刻畫精細到位,讓人遐想;衣紋流暢,濕紙墨線勾勒,擬人的創作手法,獨具一格;鬼怪之間的關系,引人想象,有畫家自我的符號化語言。這種形態上的夸張,是畫家臆想的客觀表現,耐人尋味。
三、“神”的趣味性
《歷代名畫記》中記載:“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后全。”魏晉顧愷之提出“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以形寫神”,強調繪畫作品要注重傳神,畫面才能生動有趣。“神”是畫作融入內涵與畫家靈魂的表達,這使得“神”有了更多的內涵。《鬼趣圖》中“神”的趣味性,不僅從畫面中筆墨的變化、造型的抽象表達得以顯現,而且延伸到了作畫者對社會現實的暗諷。首先,鬼怪的五官神態表達出不同的故事情節。如畫中有兩鬼竊竊私語;旁邊另一鬼在偷聽,手中拿著的花朵,仿佛表達鬼怪之間的愛情。神態是個體內在的表現。在中國古代繪畫中,早期鬼怪題材的創作,多表現簡單,是為宣傳宗教或政權服務的表達方式。在后期的發展中,鬼怪題材的創作逐漸轉向神態多樣、趣味濃重。其次,《鬼趣圖》中“神”的趣味性可以體現在形象刻畫的夸張表現上。羅聘根據現實中的人物形象進行夸張變形,用線勾勒得極為簡練,同時又描繪得極具故事性。畫家對故事的闡釋是其主觀情感的表達,讓畫面的趣味性再次提升。羅聘通過對社會時事隱喻暗諷的創作方式,讓鬼怪的形象更豐滿,神態更生動。傳說是一位張姓的姑娘被衙役調戲后,羅聘上前幫助反被痛打,心中憤怒,便作多幅鬼怪畫張貼于官府門前,畫中女鬼張牙舞爪,使得縣官衙役們都很恐懼。
在清政府統治下的漢人多受壓制,羅聘創作的畫中鬼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正如大多數人的處境,因此反映“人趣”的《鬼趣圖》被世人接受。所謂“鬼趣”重在游戲人間“趣”的表達,將鬼怪人格化,鬼怪的神態中都透著人情味。鬼怪題材的創作在中國美術史上有著諸多佳作。早期的鬼怪題材作品多是圍繞外在形體來描繪,缺乏內容與內涵,多是單純為宗教或政權服務;宋末元初,鬼怪題材畫作才慢慢表現出現實意義。羅聘的鬼怪題材作品表達的現實情趣更加深切濃烈,形象更加人性化,作品的“神”也更有趣味性。《鬼趣圖》中題跋眾多,題跋存在的趣味性表現在詩與畫的相得益彰。每個題跋都是題寫者對畫面故事情節與情境的聊表自得,如吳楷所題“幽人具冥懷,涉筆便成趣”。鬼怪題材的作品是畫家主觀想象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表現畫家的個人趣味。
四、圖像背后的時代隱喻
關于鬼怪的圖像發展,遠古時代人們認為鬼神皆是來自大自然中未知領域的存在,并在民間口口相傳至今。《禮記·祭義》中記載“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說鬼是人死后的靈魂;儒家則“事鬼敬神而遠之”,認為鬼神超脫于骨肉形骸,隱于世人之間,是一種極其微妙的存在;道教認為鬼怪是民間巫術,修道可由鬼變仙;佛教有六道輪回之說,認為鬼是對人死后依生前牽引至六道輪回之中,善惡在六道的流轉中得到相應的因果報應。中國歷來有著喪葬文化,很大程度促進了鬼怪文化的發展[4]。在朝代更迭中,統治者將鬼神之說作為政權統治的手段,以此鞏固正統。因此,在不同朝代的社會環境影響下,鬼怪的內容與形式便不盡相同。隨著文人畫的發展,畫家將個人情感融入畫面中,把自我個性通過畫面展現,鬼怪題材的創作背后所蘊含的內容也隨之豐富。鬼怪文化在士大夫群體中流行,他們認為鬼怪是人間的鏡子,反映的是世人的心理狀態、行為活動。畫家們借助“鬼”的形象和故事警醒和教化世人。當今社會也有人認為鬼怪是受盡永恒折磨的存在,以此寓意來震懾人心、激發世人對惡畏懼、積極從善。
《鬼趣圖》上的大量題跋揭示出當時社會借鬼怪形象諷刺社會的潮流,所謂的隱喻主要體現在對社會時事的暗諷。如張曾題“天生屈子多離憂,國殤山鬼愁復愁”,將屈原的詩歌與羅聘的鬼怪畫作相比較,認為屈原的騷體中引用美人香草和神話傳說來比喻胸中情懷,表達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和暢想將來的美好,同時又以鬼怪來暗示現實的殘酷;蔣士銓題“侏儒飽死肥而俗,身是行尸魂走肉”,以矮胖鬼暗諷貪婪享樂、趨炎附勢的小人;張問陶題“對面不知人是骨,到死方信鬼無皮”,將畫中骷髏暗諷為喪失骨氣之人。《鬼趣圖》中所繪眾鬼各有凄慘之狀,例如鬼怪形象胖瘦之間的對比,是對社會貧富差距的批判,這與當時社會的官僚風氣有很大聯系,是對官場的暗諷,對污濁丑相的揭露;畫面中的鬼越來越多,鬼氣凜人、夸張嗔怪、陰森縹緲,表現出了社會的陰暗。形態各異的鬼怪形象皆是畫家隱晦的表達,對鬼怪世界的刻畫喻示著畫家所處的世間之景。畫家通過作品直抒胸臆,不僅表露了心中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在暗諷中帶著些許期許之意。
結語
隨著科學的發展,從現代的視角看,鬼神只是虛構的存在,是人們特殊的情感寄托。對于鬼怪,羅聘將他“看”見的鬼怪描繪出,讓大家心中有了具象的形象,寫實與抽象結合,形與神貫穿。在對鬼怪的時代審美風尚中,他賦予了《鬼趣圖》更多隱秘的意味。在鬼怪形象創作的歷史變遷中,通過對羅聘《鬼趣圖》的研讀,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形與神在創作中的作用,形象固然是夸張與變形的,但萬法自然,都是畫世人、畫自我,都是畫家表達個人思想的手段。羅聘的《鬼趣圖》在很大程度上也豐富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價值,拓寬了藝術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