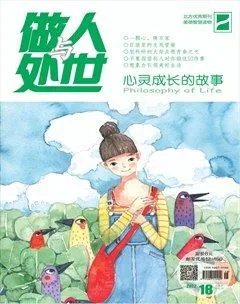整理人生
喬貝
尊重自己所選擇的職業,你就是強者
西卡是在28歲時下定決心當遺物整理師的。雖然在父母的眼中,這是一個很突然的決定,但西卡知道,這是她深思熟慮后的選擇。
那是在2014年,當時,西卡被查出體內有一顆腫瘤。等待檢查結果的那幾天,她問自己:“我能在一個青春剛開始的時間留下什么?”什么也留不下來,能留下的好像只有物品。那是她第一次想到物品和人的生命之間的關聯。
還有一次是在2016年,西卡看了一部日劇《我的家里空無一物》。女主人公是個扔東西“狂魔”,家里沒有電視,沒有桌椅,待客時要從收納柜中拿出那種日式盤腿椅,拖地時整個屋子都是空的。西卡一下子被震撼到了:“原來生活還可以這樣過!”
如今回頭看,西卡認為,那部劇主要講的其實是收納而非整理。“收納單純強調物品擺放,整理是梳理自己的物品、事件、人際關系等,是在我們的生活甚至生命中建立一個思考體系。”自那之后,她開始對“整理”有了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有些人可能只經歷一件事情,就很快蛻變,對我來說,我需要一個過程。”西卡說。
2018年,西卡的眼部需要做一個小手術。刀片揮舞,她忍不住紅了眼眶。主刀醫生看出西卡心里的恐懼,囑咐護士握緊她的手,還像哄小孩一樣假裝“兇”她:“你眼圈不要紅,你眼圈一紅,我就知道你要哭了哦。你已經是大孩子了,不能像小孩子一樣那么容易哭。”西卡很感動,主刀醫生一天要接待很多病號,可能十幾分鐘就換一個,“但像他那么大腕兒的醫生,還在很細微的方面關懷患者,給我一種安定感,這樣的人太有力量了”。
這件事對西卡的觸動很大,她想做一份工作,一份可以直接幫助到別人的工作。西卡把這個想法講給朋友聽,朋友趕緊勸她,說任何一個職業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幫助別人,以自己的方式為社會創造價值。話是這么說,可西卡還是說服不了自己,她待在辦公室里就覺得透不過氣來。
不久,西卡就辭去了BAT大廠的工作,從整理咨詢師做起,為成為遺物整理師做準備。那時,西卡還擔心一旦告訴委托人自己也做遺物整理,會把好不容易才找過來的委托人都嚇跑。然而后來的發展出乎她的意料。“不管是委托人,還是身邊的人,我突然發現我可以和很多人聊死亡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并鼓勵我。”最近,西卡剛接到一個遺物整理的委托,此時距離遺物主人逝世已近十年。“父母都已經走了,子女不住在那邊,他們又不知道怎么面對,所以擱置多年,那個地方就像被封印了一樣。”西卡說。
做遺物整理師久了,她發現,來委托的人都有一個共性: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這時,西卡就會向他們拋出一個問題:“促使你找到我的最大動力是什么?”回答五花八門。有年輕人說自己特別難過,心情已經連續低沉好幾個月了,不知生活如何進行下去。也有委托者認為自己已經走出困境,希望通過整理遺物化解家人的悲傷。還有老人年齡大了,沒有其他家人,問西卡,他能在生前做些什么。又或者老人去世后,家中子女找到西卡,想知道老人遺物有多少,方便分割。
一般聽完委托人的回復,西卡心里就已經有了底。如果是情感寄托類的遺物整理,她會花大量時間和委托人溝通,一件一件確定遺物的處理方式,尤其是照片、日記、信件等珍存了過往記憶的物品,西卡會特別注意。如果是涉及法律和隱私的遺物整理,她則會更側重于遺物清點,將每一項都仔細地記錄在案,甚至不會移動全部物品。
在西卡看來,“遺物整理”是一個很宏大的概念,它不只指向“身后”,還應指向“生前”,涉及社會學、醫療保險、財產分割等多個領域。她以日本紀錄片《無緣社會》為例,“老齡化、少子化、不婚這樣的大環境,是社會學領域的問題;背后還涉及這些老人怎么安排自己的臨終護理,屬于醫療領域;還有養老金安排,過了多少歲,能領多少錢,又屬于養老保險方面的知識。他們要分配的東西和事物太復雜了,誰來給他們整理?”為此,過去幾年,西卡看了很多資料。她記得自己看的第一本講述生命的書是《活出生命的意義》,作者是弗蘭克爾,一個從納粹集中營里走出來的心理學家。
不看書時,西卡就看紀錄片,講的都是生老病死、臨終關懷等生命命題。她有意識地讀各種法律資料,2021年遺產管理人制度確立后,她還研讀了《民法典》。這些塑造了西卡的生死觀。她從不避諱談死,也不認為“遺物整理”是一件冰冷、消極或者憂傷的事情,相反,“它是溫情的、默默的、克制的”。
對應到遺物整理的過程中,西卡定了一條規矩:把情感的閘門關掉,保持理智與清醒。你不能哭哭啼啼,這樣會給對方帶來麻煩。西卡和委托人一起整理遺物,看到逝者年輕時的照片、興趣愛好,聊著聊著兩人會相視一笑,“那一刻是幸福的”。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