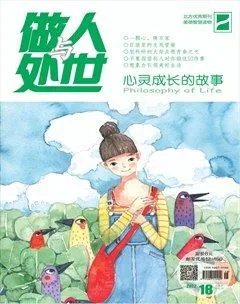“唇語”女孩
姚春華

她是“2021感動廈門十大人物”之一;她靠讀唇語聽課,“一路開掛”考上博士,211本科學士+211碩士+985博士在讀——這是年幼失聰的趙蚰竹為無聲的青春交出的美麗答卷。
“90后”的趙蚰竹是遼陽市人。在她3歲上幼兒園后,老師多次反映:“這孩子總是不聽話,還自顧自地玩,說話也含混不清,是不是聽力有問題?”父母便開始帶著小蚰竹求醫,在北京同仁醫院,小蚰竹被確診為先天性神經性耳聾,有一點兒聽力,但會逐漸喪失。
診斷結果出來后,年輕的父母瞬間陷入痛苦的深淵。但不久,堅強的父母做出一個改變孩子命運的決定——“語言搶救計劃”。“我當時就像瘋了一樣,要趕在她全聾之前,教她學會張口說話。”趙蚰竹的母親回憶說。每天傍晚,她都會強迫4歲的女兒站在鏡子前,把嘴張到最大,雙手隨著聲音一開一合:“a——”即便戴著助聽器,趙蚰竹也很難聽清母親的聲音,只能學著張大嘴,渾身用力地從嗓子眼里擠出些聲音。母親又心急又心疼,只能繼續張大嘴,重復這個口型。每個拼音字母,都要數十遍、上百遍地教。就這樣,小蚰竹戴著助聽器,以微弱的聽力,在學齡前學會了拼音、速算、唇語和英語音標。
為了和時間賽跑,5歲的趙蚰竹提前一年上了小學。怕跟不上學校的學習進度,在母親的輔導下,趙蚰竹每天晚上都提前預習課本內容,并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聽課”方式。她坐在教室第一排,上課時緊緊盯著老師的口型,生怕錯過老師說的每一個字。通過讀老師的唇語,并結合自己的預習內容,判斷老師的講課知識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就這樣,趙蚰竹很快適應了校園生活,學習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
趙蚰竹第一次徹底失聰是在小學三年級。她和同學玩沙袋時,直挺挺地向后摔倒在地,劇烈的碰撞,讓她瞬間失去了微弱的聽力。喪失聽力的趙蚰竹有時間大量地讀書。每次出門,她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書店,常常在那里一看就是幾個小時。大量閱讀讓她的寫作能力十分突出,從小學有作文課以來,她的作文幾乎都被作為范文。小學畢業考試前兩個月,趙蚰竹因感冒咳嗽,病情加重,眩暈不止,不得不到長春市一家醫院住院治療,直到考試前四天才回到學校。結果,她以全校第二的成績畢業,并受到校方的嘉獎。
三年后,趙蚰竹以優異成績考入遼陽市一中。高二暑假,趙蚰竹第三次住進了長春的那家醫院。“一想到十幾年的學習都要白費,她就很焦慮。”媽媽說。直到高考前一百多天,趙蚰竹才正式出院回歸復習狀態。時間緊迫,媽媽安慰她:“沒事,上大專也沒問題,實在不行就復讀一年。”趙蚰竹卻憋著一股勁,堅定地說:“媽,相信我,我能行!”
這一年,是趙蚰竹最艱難的一年,先后五次入院治療,每次一個月,幾乎整個高三階段都沒能正常上課。盡管如此,她仍不放棄。回到學校的趙蚰竹,坐在班級最后一排,為了趕上進度,她每天沉浸在自己的節奏里,從早到晚不停地刷題。“從早上9點,一直到晚上,我都不停地刷,因為我覺得我不比別人差。或許,我聽不見老師講課,但是我可以自己研究。”
經過上百個日夜的奮戰,趙蚰竹如愿考入東北農業大學水利工程專業。大學期間,她的成績一直保持在年級前列,屢獲獎學金。然而,好景不長,大四畢業前夕,她再一次徹底失聰,在長春的醫院里整整治療了一年,才逐漸恢復。
在治療期間,趙蚰竹也想過考事業單位、政府機關,但都由于身體原因,未被錄取。“我還是想考研。”下定決心后,趙蚰竹買來考研書籍,三個月內完成了全部課程的復習。最終,考回東北農業大學。在研究生期間,她連發6篇學術論文。2019年,趙蚰竹又考取9廈門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攻讀海洋事務專業。當初那個失聰的少女,如今已成為一名青年學者,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
趙蚰竹在學生時期曾寫過一篇題為《給海倫·凱勒的一封信》的作文,她寫道:“我曾經怨恨過老天的不公,怨恨過父母為什么給了我一雙失聰的耳朵。”如今,她更多的是感謝父母在她成長道路上所給予的愛。談及未來,趙蚰竹說:“北方陸地是我的故土,南方海洋是我的禮物,陸海統籌是我的歸宿。”她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創造著奇跡,在逆境中譜寫著靜謐而絢麗的人生。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