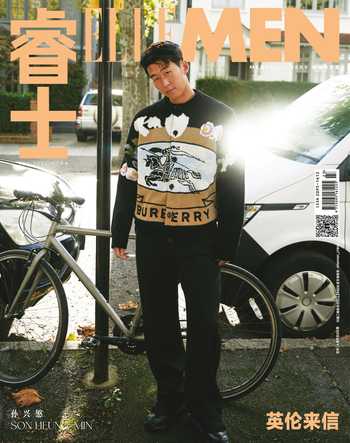蘇陽 用身體作畫的藝術家

蘇陽,中國當代音樂家、藝術家。
來自西部銀川。是首位在美國舉辦多媒體藝術展的中國音樂人。此次在翡翠畫廊的個展“生印——蘇陽的圖像預言”展出了他的16件布面油畫、34件綜合媒材作品以及影像作品。
花腔、秦腔、花兒(一種西北民歌形式),這是蘇陽的音樂中最與眾不同的地方。過去二十年間,他將西北土根性與音樂結合得爐火純青。他的音樂帶著一種來自西北的特有力量,從黃河延伸出來,流經土地,裹挾著最原始的純粹與粗獷的詩意,流進聽眾的心里。樂迷親切地稱他為“西北搖滾歌王”。
在臺下的蘇陽內斂安靜,甚至顯得有些局促。西北的土地賦予了蘇陽一種原始的力量,那些強爆發力的藝術表現形式似乎是他宣泄情緒的出口。與音樂類似,他的繪畫作品也有著強烈的視覺沖擊力。
蘇陽沒有刻意學習過專業的繪畫,只是小時候描摹過小人書,練過書法,迷過潑墨。2016年左右,蘇陽開始臨摹賀蘭山巖畫,用在Video Jockey(用作搭配音樂呈現的視覺畫面)的制作上,由此逐漸開始了抽象繪畫創作。
他的繪畫風格也是原始而純粹的。也許正是缺少了學院派的系統教學,蘇陽的繪畫更加追從內心,不為美術史、人類史、文化史這些概念所束縛。
拿來一幅兩米以上的畫布,用鐵鍬砸出大面積的色塊,顏色直接滲透到畫布里。有三四個月,蘇陽幾乎沒有用過傳統的繪畫工具,而是選擇布條或工地常見的工具,他戲稱自己是“泥瓦匠”,創作中他的身體和精神的結構,詮釋了創作行為本身。
對蘇陽來說,創作也是不斷產生缺點的過程。他作畫過程中幾乎每天都會重復的事,就是破壞。畫好的畫面,一旦他覺得不滿意,就會開始破壞畫面,全部涂掉。他說自己的畫都是“破壞出來的”,而這種破壞本身也是一種創作。直到出現打動他的東西,這種創作才會停止。一幅兩米左右的作品,是耗時最長的一幅作品,蘇陽創作了一個星期。
正如他本人所說,他的繪畫本質上是“利用身體進行創作,需要將身體全然展開,在夠得到的范圍內盡量舒展”,而自己作畫“就像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像是在工地里”。
這種勞動當然也離不開孕育他的土地。在做音樂的時候,蘇陽會在專輯封面用剪紙等明顯的陜北元素做設計。但在繪畫中,他想要體現出的黃河流域的表達方式,則更為隱秘。有些畫作受到秦腔的影響,更多的畫作則是無論如何修改都脫離不開黃色的基底。對他來說,一個人的成長和生活印記,都是刻在基因里的,很難遠離。
藝術對蘇陽來說就是一種生活。他希望自己通過藝術,這種富有精神的勞動,延續民間文化,找到生命的意義。因此,他也不為所謂的“個人風格”設限,在創作過程中一直尋找自己的藝術語言,一種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跨越時空的獨特語言,讓他能夠與全世界對話。

水冰草 綜合媒介 55×43cm 2021年

抗烙 布面油畫 122×170cm 2021年
Q&A
Q:無論音樂創作還是繪畫創作,你覺得能給你最多靈感的是什么?
A:其實對我來說,所謂的藝術創作是沒有那么格式化。我每天都會去摸琴,去發出一些聲音,而在這個過程中,他會自己出來一些東西在你的心里面。作畫也是一樣。我先動筆去畫,很可能在下一分鐘,也可能在明天,才會有不同的情緒,這是一個過程。當然在后期的時候,我需要有一些共性的手段,進行技術性的處理,但是前期沒有那么多預設。
Q:你是如何確立自己的繪畫體系的?
A:也經歷了一個時期吧。剛開始看一些抽象的東西,癡迷這些東西,肯定要受它們的影響。但是最終還是要走出來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尋找跟你最息息相關的東西,那才是建立自己語言的一個基底。但2016年至今,我作品的風格都是動態的,今年的繪畫也與之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
Q:從這種無師自通的繪畫過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A:繪畫其實是一個最好的認識自己的過程,畫的過程中你會慢慢發現,你對這個世界的了解還是太少,你對自己的了解也少。如果你要是全部用感受去畫一幅畫,和你用理性的思維去畫一幅畫,你進入的是兩個世界。
Q:這兩年創作心態有什么不一樣?
A:這兩年我的創作非常密集。2020年我出了兩張專輯,然后2021年發了一張電影音樂專輯。繪畫上畫了幾十張大畫,其實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今年好像反而量少了一些。
Q:你如何評價自己今年的作品?
A:今年的作品可能應該比去年還要更成熟一些。我覺得其實我們最后都要走向一種系統,只是每個人心中的系統不一樣。哪怕是瞎畫,也是一種系統,只不過是自己的系統。
Q:2016年,你發起了“黃河今流”文化活動,與多位藝術家跨界合作,融合了民間藝術形式和現代藝術形式,通過繪畫、影像、動畫等藝術媒介,展示了黃河流域的文化底蘊。這個計劃的現狀如何?
A:這個計劃沒有停止,只是因為疫情暫時擱置了。我今年還是要想辦法用更可行的方式去推進這個項目,比如能夠轉移到線上的就在線上呈現。相比2016年,它也會更加綜合,在多個藝術領域之間的協作性更強,也會更加完整。
Q:嘗試過這么多藝術形式之后,有沒有讓你覺得最自信或最舒適的領域?有想要嘗試的新形式嗎?
A:我對音樂最了解,畢竟做了三十多年,內在的邏輯性我更加熟悉。繪畫也還好,我不是靠繪畫出名的,也沒有什么壓力。未來也許還想嘗試裝置藝術,或多種材質的立體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