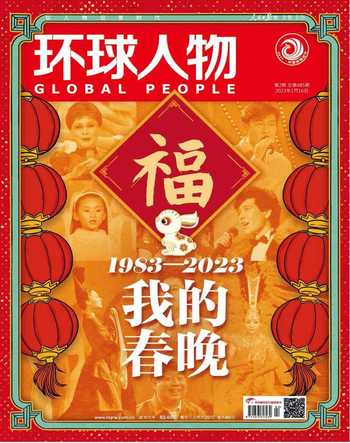新民俗養(yǎng)成記
劉舒揚 毛予菲

位于北京五棵松的央視“影視之家”,是最早感受到春晚的地方。去年夏末秋初,2023年兔年央視春晚在這里建組。半年的時間里,看著逐漸多起來的各種熟臉,“影視之家”的工作人員可以熟稔地推斷出春晚籌備的節(jié)奏:這是收集素材了,這是要挑節(jié)目了,這是拿設計方案了,這是聯系主創(chuàng)了。直至去年年底,明星藝人魚貫而入,好了,這是開始聯排了。
這套工作節(jié)奏,從上世紀90年代逐步形成,穩(wěn)定地延續(xù)至今。“影視之家”這個安營扎寨的地點,也是1996年固定下來的,從此春晚劇組結束了“居無定所”的日子。
現在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半年里,春晚的痕跡在生活中隱而不見,要到1月21日除夕晚上才會一瞥春晚的模樣。這正像一個隱喻:作為一個早已穩(wěn)固的存在,春晚很難像早期那樣,激發(fā)人們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人們在364天里都不太會想起它,但最終又在除夕這一天鄭重地面對它。
尤其是今年,太特殊了。起于1983年的春晚走過了整整40年,40年的潛移默化讓合家看春晚成了“全民默認程序”,成了我們集體構建的當代民俗。今年這個春節(jié)的特殊性還在于,這是許多人3年來第一個回家團聚的春節(jié)。還有什么比一起看場合家歡的春晚更能抒發(fā)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的感懷、紀念和重啟呢?
2023年的我們,期待著,準備著,在除夕夜“啟動”春晚。
今年1月5日,于蕾以2023年兔年央視春晚總導演的身份出席了一場發(fā)布活動,短發(fā),格紋禮帽,黑色外套配玫紅內搭,褲裝,是干練爽利的女導演形象。在此之前,她身上最知名的標簽是《國家寶藏》總導演和制片人。那是她一手打造的現象級綜藝節(jié)目,視頻點擊量超過40億。
于蕾春晚總導演的身份“官宣”后,帶著她名字的詞條很快上了熱搜,其中不乏網友們基于《國家寶藏》而發(fā)出的歡呼與期待——它非常具象地傳達出一名導演對于一檔綜藝節(jié)目的標準和要求。
比如,她很看重“故事”。有媒體曾問她,節(jié)目制作過程中有什么困難。“你們都愿意聽故事嘛,那我說個小故事。”她迅速給出一個時間、地點、人物、沖突、轉折等要素一應俱全的故事:“有不少明星嘉賓接到邀請時有恐懼感。梁家輝先生最開始的時候就說,我去跟國立老師聊文物,我會不會很傻?我完全不懂。段奕宏也說,我一個演員參加這樣的節(jié)目,我能干嗎?大家沒有見過這樣的節(jié)目,所以需要慢慢地、不停地溝通。等真正見到文物,他們才理解,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我在這里邊有不能替代的作用,我可以站在這兒聊一個完全無關自己的話題。”
“如果一個有價值的東西,變成一個傳播的節(jié)目樣態(tài)后,讓受眾覺得無趣,那理論上不會是這個東西的問題,一定是傳播的人的問題。”于蕾接受《環(huán)球人物》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過。為了傳播好故事,她會一遍遍洗練自己的表達,《國家寶藏》每一期,她至少盯著剪六七遍,熟悉到每一句話都能記下來。還不能剪得太“禿”,“要有‘氣口’,是活的、圓潤的,并且沒有廢話”,直到一句話也去不掉了,才算完成,“按照你覺得最好的邏輯、最好的節(jié)奏組合在一起,觀眾在看的時候,覺得這一切就是現場水到渠成的發(fā)生”。
于蕾是春晚的老朋友了。2011年5月,32歲的她接到任務,協助時任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總監(jiān)助理的哈文策劃召開一系列“春晚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工人、農民、學者、大學生……7場座談會留下了10萬字的會議紀要,最終由于蕾濃縮成8000字的建議匯總,作為當時春晚的一份創(chuàng)新指南。
那年6月下旬,哈文被正式任命為2012年央視春晚的總導演,于蕾成為哈文團隊中最早被確定加盟春晚的人,自此,她連續(xù)擔任了4年央視春晚的總撰稿,對春晚的定位、氣質、節(jié)奏等逐漸熟悉。
2015年于蕾還擔任了央視春晚的總設計,一支吐槽春晚的網絡配音隊伍剛好進入當年《我要上春晚》的總決賽,還出現在春晚直播前的一檔專題節(jié)目里。于蕾表示很“生氣”:“你們吐槽春晚,你們還吐槽得那么好!”鏡頭前的她大笑著說:“我們心理很強大,我們相信春晚其實不怕吐槽的。我們歡迎大家更精彩地吐槽春晚,我覺得那是大家對春晚的關注,是對春晚的愛。”
于蕾看重年輕人在春晚這場演繹中的參與。她知道,央視從不缺老年觀眾,“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們一直喜歡我們,每次都拉著我們的手說,你們做什么我們都看”。但文化需要傳承,她做《國家寶藏》的時候,就找到了嗶哩嗶哩網站(以下簡稱B站),這個傳說中“最火的青年潮文化社區(qū)”,目標明確:想知道年輕的孩子們在想什么,通過我們的節(jié)目和孩子們做第一手的互動。
對方有幾分吃驚:你很勇敢,主流平臺的節(jié)目一般不太“敢”往我們這放,年輕人沒有什么忌諱,什么都敢說,如果他們不喜歡,會毫無顧忌地批評,你有這個心理準備嗎?于蕾說,我們有信心。
后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國家寶藏》第一季在B站收獲了9.8的高分、近3000萬播放量,彈幕幾乎幀幀刷屏。“這個事兒的根基,在于國寶挖掘不盡的價值。真正吸引年輕人的并不是‘傻白甜’的方法,而是有質感、有內涵的東西。”于蕾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
于蕾干脆開通了B站賬號,后來經常有人@她:你要看看這個,她就點開看,“我一直希望能夠在B站上看到現在的孩子們到底喜歡什么”。如今,她對部分互聯網社群的語言體系運用得駕輕就熟,她會在每次節(jié)目播出后說:“等彈幕養(yǎng)肥,我就扒在上面看大家給我的那些評點。”
現在,這些涓滴過往聚合到春晚的平臺上,新的元素和獨特的印記開始呈現。去年年底,2023年央視春晚吉祥物“兔圓圓”發(fā)布,這是春晚40年來首個通過互聯網大數據分析完成初始原創(chuàng)的吉祥物IP,集納了大量受眾的喜愛元素,并且經過扎實的大數據調研畫像。總設計師陳湘波說,整個設計就是建立在以滿足人們審美需求為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的。
“兔圓圓”的4顆門牙,取自“安徽模鼠兔”化石生態(tài)復原形象的典型特征。它生存在距今6200萬年前,是迄今發(fā)現的世界最早的兔形動物,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李傳夔先生發(fā)現并命名。這體現的是中國科學家的研究成就。

左圖:2023年春晚的演播廳頂部藝術裝置由四瓣花結構演化重構而成。右圖:2023年春晚的吉祥物形象“兔圓圓”。

2023年春晚以《山海經》《抱樸子》《史記》等典籍中的神獸為原型設計的中國神獸形象。上排從左至右為麒麟、鳳凰,下排從左至右為貔貅、鯤。
今年春晚舞美設計“滿庭芳”的理念,取意自中國古典文學詞牌名。由四瓣花結構演化重構而成的演播廳頂部藝術裝置,創(chuàng)意取材自距今6000年至4800年前的廟底溝彩陶標志性的“花瓣紋”。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提出,花卉圖案彩陶,可能就是華族(即華夏民族)得名的由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樊溫泉說得更直接,廟底溝文化正如這朵“花瓣紋”一樣,以陜晉豫交匯地帶為花心,逐漸綻放在華夏大地。在此基礎上,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的“中國相互作用圈”逐步崛起為光彩奪目的文明中心,成為中國之前的“中國”。
這就能很好地解釋,同過往40年春晚的導演們一樣,于蕾是被時代選中的。“今年春晚要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舞臺呈現上發(fā)力,傾向于有當代媒介經驗的導演。”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佳山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

2021年1月19日,于蕾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早年間,黃一鶴、鄧在軍等春晚導演普遍更適應傳統的廣播電視媒介形式。最初階段是聯歡會式的舞臺,現場的互動性很強,但隨著現場觀眾的增多,聯歡會式舞臺的藝術效果傳遞就無法保證。隨著春晚現場向現代舞臺的逐漸轉變,加之電視直播、分會場等新形式的要求,郎昆、張曉海等新一代導演陸續(xù)被起用。
到了2012年,哈文任總導演的春晚舞臺由半圓形演變?yōu)檠由斓接^眾席的T字型,全息LED大屏也首次大規(guī)模應用。2022年更進一步,首次運用LED巨屏打造720度的穹頂舞臺空間,使觀眾席與主舞臺渾然一體,在空間上突破了傳統晚會的觀演關系。“幾代導演呈現出來的風格演變還是比較顯著的,春晚一直在嘗試新的媒介形式、新的視聽技術,舞臺空間的藝術表現力也越來越強。”孫佳山說。
時間回到5年前,于蕾正忙于《國家寶藏》第二季的工作,她常常提醒自己,永遠不要忘了最開始出發(fā)的那個目的:做一個“自知”的節(jié)目。“我們小時候,電視上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各行各業(yè)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表揚大家的方式就是‘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積弱了那么多年,我們要猛勁兒地追趕,到這個時間點,好像我們都攆上了一些,在很多領域好像已經可以跟世界對話。這時,似乎就更需要你來看一看,我們是誰。”那時的于蕾說,她希望把這個節(jié)目捧到大家面前的時候,大家會發(fā)現,“原來我是需要這種文化節(jié)目的,我想知道我們中國人為什么是這樣,我們?yōu)槭裁匆袁F在這種生活方式存在”。
或許再過40年,人們回憶2023年的春晚時,會記得自己小時候看到過幾只自己喜愛的小動物,它們的本名挺不好記的,但它們代表著古老中國的故事。
當然,時光走到2023年時,我們的春節(jié)生活里,也不止春晚了。
陳雷是河南鄭州人,童年的除夕,在爺爺奶奶家的平房里,十幾口人守在電視機前看央視春晚,零點一到,電視機里叮叮當當敲鐘,院子里家家噼里啪啦放鞭炮,特別熱鬧。許多年后,他以另一種方式走向了春晚——2021年,37歲的陳雷成功競聘河南春晚總導演。從此,河南春晚一炮而紅,成為當下春節(jié)文藝體驗里嶄新又迷人的一環(huán)。
當時河南春晚已經辦了多年,衛(wèi)視領導層的一個共識是,整體不夠洋氣,得來點兒科技感。經費是個很大的掣肘,需要精打細算。“所以我們想,是不是首先要明確一下,在互聯網時代,衛(wèi)視春晚還有沒有必要像以前那樣做。”陳雷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這句話的直白講法是,現在還有多少人看電視?對觀眾來說,衛(wèi)視春晚意味著什么?
陳雷和團隊商量,節(jié)目是不是可以做得更“網感”一些?他要求大家把自己當成一名up主來想節(jié)目:這些視頻發(fā)上網,會不會有點擊量、會不會有瀏覽量、會不會有轉發(fā)量?
換位思考的結果是突破性的。原來,一臺晚會并非一上來就要大寫意,就要搞編年體或文學式的撰稿,“我們換了一種方式”。2021年的河南春晚確立了兩條敘事策略:表達更直觀,快樂也好,感動也好,都更接地氣;形式更靈活,誰說演出一定要在舞臺上?
當時有一種創(chuàng)作思路——要有節(jié)目俯瞰式地展示河南的都市面貌,作為現代化建設成就的一種體現。陳雷很為難,這意味著要額外搭建一個分會場,“我們沒有錢做,而且我還要填幾個節(jié)目,不可能就為一個節(jié)目搭舞臺”。
陳雷選擇拍攝一支MV。歌手騰格爾乘坐一架“不明飛行物”降落在鄭州一座地標性建筑上空,以一種魔性的土潮風格反復唱著“international(國際化)鄭州就是不一樣”。畫面中,鄭州CBD(中央商務區(qū))的繁華夜色盡收眼底。陳雷對這個構思很有些小得意,在MV中,他做出了舞臺現場不一定能呈現的“賽博朋克風”。
用同樣的思路,陳雷帶領團隊推出了《唐宮夜宴》。演員們在舞臺錄制了一遍,又在棚內錄制了一天,最后通過技術手段進行合成。虛擬場景和現實舞臺的結合,制造出博物館奇妙夜的感覺,當即爆火。

自2021年起,陳雷連續(xù)執(zhí)導了三屆河南春晚。(受訪者供圖)

《唐宮夜宴》在2021年河南春晚一經亮相,迅速“出圈”。

2022年12月31日晚,東方衛(wèi)視跨年晚會拉開帷幕。
熱烈的贊美如潮水般涌向河南衛(wèi)視。2021年臘月二十九當天直播結束,僅在一個短視頻平臺上的累計觀看人數已經超過800萬,破了河南衛(wèi)視以往節(jié)目的收視紀錄。大年初一,《唐宮夜宴》視頻更是在一天內被全網觀看了1000萬次。
2023年是陳雷執(zhí)導河南春晚的第三年,呼應兔的生肖,主題定為“卯足勁頭弄春潮”,核心仍是對優(yōu)秀傳統文化、地域文化的再發(fā)掘、再轉化與再表達。節(jié)目采用了更多元、融合的表達方式,把舞蹈、器樂、語言類表演等元素糅到一起。現在還不能“劇透”,但陳雷說,應該能“向大家傳遞簡單的快樂,給大家一些喜悅和希望”。
回過頭來看,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在過年期間不單單只期待一臺央視春晚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中國內地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上映,以3600萬元人民幣的票房正式拉開了內地電影賀歲檔的序幕。現在中國電影最重要的檔期春節(jié)檔,就是在賀歲檔的基礎上更加精準地發(fā)展起來的。賀歲檔一般從當年12月底延續(xù)到來年1月,春節(jié)檔就是緊隨其后的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這一周。2022年中國春節(jié)檔電影票房達60.35億元人民幣,取得影史春節(jié)檔票房第二的成績。
7天長假、過年期間樂于消費的習俗、快速增加的銀幕數量和院線數量,都是春節(jié)檔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一個可以明確的時間點是2013年,電影《西游降魔篇》在大年初一上映,觀眾開始將“觀影”與“春節(jié)”兩個概念緊密聯系起來。到現在正好10年。
另一條線正在與之交匯。2005年12月31日,湖南衛(wèi)視以“超級女聲”為班底,辦了一場以“跨年”為名的演唱會,一舉拿下當天收視率第一,開辟了電視綜藝節(jié)目新的黃金收視檔期。緊接著,東方衛(wèi)視、江蘇衛(wèi)視等紛紛加入這一陣營。到了2013年,在元旦3天小長假與“雙限令”(指“節(jié)儉辦晚會”與限制晚會數量)的雙向作用下,湖南、江蘇、東方、北京、浙江5家衛(wèi)視逐漸拼出重圍,形成地方衛(wèi)視跨年晚會的五大主力。這個時間距今也是10年。
這10年以來,春節(jié)文藝生活變成了盛大的協奏曲。12月31日的跨年晚會往往是奏響這場文藝盛宴的第一個音符,繼而是電影賀歲檔、地方衛(wèi)視春晚、央視春晚、電影春節(jié)檔的依次鳴奏。而熱衷于網絡生活的年輕一代,還擁有B站跨年晚會這樣極具辨識度的存在。
B站跨年晚會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一場以影視、動漫、游戲經典IP為主要呈現方式的可視化音樂晚會。在2022年12月31日的跨年晚會上,《灌籃高手》《數碼寶貝》《名偵探柯南》等作品的主題曲一次次引發(fā)彈幕的集體狂歡。如果你不熟悉二次元文化,那么在面對滿屏彈幕中暗號一樣的語言符碼時,會不可避免地陷入茫然。
“互聯網時代的社群在形成時就已經對某個主題進行了設定,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獨有的文化體系和價值取向,在一些節(jié)日的儀式當中,又產生了新的集體記憶。”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付曉光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二次元、達人向不一定是我們傳統春晚呈現的主要內容,但在B站,卻進行著對相關主題的一次次強調。“這也是互聯網帶來的分眾化。原先我們的春節(jié)可能是大家無差別地一塊過,現在則可以‘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如此浪潮中,央視春晚也就由一枝獨秀的引領者轉型為文化繁榮的集納地。春節(jié)檔的電影演員張小斐是春晚小品的常客,2022年她身穿一件藍綠色絲絨大衣出場,10分鐘后同款大衣在電商平臺售罄;參加今年春晚幾次聯排的明星藝人,有不少是各大跨年晚會的嘉賓。
“央視春晚也在從不同媒介平臺吸收其他的類型模式,對青年藝人一直非常開放。”孫佳山說,這也推動了年輕人背后的新的明星制度、明星文化向靠近主旋律的地方發(fā)展,“春晚對這些都是開放、包容的”。

在2022年12月31日的B站跨年晚會上,周深一人分飾多角,演繹“四大名著”主題曲。(視頻截圖)

年輕觀眾在2022年12月31日的B站跨年晚會重溫童年經典動畫。(視頻截圖)
春晚誕生之初,人們曾懷著極大的好奇與熱情,注視著這個尚在蹣跚學步的嬰孩,為它的活潑、時髦,為它那廣闊宏遠的世界而深深著迷。如今,當春晚步入40歲,那些未曾經歷過電視媒體初創(chuàng)時代的年輕人,又對它抱之以怎樣的目光?
在微博、豆瓣、B站以及無數個自媒體上,春晚這顆石子所激起的漣漪,是任何一檔綜藝節(jié)目都無法比擬的。26歲的廣東姑娘小池已經連續(xù)幾年圍觀豆瓣上的“春晚吐槽樓”。每年除夕,春晚一開播,就會有很多人開帖,實時討論節(jié)目,感興趣的人跟帖互動。“前排售賣瓜子”“前排領取砂糖橘,一人一個,分完即止”,大家模擬著線下聚會的空間環(huán)境,你一言我一語,“樓”越蓋越高。“一般一個帖子,‘糊’組都能有幾百樓,大組動輒上千樓。你要是不看春晚,這一晚上玩手機都不懂大家在聊什么梗。”
“新一代觀眾對春晚的反饋,是基于他們的媒介使用經驗和成長過程中的文化經驗的。所以吐槽或二次創(chuàng)作并不等同于解構和顛覆。”孫佳山認為,這恰恰說明,“人家還在乎你,年輕人真把春晚當回事兒的。”他把圍繞春晚的“吐槽文化”“二創(chuàng)文化”,同自己在直播短視頻平臺的幾個調研相對照:好些小孩去學嗩吶,學一些很不常見的民族樂器,“學得熱火朝天”;動畫《那年那兔那些事兒》僅第一季在B站已經有1.9億的播放量。“這些都說明,我國青年是高度擁抱、認可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主旋律的。”
“新一代的中國青年確實是改寫了世界范圍內的青年文化經驗。過去不管在北美還是西歐,也包括日韓,青年文化跟主旋律、跟傳統文化都不兼容。”孫佳山說,我國這種青年文化經驗從2013年前后開始展露苗頭,在10年這樣一個周期里,“都是非常清楚的”。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講師賀少雅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講起一名同事去北歐訪學的經歷——沒想到,受當地華人的影響,部分本地人竟也加入到春節(jié)的慶祝活動中。
“這就是中國年文化的魅力,也體現著傳統民俗當代傳承的新動向。”賀少雅說。在國內亦是如此,春晚就是這40年最生動的“新動向”。媒介傳播的溫情陪伴、雅俗共賞的“文化大餐”、跨越時空的中華團圓,春晚所萌生出的新的儀式感,正在融入人們日用而不知的年節(jié)禮俗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是年俗的傳承者。誰會離得開當代人共同的年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