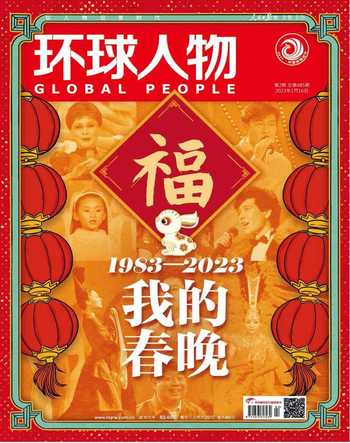讓老百姓過個歡樂年
楊學義 陳娟

2012年春晚,在舞臺科技的襯托下,雜技《空山竹語》美輪美奐。
我們清晰地記得那些春晚舞臺上的動人旋律、歡聲笑語,但總有一些有關春晚的人和事,臺前的,遠去了;幕后的,不知名。但這些人同樣不可或缺,他們用另一種方式成就著經典,“雕刻”著春晚,年復一年。
作為主持春晚次數最多的女主持人,周濤曾17次在除夕之夜與全國觀眾見面。雖然已經離開春晚的舞臺,但她依然對當時的演出細節記憶猶新。
“5點半了,頭發差不多做完了,下面該化妝了。”“7點了啊,該換衣服了。嗯,再過一會,主持人該候場了,演員們該準備了,誰從4號門進來,誰從觀眾席里出現,還有導播開始檢查了,一號機、二號機……”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她摸了摸自己的手心說:“這些環節,熟到像我手心里的紋路。”
周濤曾說,她在央視工作期間,是最年富力強的階段。更幸運的是,她又恰好遇到時代的東風:“我趕上了中國電視大發展、大繁榮的20年,等于我跟著中國電視一步一步走向它最輝煌的時刻。”
這20多年里,她見證并參與了春晚主持人的新老交替。當她1996年首次登上春晚舞臺時,正是倪萍和趙忠祥這對“黃金搭檔”最穩定的時期。而當她2016年最后一次擔任春晚主持人時,李思思、尼格買提等曾經的“新生代”也成為國民熟臉了。

1983年首屆春晚開場動畫和四位主持人,左起依次為:王景愚、劉曉慶、姜昆、馬季。

2018年6月24日,周濤接受本刊專訪。從1996年起,她一共主持了17屆春晚。(本刊記者侯欣穎 / 攝)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和榮幸成為別人記憶的一部分。因為春晚,我成了大家記憶的一部分,這是最大的一份功德。”說起往事,周濤滿懷感激。正如她所說的那樣,在春晚40年歷程中,主持人已經成為記憶的重要載體。
1983年首屆春晚,主持人以一種極具創意的方式和大家見面。一則1分29秒的動畫短片拉開了春晚帷幕,主持人王景愚、劉曉慶、姜昆、馬季分別以漫畫的形象亮相,并變身寓意大豐收的饅頭、桃子、玉米、小豬。其實,如果按當年的常規操作,應當用報幕員串起整臺晚會,但晚會現場開通了點播電話,“我報你聽”的方式不能讓觀眾參與其中,導演需要應變和互動能力強的人來串場。靠“現掛”等即興發揮藝術技巧吃飯的相聲演員很快進入導演視野,馬季和姜昆的入選也順理成章。不過,兩個人無法支撐5個小時的現場直播,于是加上了演員王景愚。可三位男主持人難免單調,導演又請來熱映電影《小花》的女主角劉曉慶,不僅解決了單調問題,還用明星效應吊足觀眾胃口。
當時的主持風格和現在大相徑庭,有時候甚至分不清主持人是在主持,還是說相聲。他們機智、活潑、幽默的風格贏得了全國人民發自肺腑的笑聲。整個上世紀80年代,馬季、侯耀文、姜昆等相聲演員繼續擔任春晚主持人,“專業主持+著名演員+相聲演員”這套模式延續很多年。
進入90年代,春晚主持人越來越專業化,大多是從播音員或演員轉型而來,長期從事綜藝節目主持。從1991年開始,倪萍和趙忠祥便成為一對穩固的組合,兩人也成為那個時代春晚的一大標志。
與全民關注一同而來的,是春晚主持人越來越大的壓力。周濤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97年春晚上,在零點鐘聲敲響之前空出了1分48秒,加一首歌太短,添別的節目更不現實。有人拿著一沓電報找到周濤,讓她念到一個時間點馬上停止。她一看才發現,這一沓電報有傳真紙、打印紙、手寫紙,有的字跡都不清晰。作為當時的春晚新人,周濤沒有多少時間熟悉電報內容,就被人匆忙叫上去了,剛上臺時,她甚至都不知道站在哪里。“我心里非常干凈,完全專注于手里那沓字跡不同、多處修改的稿件。”最終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觀眾并未意識到這個環節突兀,也正是憑借這樣的救場表現,讓她在后來的春晚被賦予了更多重任。
與剛誕生時不同,春晚主持人和演員的服裝造型發生截然不同的變化。1983年劉曉慶主持完春晚后,紅彤彤的“曉慶衫”成為一陣潮流,甚至一度脫銷,但劉曉慶穿的畢竟是日常衣服。1990年之后,春晚主持人的舞臺裝和生活裝不再混為一談,不僅色彩極為絢麗,裙裝領口甚至開得很低,發飾開始新穎別致。1994年春晚,首次出現主持人換裝的情況,倪萍開場穿了一件露背設計的大紅旗袍,后來又換上綠裝黑裙。
這樣的改變,是為了滿足觀眾日益提高的審美要求。“每年春晚的服裝也是女主持人最重視的一個環節,因為那是一個全國性和合家歡的最大舞臺。實際上我們認真準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春晚舞臺的尊重。”周濤說,每個主持人都想把最好的形象奉獻給全國觀眾:“我參與的每一屆春晚,基本上都是3套禮服的體量,4個半小時的晚會總時長,幾乎每一個多小時就換一套禮服。”
進入新世紀,無論主持人風格還是形象,都朝著越來越莊重大氣的方向發展。然而隨著觀眾對字正腔圓的發音、華麗宏大的主持詞越來越熟悉,主持人的每一個細節,特別是失誤都被成倍放大了。2007年春晚的零點倒計時階段,6位主持人的口誤、搶話等尷尬,就被稱為“春晚黑色三分鐘”。
“越是大舞臺,你越不可能隨心所欲去做一些事,你要完成一些既定的東西。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依依不舍地和它說再見了。”和周濤交流時會發現,無論在回憶央視,還是在回憶春晚時,她都流露出一種堅定和留戀交織的復雜情緒。其中最強烈的,是她對春晚觀眾的一片真情。“無論是演員,還是主持人,一定要尊重觀眾,把最真誠、最質樸的狀態呈現給觀眾。要打動觀眾,不要去引領觀眾,‘拿’著觀眾往前走。”或許,這就是在不斷面對挑剔和質疑時,春晚依然能夠經受住時代考驗,持續前行的重要原因。
從1998年春晚開始,2000平方米的中央電視臺一號演播大廳開始啟用,時至今日,這里仍然是央視春晚的常駐地。從那一年到2022年,導演已經換了一個又一個,但除了2020年,美術總設計一直是陳巖,他稱得上是春晚“鐵打的營盤”了。

多屆春晚美術總設計、雙奧核心主創團隊成員陳巖。

1986年春晚,陳佩斯、朱時茂表演小品《羊肉串》,背景是孔雀開屏造型。
不少觀眾依然對1986年春晚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羊肉串》記憶猶新,同時也記住了他們的身后“孔雀開屏”的鮮艷舞臺背景。陳巖與春晚的首次結緣,便是從那些孔雀羽毛開始。1985年大學畢業后,他來到中央電視臺工作,很快就擔任春晚美術助理。從舞美角度來說,那時的春晚更像一個小型聯歡會。陳巖清晰地記得,算上他,春晚劇組的美術、道具一共只有4個人負責。導演派他們幾個到上海買孔雀羽毛,陳巖和同事非常興奮,“首先是第一次坐飛機,第二是有中央電視臺的身份,第三是要做春晚。可以說是‘膨脹’到了極點”。陳巖心底知道,他們做的只是把羽毛插上,“但我相信有一天我們的舞臺不會這么簡單,我們會把它做成產業。”
后來的春晚舞臺的確有很多探索和進步。1990年春晚,舞臺燈光和背景層次都更加豐富、現代了。1993年春晚,將現場改造成包廂式,大廳中間為舞臺,三面為觀眾,觀眾席還被設計成兩層立體場景,不僅拉近了和舞臺的距離,還豐富了視覺場景。1994年春晚,舞臺面積擴大了,占到整個演播大廳的2/3,舞臺中央還出現一個12米的大轉臺,恢弘大氣。
不過這一時期,陳巖到歐洲留學,與春晚漸行漸遠了。直到1997年,他突然接到國內電話,春晚導演組邀請他擔任美術總設計。他首先是不敢相信,緊接著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邀請。“他們問我:你沒有離開這個行業吧?我肯定得說沒離開。其實我當時在國外賺錢就靠送報紙,然后還得學習。就這樣,我吹著牛就回來了。”
當時負責春晚的領導提醒他:你可得想好后果,失敗了怎么辦。陳巖回答:“我都沒成功過,干嗎怕失敗啊?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失敗。”他還對領導說:“您可得想好了,如果用我,可就再也下不去了。”陳巖之所以敢這么說,是深諳舞臺規律:“整個春晚的發展,不是在于每年更換一個藝術家,而是要建立一個體系,再建立一種風格。”
首次進駐一號演播大廳,春晚可以施展的空間變大了。陳巖的最大目標就是讓舞臺動起來,他把工業時代的機械亮點帶進來。晚會開場緩緩打開的龍柱、中央的噴泉,特別是機械升降臺,都成為那屆春晚的亮點。
陳巖一直說,春晚和其他晚會不一樣,有些東西是必須要堅持的。“審美應當符合中國人的特點,就像吃年夜飯,就應當四世同堂都照顧到,雖然每年就是那些菜,但必須還得有。”具體來說,就是要紅紅火火過大年,舞臺要以紅色為主,一些傳統的民族元素也不能少。
1999年春晚以中國傳統的大紅門為背景,醒目的九顆金門釘緊扣“九”的概念,象征著新世紀大門即將叩開。2000年春晚將舞臺設計成球狀,有“團圓”和全球化的雙重寓意。圓形架子上方,有鏤空巨龍圖案,寓意龍年祥瑞。2004年春晚,用現代科技將舞臺變成了大紅燈籠的形狀,又通過搭建開合階梯,形成三層表演區域。

2007年春晚,舞蹈《小城雨巷》。

2012年春晚,王菲(右)和陳奕迅演唱《因為愛情》。
在此基礎上,陳巖也有一些大膽的嘗試。2002年春晚,舞臺首次打破穩定結構,采用錯落有致的“非對稱”設計,同時加入了不少中國結元素。2003年春晚,舞臺根據具體節目搭建不同場景,比如歌曲《讓愛住我家》,一家人在前景溫馨獻唱的同時,一組演員在后景營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境,豐富了舞臺信息量。
隨著時代變化,過去成熟的舞臺模式越來越難以滿足觀眾需要了。陳巖看到,升降臺出來時,觀眾已經不再鼓掌了。2004年,陳巖看了席琳·迪翁的演唱會,在后臺看到LED屏幕時,他大為震撼。回國后,他憑著記憶在《夢想中國》欄目中做實驗,沒想到觀眾反響很熱烈。于是這項技術就用在了2005年春晚上,LED大屏幕開始在春晚地面和側幕中使用,這標志著春晚從機械舞臺走入現代舞臺。
從此,陳巖將精力用到了LED屏的視頻制作上,以便用LED大屏幕的加持,來完美配合節目。這的確讓不少節目取得成功,2007年春晚刪除了舞臺上稍顯累贅的裝飾物和兩側不透明隔斷,營造出舞臺后區和兩側的一面超大電視墻,讓舞臺簡約、大氣。舞蹈《小城雨巷》就讓觀眾第一次看到視頻與舞蹈的完美融合。這些勇敢的嘗試,還幫助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大放異彩。作為開幕式美術總設計,陳巖將LED屏用在了地面徐徐展開的畫軸上。而奧運會開幕式的技術探索又進一步促進了春晚舞美的發展,2009年春晚吸納了不少參加奧運會開幕式的班底成員,LED大屏幕與節目更加深度地融為一體。在舞蹈《城市變奏曲》中,演員與大屏幕中高樓林立的北京城形成互動,展現了城市的飛速變化,達到了虛實相生的效果。

2012年春晚,楊麗萍表演舞蹈《雀之戀》。

2009年春晚,舞蹈《城市變奏曲》。
2012年春晚,是陳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全息LED首次大規模應用,地面、天棚、舞臺正面及兩側全部采用全息LED屏幕,三維立體效果讓科技與節目的關系更為緊密。陳巖的看法是,科技雖然已經成為節目的一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藝術的情感,如何使科技幫助演員更好呈現情感,應該是重點思考的問題。那一年的春晚上,有兩個節目就是他思考的結果。一個節目是楊麗萍的《雀之戀》,當舞臺后方大屏幕呈現的孔雀開屏畫面與楊麗萍呈現的造型融為一體時,舞者塑造的孔雀形象更加飽滿了。另一個節目是王菲和陳奕迅演唱的《因為愛情》,兩人最初是一前一后隔很遠站著,音樂一響,舞臺中間升起一座全息影像的橋梁,整個舞臺飄起了全息影像構建的花瓣。配合音樂,“橋梁”“鮮花”構建了唯美的愛情意象。
后來,陳巖讓越來越多的“黑科技”上了春晚。2017年春晚,舞臺可升降屏幕達到了創紀錄的173塊,其中地面132塊、天空41塊,為觀眾呈現出天地渾然一景的場景。2019年春晚,又首次實現了全媒體傳播,在4K、5G、VR、AR、AI等多方面進行技術創新。
不過,陳巖還是很冷靜,始終將科技作為一種表現手段,而不是藝術本身。他說:“現在我最擔心的是唱歌的人光為了(舞臺)漂亮,那挺可怕的。”在他的概念里,西方美學是“三維”的,而中國美學是“二維”的,通過看似有限的“形”傳遞更多的“意”,這才是他的追求。中國人不一定要建造世界最大舞臺,但一定要創造最能激發人無限遐想的舞臺,這才是科技對舞臺的意義。
長期研究春晚的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宮承波在其主編的《春晚三十八年》一書封面上,特意加上了一個副題:伴行改革開放,歡樂國人大年。他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之所以這樣做,是想闡述春晚的發展意義。“伴行改革開放”決定了春晚要把體現時代元素的時事、科技、潮流等融合進去;“歡樂國人大年”決定了無論時代怎么發展,春晚都應當將老百姓的歡樂放在重要位置。在春晚的發展歷程中,始終都在尋求這對關系的共融與平衡。
宮承波曾跟訪首屆春晚導演黃一鶴,讓他印象極深的是黃導的堅定初心:“我們不止一次聊過,當初為何要辦春晚?他說其實很簡單:讓老百姓過一個歡歡樂樂的好年。”這個看似簡單的愿望,實現起來卻并不容易。
1983年和1984年春晚大獲成功后,黃一鶴產生了一個大膽想法:將1985年春晚的舉辦地搬到四面環座的北京工人體育館,讓春晚場景從“茶座式”變成氣勢恢宏的“場館式”。“1984年,我看了國慶閱兵式、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再也坐不住了。我們是國家一級的電視臺,晚會節目應該符合身份,向世界展示我們的繁榮,讓人民看到希望。另外,連續兩年搞茶座,模式談不上創新,觀眾容易厭倦。”從黃一鶴的回憶可以看出,他想要辦出大國氣勢。
不過,現實并未如他所愿。由于體育館環境超出了導演組駕馭能力,觀眾距離演員非常遠。舞臺上精心布置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等景觀也沒被攝像機拍進去,觀眾看到的是一片黑壓壓的背景,與過年熱鬧喜慶的氛圍很不相稱。問題還有很多:彩排準備不夠、港臺風太濃、廣告太多……后來主管領導和導演團隊總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抓住電視規律,也沒有根據自身科技實力準確把握春晚動向。
雖然1985年春晚有很多遺憾之處,但整個80年代的春晚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宮承波認為:“從藝術魅力的角度來講,真正大美的、富有感染力的東西,都是樸實自然的。”這也給了后來者啟發,不能丟掉春晚最寶貴的東西,“不管科技如何發展,春晚都不能單純炫技,這樣就不溫暖、不真實、不真誠了”。

2006年春晚,舞蹈《俏夕陽》。
后來的春晚有很多形式上的探索。1988年春晚以北京演播室為中心會場,同時穿插廣東、四川、黑龍江三個省臺的實況轉播,首次突破了地域限制,將春晚舞臺放到全國多地。1990年春晚,評書演員田連元、小品演員朱時茂等明星以隊長身份,率領隊員開展除夕夜比拼,串聯起整場晚會。1996年春晚,北京、上海和西安首次實現“三地聯演”。通過衛星實時傳輸,演員通過大屏幕實現了三地隔空聯演,打破了單一會場的單調。直到1998年春晚到中央電視臺一號演播大廳舉辦后,形式相對穩定下來。
但這種穩定又帶來千篇一律的模式化問題。“文藝創作永遠要抓住時代的脈搏,最怕失去生機活力,變得老氣橫秋。”宮承波認為,春晚日益成熟的同時,也迎來新的挑戰。“既然模式化了,就要不斷突破模式;既要走向成熟了,還要走出成熟,保持生機和活力。歸結為一點就是,要回歸人民群眾,老百姓的現實生活需求永遠是創新源泉所在。”
“開門辦春晚”就是突破模式、“走出成熟”的大膽嘗試,催生出大量經典作品。2005年的《千手觀音》是“開門辦春晚”取得強烈反響的第一個節目。2006年春晚,以唐山皮影為靈感的舞蹈《俏夕陽》走紅,一群基層老太太形神兼備的表演具有獨特視覺沖擊力。
隨后幾年,越來越多的“草根明星”通過春晚舞臺大放異彩。2008年,盲人歌手楊光演唱一首大氣磅礴的《等待》,令人格外動容。初出茅廬的王寶強在《農民工之歌》和小品《公交協奏曲》中兩次以農民工形象出現。2011年,在專門開辟的“我要上春晚”版塊上,西單女孩任月麗、旭日陽剛組合、深圳民工街舞隊輪番登場。2012年春晚,“大衣哥”朱之文唱了一曲《我要回家》,還很青澀的開心麻花演員沈騰、艾倫首登春晚舞臺。
在“開門辦春晚”的浪潮中,主持人也被吸納進來。2014年春晚上,演員張國立加入主持人隊伍,以接地氣的語言和插科打諢的方式與觀眾互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春晚的主持人司儀化風格。甚至有人說,這很像是首屆春晚風格的復歸。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新人因走上春晚舞臺被觀眾熟知。宮承波說,這正是春晚的可愛之處。無論是主持、舞美,還是節目編排,春晚能夠一直向前走的秘訣依然是真誠。宮承波說:“實際上,植入廣告、過度炫技這些問題,就是不真誠導致的。”情感才是春晚連接觀眾的唯一橋梁,春晚之所以能夠在今天依然打動我們,就是因為這座情感的橋梁依然穩固,帶我們越過每一年的浪潮澎湃、際遇起伏,在這一晚準時回到家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