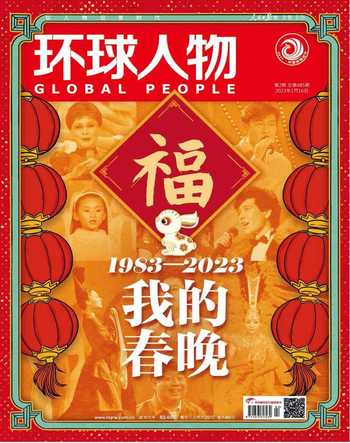鄉愁紀念冊
楊學義 馮群星 劉舒揚

2009年春節,“5·12”汶川特大地震受災群眾走出陰影,在建好的新房里看春晚、包餃子。
當中國香港歌手張明敏在1984年春晚演唱《我的中國心》后,同年12月,《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香港確定在1997年7月1日回歸。
當中國臺灣歌手費翔在1987年春晚穿著最前衛的服裝演繹勁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時,無數年輕歌迷的青春火焰被點燃了,開放的新風吹遍神州大地。
當那英和王菲在1998年春晚攜手演繹《相約一九九八》時,中華民族正沉浸在“言有盡,意無窮”的香港回歸喜悅中。
當田震在2003年春晚用一曲《風雨彩虹鏗鏘玫瑰》唱出女足姑娘的英姿颯爽、永不言敗時,勇奪世界杯亞軍的巾幗英雄再次燃起國人激情……
如果時光是一輛緩緩行駛的列車,那么這些春晚經典節目就像重要站點的標識牌。坐在列車上的我們,可能會逐漸忘卻大部分沿途的景色,卻很容易想起列車停駐時,那個醒目的站牌。因為它提醒你,這一站的哪幾處美景,是永遠值得銘記的。這種銘記,構成了個體記憶、家庭記憶,又進一步豐富了民族記憶。
春晚的“家—國”展演是如何深入家庭的?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謝卓瀟在8年前撰寫相關論文時,就開始進行調研和思考。
在她看來,春晚的魔力首先來自春節這個節日及其相伴相生的一系列儀式,像吃團圓飯、祭祀祖先、燃放爆竹。“伴隨著電視的普及,春晚得以在春節的‘神圣時刻’深入中國人的家庭公共空間,成為一種精神文化媒介。”
在家鄉貴州省荔波縣,謝卓瀟圍繞16個家庭及部分個體展開了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訪談對象一共69位。她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的春晚回溯,往往與自家的第一臺電視機密切相連。“他們記得家里買電視的所有細節,包括價錢、牌子、購置電視的過程,相伴而來的是當時看電視、看春晚那種極大的激情。”
69位調研對象中,率先承包土地的楊云祥是在1986年擁有第一臺電視機的。他揣著種植花菜掙到的幾千元錢,坐車到貴陽把電視機扛回了家。蒙尚武夫婦則是在1989年結婚時,才舍得買一臺14寸的黑白電視機,花費是兩人近三年的工資。
退休公務員謝榮昌的記憶最曲折。他最早看電視是在單位,上小學的兒子吵著跟他去,“看到睡著了還不肯回家”。他曾托人從上海帶回一臺電視機,卻被親戚“截胡”。1982年,單位的電視機被清退,謝榮昌終于借此機會買回一臺,全家人因此趕上了1983年首屆春晚的播出,鄰里街坊都聚過來看春晚,“沙發、沙發扶手、沙發旁邊都站著人”。家里大門始終開著,孩子們呼喊著跑來跑去。
那時的胡同里、弄堂中、小巷間,大江南北的中國人對春晚的最初記憶,都離不開這種集體觀看。電視屏幕小,人頭卻很多,站在后頭的人可能看不清電視畫面,但熱氣騰騰的人氣烘托出幸福的年味兒,成為揮之不去的時代記憶。謝卓瀟察覺到,經歷過這種集體觀看的人,對春晚的感情最特殊、最忠實。
謝卓瀟還發現,當一個人回憶起多年前的某屆春晚時,可能已記不清具體的節目信息,幫助他們想起過去的,是自己家庭與春晚有交集的大事件。春晚就像一個時間坐標,成為梳理家庭史、回味悠悠歲月的支點。訪談中的一次沖擊來自她的舅父。“全家最后一次看春晚是什么時候?”舅父回答得很清楚:“你舅媽還在的時候。她是2002年春節初五不在的,現在已經有13年了。”
另一個讓謝卓瀟印象深刻的訪談對象是82歲的老太太周簡。2015年,周簡的4個子女全都回家過年。這樣的團圓場面已經久違22年,一家人策劃了一場家庭春晚。謝卓瀟在周家看到,電視上播放著春晚,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家人的“春晚”上,周簡的外孫女高興地報幕:“第一個節目是大舅媽的扇子舞《我的祖國》,第二個節目是大舅唱的《媽媽的吻》……”全家人甚至模仿了春晚與觀眾的互動,在家庭微信群里發紅包、搶紅包。“這和2015年春晚的流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謝卓瀟感慨:“春晚維系親情的作用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這些情境下,春晚的記憶文本與其他記憶文本互文,變成人們建構、流通其他記憶的一部分。”
就像周簡一家人大方地在朋友圈里傳播自家春晚的視頻一樣,如今電視中的春晚也在利用微博和短視頻影響千家萬戶。即便不看電視,只要拿起手機,人們的目光也很難避開春晚。疫情的三年時間里,不能回家過年的人們甚至與父母進行視頻連線,一起隔空看春晚。
最終,謝卓瀟的論文定了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現代性“鄉愁”:小鎮家庭的春晚記憶結構》。的確,經過40年,觀看春晚早已成為中國人鄉愁的寄托。這場盛大的演出儀式,將每一個小家凝聚在一起,變成“神州萬里同懷抱”的大家。它讓每個卸下一年疲憊的人意識到,原來“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它提醒每一位漂泊他鄉的人,無論你走到哪里,永遠都有“天邊飄過故鄉的云”,只要有時間,就要“常回家看看”。
對海外華僑華人來說,春晚是真正意義上的萬里鄉愁。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1985年除夕,黃錦波在春晚舞臺上第一次唱起這首《龍的傳人》。他的普通話很標準,只有仔細聽,才能辨別出個別字詞的走音。他身著時髦洋氣的黑色燕尾服,鏡頭掃過1985年還是“黑藍灰”衣著的觀眾時,兩方形成一種奇特的對照。
這是春晚第一個為海外華僑華人準備的節目,黃錦波的名字第二天就傳遍大江南北,很多人記住了這個首位登上春晚舞臺的美籍華人。
兩年后,春晚迎來了另一位出生于中國臺灣的美籍華人費翔。演唱前,費翔說:“能在北京過春節,我心里十分高興,我想與大家分享這激動與快樂。這次回到祖國,我初次見到了我的外婆。請允許我唱一支歌,獻給我的外婆, 獻給我的母親,獻給我的故鄉。這支歌的名字叫《故鄉的云》。”

1985年,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左)接見黃錦波。

1998年,黃錦波在湖北抗洪前線慰問搶險救災的戰士。
可以說,春晚幾乎從誕生開始,就成了改革開放的中國深情呼喚海外游子最好的舞臺,也成了海外華僑華人了解祖國精神風貌、寄托故土眷戀的現實載體。春晚歷史上的多個“首次”,正是這種雙向奔赴的最佳見證。
1986年,春晚首次出現英語主持;1989年,首次開辟了面向廣大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的600平方米英語晚會直播現場,并在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目中轉播;1993年,春晚首次設有6位主持人,分別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華人較多的新加坡。
再后來,隨著1992年10月1日央視中文國際頻道開播,海外觀眾可以和國內觀眾一同收看春晚了。1993年的春晚信號覆蓋了整個亞洲以及獨聯體和東歐等地的60多個國家;北美洲的兩套衛星也向海內外同步直播,覆蓋了從加拿大到加勒比海的全北美地區。春晚一步步走向世界。
結束“春晚之行”的3年后,黃錦波在1988年3月創辦了中美電視臺(CATV),用英語報道中國,每晚9點黃金檔在洛杉磯18臺播出。他把馬季、馮鞏等人在春晚表演的經典相聲翻譯成英文,結合美式脫口秀的風格,呈現給美國觀眾。“我始終堅持用英文向美國報道和介紹中國,就是希望不僅能向海外華僑華人介紹中國的巨變,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當地人士對中國的偏見。”直到現在,他在除夕之夜還必定看春晚,“里面有我的很多老朋友,馬季、費翔、張明敏……我看看他們今年有沒有上啊!”
對年輕一代來說,春晚也許就是互聯網時代的“電子鄉愁”。
“90后”對春晚時代性的感知是借由一件件電子產品標記的。2006年春晚直播過程中,經過1億人次的短信投票,“團團”“圓圓”成為兩只贈臺大熊貓的乳名,表達了全國人民盼望兩岸團圓的心聲。田靜雯的媽媽就是那一億分之一。在2022年“團團”因病去世時,21歲的田靜雯是那么清晰地記得媽媽給春晚發短信選名字的每個細節,還有主持人公布得票最高名字時自己雀躍的心情。“一切如在昨日。”在她的講述里,春晚短信投票這件事,跟那幾年自己給《快樂男聲》短信投票一樣重要,“都是彌足珍貴的舊時光”。
后來,“搶紅包”在2015年前后取代了發短信;近幾年,短視頻直播間聊天又取代了“搶紅包”。舞臺上下、熒屏內外,親朋好友間的互動也在春晚時刻里與時俱進了。
一同被改變的還有人們的消費方式。2020年春晚主持人的口紅色號,讓田靜雯和閨蜜們接連討論了好幾天,“我們都覺得這個造型真好看”。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佳山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小時候過年喝兩瓶可樂就是很幸福的春節消費了,“而現在很多消費習慣是在移動互聯網周期形成的,春晚可以讓我們很直觀地感受到節日消費形態的變化與更新。”孫佳山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放在更廣闊的視域下,春晚是傳統節日進行現代性轉型的一個縮影,而這40年的實踐也充分表明,“說我國的春節是傳統文化現代性轉型的樣板,一點也不為過,確實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世界范圍內來看,這都是屈指可數的文化經驗”。
“春晚更大的價值,是將個體、家庭與廣闊的外部世界連接,成為‘家’‘國’一體的當代催化劑。”謝卓瀟說,自從首屆晚會大獲成功,春晚便擁有了一種“自覺”,它力圖成為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一種坐標,并在形式多樣的表演中承擔起凝聚國家情感的職責。如果把40年的春晚串聯起來,可以明顯看到“家”與“國”的交相輝映,既有“天涯共此時”的溫情,也有“共祝愿祖國好”的厚重。
1985年的春晚值得一提。在那場著名的“工體春晚”上,雖然舞臺創新效果遭遇滑鐵盧,但有一個節目具有標志性意義——伴隨著《運動員進行曲》,主持人馬季、姜昆和體育解說員宋世雄共同邀請一隊人站在了聚光燈下。
在剛剛過去的1984年,中國女排奪得第二十三屆洛杉磯奧運會冠軍,實現了繼1981年女排世界杯和1982年女排世錦賽冠軍后的“三連冠”。正在福建漳州備戰第四屆女排世界杯的隊員們委托宋世雄,在這個團圓喜慶的除夕夜,向陪伴自己多年的無名英雄們道一聲“謝謝”。領隊、教練、隊醫、廚師、司機……宋世雄向觀眾一一介紹著他們。
正如現場播放的那支短片中所說:“他們和你們一樣,只有一次青春,一次生命……然而祖國交給他們的,卻是默默無聞的重任……逢年過節,他們撇下妻子兒女,陪你們練球,暗中模仿你們比賽中的對手,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胸前沒有掛過金牌,他們的手里沒有捧過鮮花,報紙上沒有他們的名字,電視中看不到他們的身影。然而,他們仍在默默地、毫無怨言地流著血、流著汗,送走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天……”
這個節目在現實的體育世界有著更加激蕩人心的延續:當年11月,中國女排以七戰全勝的成績在世界杯奪冠,第四次榮膺冠軍;第二年,它成為第一支在世界女排歷史上連續五次奪得世界大賽冠軍的隊伍。
1995年的《獻禮黃河》,也是很多觀眾難忘的節目。
當時,臺灣問題是國內的焦點話題之一,春晚為此安排了十多位居住在黃河流域各地區的群眾來到現場。他們使用當地特有的器皿,把來自1000多個黃河水源站的水樣倒進透明的塑料水瓶里。
99個水瓶被排列成一幅微型的黃河示意圖,展現出黃河水“青—灰—淡黃—醬黃—灰—藍”的顏色變化。令人動容的是,由于大雪封山,來自青海水源地的女孩拉姆行走了12天,才帶著所有鄉親的祝福走上春晚舞臺。她和其他群眾代表一起,把黃河水交到了臺灣同胞手里。
“從水樣的采集到最后送給臺灣同胞,每一個環節都表達出人們關于祖國統一的美好愿望。家住黃河兩端的送水人握手相見,更蘊蓄豐厚內涵,海峽兩岸‘一家人’的概念得到了最樸實而又深刻的傳達。”宮承波這樣闡述。
對于國家的認同與愛,總是在一些特殊時刻強烈迸發。它可能讓我們精神抖擻,也可能讓我們淚流滿面。在宮承波看來,進入21世紀之后,有一臺春晚盡顯這種“悲欣交集”的復雜感情,那就是2009年的春晚。
“對中國人來說,2008年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年份。‘神舟七號’ 邁出中國人航天行走的第一步,北京奧運極大地激發民族自豪感,但與此同時,金融危機的寒潮在年底漸起漸兇,令人牽掛的還有汶川地震后破碎的土地和受災的同胞。”宮承波回憶道。

1985年春晚,朱玲等女排隊員出現在現場。

1995年春晚,99個裝滿黃河水的水瓶被排列成一幅微型的黃河示意圖。

2009年春晚,舞蹈《天地吉祥》

2008年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實現了金牌總數第一的歷史性突破。對中國人來說,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夏天。人們聚集在電視機前,為體育健兒們吶喊鼓掌、如癡如醉。在春晚上,50多位奧運健兒集體亮相,用他們的獎牌拼出“祖國萬歲”的字樣。
如何在歡樂喜慶的除夕夜加入汶川地震的元素?最終,春晚連線了“敬禮娃娃”郎錚、“最堅強女警花”蔣敏、“可樂男孩”薛梟等劫后余生的災區代表。“悲傷過去了,我們要微笑面對生活。”他們樸實、沉靜的講述,于細微處傳遞著樂觀、團結、堅強的力量。
劇場被震塌后仍堅持去災區演出的四川民族歌舞團,在春晚現場表演了舞蹈作品《天地吉祥》。在升騰的白煙中,身著羌族服飾的舞蹈演員們登場,踩著鼓點獻上了真誠而雄渾的舞蹈。
“我們受到了大災,但得到了政府、海內外朋友方方面面給我們的援助。滴水之恩,涌泉相報,這時候我突然發現《天地吉祥》能生動地傳遞災區人民感恩和祈福祖國的心聲。地震可以毀壞我們的家園,但是我們要告訴世界:羌歌依然動聽,羌舞依然美麗,四川依然美麗!”團長蘭卡布尺當時這樣說道。
以情動人,是春晚上家國認同的核心。這些節目固然有高超的編導技巧和精彩的視聽呈現,但究其根本,是主創人員發自肺腑、每個中國人都能共情的純粹情感。
在2020年春晚上,疫情防控特別節目《愛是橋梁》達到了以情動人、毫無技術渲染的最高潮。
據這屆春晚的總撰稿秦新民回憶,《愛是橋梁》是春晚歷史上準備時間最短的節目,晚會開播前10小時才被加入節目單,甚至沒來得及進行一次正式的彩排。
“特別想給所有奮戰在一線的白衣天使拜年,我們在這兒過年,你們卻在醫院幫我們過關。”“想給所有的湖北人拜個年,隔離病毒,但絕不會隔離愛。”“我們愛你們!不止在今天,還在未來生命中的每一天。”6位主持人滿含深情地朗誦出這些句子,他們身后的大屏幕上則持續播放著武漢戰疫的情景。
這些在新聞中出現過的畫面,在春晚這個特殊的場合,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國人的心中。“淚目”成為網友在2020年除夕夜評論春晚的熱詞。而節目傳達出的信息——守望相助,我們終將渡過難關——不僅在當時撫慰了人們的心,也在近三年起起伏伏的疫情防控生活里,給了無數人力量。
電視在“演”春晚,春晚在“演”家國。在熒幕內外,春晚構筑起一道從微觀到宏觀的光譜,它強化了傳統的家庭中心主義,也把家庭聚合成“想象的共同體”的國家。這樣的儀式感,在今天與未來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