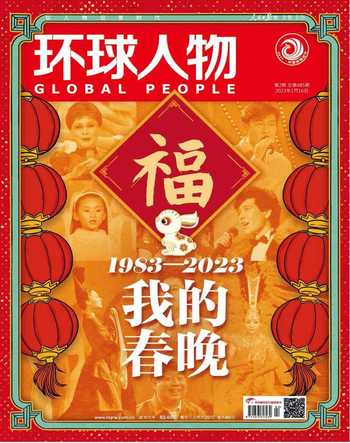美國正經歷“冷內戰”
刁大明
這場美國議長“難產”鬧劇涉及許多政治人物,自然也牽動很多因素。從總體上看,背后有兩條最為關鍵的主線,即美國兩黨政治的高度極化與各自黨內的碎片化。這兩條線索的交錯,積累出的必然是持續上演的政治危機。
共和黨在本屆國會中僅實現222比212的多數優勢,可謂是第107屆國會(2001年-2003年)以來最微弱的一次。如此勢均力敵之下,兩黨互不相讓,針鋒相對,直接導致未來更加極化。相比于極化,碎片化趨勢略微隱形,但也普遍存在良久,兩黨皆有之。除了此次反對麥卡錫的共和黨自由連線黨團,民主黨也在吸納勞工家庭黨等激進自由派力量。吸納與被吸納的雙方在選舉時可以聯手,在施權時卻可能出現內訌。
議長“難產”,應該可以與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總統的政治意義聯系起來,甚至并列觀察。這是兩黨政治持續重大變化與又一次重組的表現。更深層次講,這種變化也映射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態、經濟發展方式、社會與人口結構乃至國際角色與行為的重大變化。
美國政治生態已呈現出“部落化”端倪。兩黨更像兩個部落,黨內還有相互沖突的分部落。一些政治人物與生俱來的政治標簽——比如“白人”“少數族裔”——讓他們帶有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使部落之間更水火不容。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富裕階層擴大在全球的投資,導致美國自身實體經濟和藍領階層的空心化。“茶黨”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美國中下層的憤怒,其背后是美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失衡。
我們也要密切關注美國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學界普遍認為,到2040年美國將變成一個“無多數族裔人口結構”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白人必將感受到巨大壓力——“美國到底是誰的美國?”文化底色與認同感的缺失,將成為美國面臨的重大問題。
在國際角色上,美國曾經通過提供更多“國際公共品”來體現自己所謂的“國際領導力”。但現如今,美國在應對國內劇烈變化的同時,表現出日益明顯的“內顧”傾向,將盟友體系視為工具,肆意渲染所謂“威脅”,為全世界輸出了更多不確定性。
令人玩味的是,比15輪投票還嚴重的前一次議長“難產”,即從1859年12月延續到1860年2月的第36屆國會議長選舉投票,共44輪。一年后,南北戰爭爆發。南北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北方工商業與南方農業種植業及其背后利益的深度矛盾。在當今的美國,不斷累積的政治對抗和社會分裂正以一種不完全暴力的方式顯現出來,整個國家正在經歷一種所謂的“冷內戰”,這種混亂與病態可能將持續很長時間。
(本文根據采訪整理)